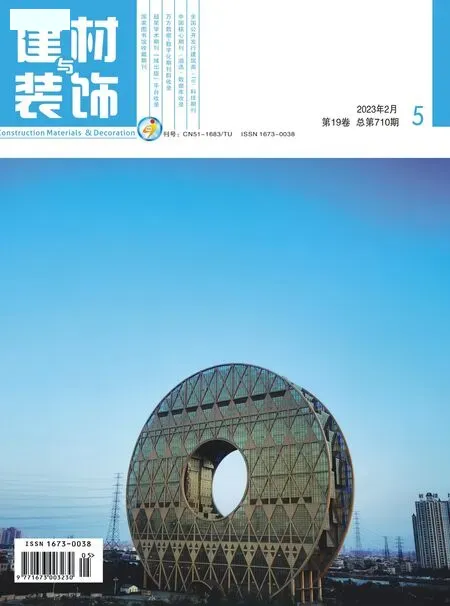基于SCOOP 結構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統優化模型分析
陳本旺
(西南交通大學,四川 成都 610031)
0 引言
現如今城市平交路口通用的綠波帶干線控制無法滿足對多路口交通進行協同控制,單一的相位時間讓多路口堵塞無法疏通,出現部分路口的延誤時間與停車次數高于理論值的現象,基于SCOOP 結構,將通行權作為輪詢中CPU 對周邊設備的定時詢問服務時間,服務時間的交替會導致因為排隊長度影響數據傳輸效率降低,也就是紅燈來臨之前無法通過路口的已有等待車輛,這種車輛會在一個信號燈周期里面經歷兩次綠燈后才能通行,因此會產生路口通車次數大于1 的情況,兩次或多次停車次數產生的延誤時間會被計算到路口延誤時間中,導致城市平交路口的多路口堵塞[1-3]。以什邡市鎣華山北路的3 個連續平交路口為參考模型,提出一種適用于多路口的協同控制策略,目的是降低這類停車次數與總延誤時間。
1 建立模型
3 個模型路口的綠燈時間分別為40s、38s 和45s,僅金河南路路口的相位差配時滿足傳統綠波帶控制,而高于38s 的兩個路口會由于相位差配時與實際路口配時的差值導致車輛無法享用當前路口通行權,使停車次數大于1,進一步增加擁堵[4-7]。為降低此類停車次數,本文提出針對相位差配時的優化算法。

式中:△t——相位差的優化量,s。優化量的取值需要通過Vissim 平臺進行路況仿真,通過對比路口停車時間的降低量,得到最優優化量[8]。
2 基于SCOOP 結構的系統優化模型
通過SCOOP 結構系統模型進行優化,將原本的信號燈配時所依據的車速調整為每一個相位具體車道的排隊隊長,即排隊車輛的總延誤時間[9]。第t 周期的i 相位上,j 方向的k 車道上(后文同),車道上的車輛隊列長度如下。

式中:Sijk(t)——j 車道的k 方向車道上停車隊列;Dijk(t)——k 車道上的剛到的隊列長度;Fijk(t)——離開路口的隊列長度;Slimit——k 車道上能夠容納的極限排隊長度。
擁有綠燈通行權時離開路口的車輛計算如下。

式中:Gijk(t)——同Sijk(t)情況下,離開路口的隊列長度;ti——相位綠燈時間;s——車輛速度。
接著,用Z(t)表示總延誤時間,用zijk(t)來表示車道延誤時間,那么此時此刻擁有通行權的相位車道的延誤時間表達式如下。

當A(i-1)jk(t)-Gijk(t)>0 時,基于本文車流不會分散的前提,車輛會均勻行駛,并設斷面通過的效率為x,單位s/輛,y 為車道總到達車輛數,z 為車道離開的車輛數,可以得到以下關系。

第二種情況是當S(i-1)jk(t)-Gijk(t)<0 時[9],可以得到式(6)。

該時刻相位上沒有通行權時,車道上的延誤時間就表示如下。

綜上,可以推算出在t 周期中,總延誤如下。

推算出平均延誤的值如下。

式中:SJk(t-1)——車道已經存在的排隊等待的車輛數;Djk(t)——車道上的車輛數。
3 數據結論
仿真實驗通過Vissim5.30 版本完成,雍城南路路口、金河南路路口和亭江東路路口3 個目標路口的數據采集工作于2022 年6 月24 日結束,當日交通量統計數據如表1~表3 所示。

表1 檢測路口1——雍城南路路口

表2 檢測路口2——金河南路路口

表3 檢測路口3——亭江東路路口
可以發現,原相位差配時不是最優決策[10-12],對比仿真結果,路口1 和路口3 最優配時是相位差減少3s,檢測路口2 的最優配時是相位差延長12s。
最后,對比實際路況和傳統算法的路口平均停車次數和單位相位總延誤時間如表4、表5 所示。

表4 不同方案下各檢測路段總延誤時間的數據對比

表5 不同方案下各檢測路段平均停車次數的數據對比
根據所統計的實驗數據,計算出在配合動態綠波周期與優化后的算法的工作下,對比原本的沒有用任何優化方法的實際路況,3 個檢測路段的總延誤時間分別降低了6.1%、23.9%和18.5%,平均停車次數分別降低了4.5%、25.4%和30.5%,足可見優化算法的有效性。
4 結語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通過優化交通控制系統來解決城市交通的通行效率在一定范圍內是最方便和最經濟的辦法。國內傳統綠波帶控制法大多通過歷史數據的采集、分析進行靜態控制,面對臨時的大型會議、商業活動等導致的隨機堵塞情況往往顯得束手無措[13-16]。本文基于SCOOP 結構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統優化模型,通過實時的路口總延誤時間與停車次數對主干道連續路口的通行率進行了優化,從平臺檢測的數據來看,新方法理論上優于了傳統算法。但在實際運用中,車流的分散情況、司機駕駛技能的熟練程度等客觀原因都會導致真實數據與理論數據的偏差。當然,也正因為有不可控的客觀因素一直存在且各不相同,動態控制的交通系統會逐漸成為主流,而隨著越來越多專業人士從不同角度進行系統優化,中國的道路交通也必將變得越來越來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