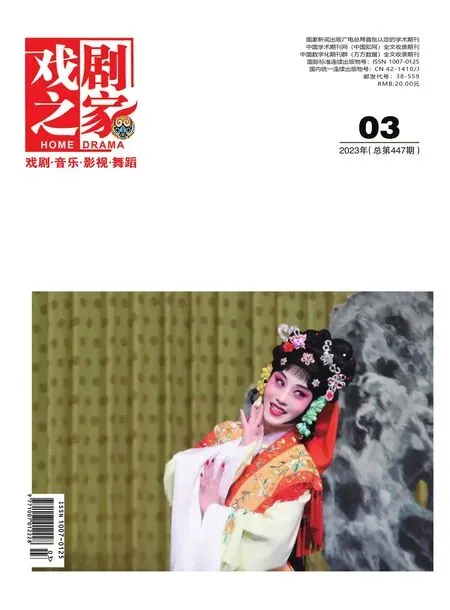新世紀華語武俠電影中的功夫元素研究
郭傳京,李瑤瑤
(韓國又石大學 韓國)
一、研究背景
在海外,功夫成為中國武打、武術、武俠的專屬代名詞。中國武術源遠流長且起源復雜,糅合了中國古代文化中的舞戲等技藝,同時功夫作為武俠文化傳播的載體,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電影產業的國際發展進程。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好萊塢電影就持續吸收東方功夫元素,并且創造了一系列票房新局面。近些年來,我國電影市場中的武俠電影作品面臨著諸多困境,這歸因于大眾審美趣味的變化與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武俠電影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而武術精神也重新塑造了中國形象。“武俠電影”中的“武”指武功,屬于傳統文化中功夫元素的關鍵內容。在電影技術不斷革新的背景下,華語武俠電影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并逐步走向創作高峰,如《十面埋伏》《臥虎藏龍》《雪山飛狐》《李白之天火燎原》《黃飛鴻之南北英雄》《一代宗師》等,其中不乏極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品。如今,武俠電影經過現代化技術沖擊,已經形成了多元化影視風格,并且武俠作品也在不斷融合中國傳統藝術特點與樣式,不管是琴棋書畫,還是舞蹈與詩歌,這些都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1]。
二、華語武俠電影中的功夫元素研究
(一)武俠電影中的功夫元素
大眾的意識形態由長期社會經驗所決定。武俠電影即在電影藝術中融入武術這一元素,并汲取中國傳統倫理觀念進行敘事引導,通過功夫元素推動故事情節,從而引導大眾認可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或對某一情節產生情感共鳴,然后再以藝術形式表現出來,行善、貴生、維護正義成了俠客行為的倫理指向。俠義精神與莊子思想有著緊密聯系,不同于老子“替天行道”的行為準則,莊子思想對于自身的個性要求和精神追求豐富了俠客的形象,我們只有從不同的藝術類型方面不斷總結經驗,最終才能夠創作出獨具藝術魅力的武俠電影作品。例如《繡春刀Ⅱ:修羅戰場》這部電影中,以沈煉為代表的武者們從綠林逐漸步入官場,他們并非利用自身超凡的身手來改變不合時宜的秩序,而是處心積慮地想要融入外部環境中。沈煉等人所行走的已不再是以往游離于秩序之外的“江湖”,而是等級森嚴的“江湖”,此種意義上的等級來源于當權者的地位,這也使得功夫電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俠以武犯禁”褪去了一定的崇高性和神圣感,被電影置于人道和正義的對立面。《瑯琊榜》中的武士百里奇所練的功夫招式比較生硬,看上去很厲害,實則外強中干。大部分綠林英雄出身于草莽,而草莽英雄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是通過粗暴殺戮,但真正的武俠精神不單單是行俠仗義,更是從根本上找出癥結所在,從而教化人、改變人,將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為國家和社會所用,最終真正解決問題。在《臥虎藏龍》中,李慕白、俞秀蓮苦口婆心地教化與引導玉嬌龍,以免其將一身武學用在邪門歪道上。而草莽英雄不同于真正的俠客,主要區別在于是否懷揣著一顆仁愛之心。此外,在《臥虎藏龍:青冥寶劍》中,幾乎每隔十分鐘就會出現一場打戲,并且大部分只是為了追求動作場面。另外,江湖兒女不完全等同于草莽英雄。俗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即使到了必須用武力解決的地步,也不同于兩國交戰那般大動干戈,而是點到為止即可,絕非誓不罷休。在該影片中。李慕白、俞秀蓮兩人的招式就是剛柔并濟,具有極大的藝術欣賞價值[2]。
(二)功夫元素的空間解構
自古以來,功夫就存在各種各樣的稱謂。漢代稱之為“武藝”,所以有了“十八般武藝”之說;春秋戰國稱之為“技擊”;清代稱之為“武術”;而到了民國以后,武術又被稱為“國術”。為了正確區分功夫與武俠、武林、武打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先對武俠片、功夫片進行區分。功夫類型電影更多來源于香港,而武俠電影則來自上海,并且兩者不可完全獨立而論,武俠片傾向于呈現俠義精神與故事情節,脫離不了功夫這層外衣,而功夫片側重表達“功夫”的結構,也離不開“俠”之精神。武林又是一個有關空間的概括,一般統稱為江湖,“有俠客的地方就是江湖”。然而江湖這一空間概念在歷史變遷中也逐漸擴大、轉變,從占山為王、落草為寇轉變為歸隱的居所,甚至是門派等私密世界。由此可見,武俠電影中的功夫元素指的是中國功夫中的關鍵構成部分,如刀槍劍戟、氣功、法寶、拳腳、暗器等,當這些內容在電影中呈現時就不再是單純的武打,而是將所有的功夫樣式整合起來并表現出民族文化中的俠義精神。武俠電影結合了現代化技術和傳統文化精神,在虛構中體現真實情景,可見武俠電影的變化與發展持續伴隨著大眾審美需求和電影技術的變化而不斷取得進步。武俠電影以功夫為主要表現手段,而功夫是建立武俠電影體系最關鍵的部分,電影中的功夫元素不單單是視覺奇觀的呈現,而是整個故事的導火索以及推動故事發展以及解決問題的關鍵,貫穿了電影事件的始終[3]。
(三)功夫元素的敘事構建
武俠電影的內部敘事需要依賴情節發展。大部分武俠電影的敘事主題圍繞著爭霸、愛國、懲惡揚善、奪寶、復仇等方面進行敘述,這些矛盾的原因各有不同,最后采用“打斗”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情節發展思路。武俠電影中的場景是特定的,同時也決定了電影的劇情時長,通過承載所要描述的事件中的事物存在空間或活動場所,將武俠小說中虛構的空間展現出來,需要由作者選擇創作的時代、背景等,并利用“功夫”打斗來表現武打場面,依托電影技術的后期處理與加工,完美地襯托出電影作品所要表達的主題與內涵。武俠電影中的拳腳、刀槍劍戟、內力等中國武術中的關鍵部分一般作為符號象征,而接受者只有充分理解符號意義,才能真正理解武術內涵,這是一個充滿想象的過程。在大部分武俠電影中,我們總能看到以武力解決所有問題的情節。例如《臥虎藏龍》中以青冥寶劍這一兵器為敘事線索,從而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其中包括獻劍、盜劍、尋劍等。整部電影呈現出復雜的江湖時空背景,圍繞獻劍展開敘述,具有極深刻的內涵,將“臥虎藏龍”的江湖演繹得淋漓盡致,體現出了歷史故事感和人物身份感。
此外,更多武俠電影熱衷于將敘事背景設定為宮廷,重構歷史現實中真實存在的事件,或者集中一切力量對朝代進行虛擬化塑造。例如在《龍門飛甲》影片中,一開頭就將全副武裝的東廠公公形象呈現出來,在黑騎戰隊等待東廠公公處罰五軍督府的時候,刺客趙懷安從鼓樓邊跳出來,黑騎戰隊頓時就準備好了弓箭與刀槍,配合著激烈的喊殺聲、打斗聲,將影像空間范圍拉滿。大眾在接收到畫面信息之后,以自身學識為基礎加以想象、構建,再通過解碼處理就能夠迅速理解影片的意蘊。現階段華語武俠電影的敘事背景一般以民國時代為主,如《劍士柳白猿》《師父》等。《劍士柳白猿》在影片開頭講述了軍閥之間的不斷交鋒,還展示了西洋樂器、道士服、僧人、傳教士等元素,暗示了不同國家文化的區別與對峙。武俠電影所包含的特殊敘事情節需要依靠功夫元素才能構建出完整的故事背景與敘事空間,而民國時期的武術已逐漸走向沒落,以此為故事背景,一方面可以將武者的情懷融入影片敘事中,從而再現客觀歷史,另一方面可以展現武術文化精神,并將其再次發揚光大。《師父》將“天津”作為時空背景,由于當時的局勢十分動蕩,加之“天津”是武術的發揚地,因而從傳統中國里走出了一批武者來積極面對異族文化的入侵[4]。
三、華語武俠電影中功夫元素的審美表現
(一)功夫元素中的暴力美學
中國武術具有多元化表達形式,無論是真實的、詩意的,還是美感的,在弱化暴力的同時還可以呈現出一定的視覺美感。“暴力美學”的出現弱化了其中的道德教化功能,武打場面與動作設計變得更加炫目,從而顯得更加唯美且富有詩意。由于中國武術的動作樣式極為復雜,武打設計并非純粹為了視覺效果,而是應該融合故事背景、人物性格等。因此,華語武俠電影中的功夫元素在當代已經演變為一種以功夫為輔、藝術表演為主的假把式。武者所使用的兵器應充分按照實際情況進行設計,力求武打動作的真實感,進而完美詮釋故事內涵。《七劍》作為武俠電影代表,圍繞七個人物角色與七把劍展開敘事,影片中存在大量的寫實場景,給人一種凄涼之感,同時還原了矛盾沖突的真實面貌,各角色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歷經磨難,各自追尋自我價值,渴望獲得心靈的重生。此外,該影片十分重視武術絕學的呈現,強調表現武俠的實際風貌,使觀眾能夠理解身體與武器的自由意志。
(二)功夫元素中的視覺美學
例如在電影《英雄》中,以雨中決斗為特色背景,表現長空和無名兩人打斗的場面,而這也是武俠電影的主要表現手法,將琴聲、雨滴作為武打背景或參照物,可以烘托兩人功夫的速度變化之快,也適應了大眾對于武打場景的觀賞需求。現階段,視覺藝術占據著重要地位,甚至出現了“視覺凸顯性美學”一說。例如在電影《十面埋伏》中,一開頭角色就在歡快的氣氛中表演舞蹈,通過拋出衣袖的力量擊打鼓,從而進一步烘托氣氛。在此情節中,小妹其實要刺殺劉捕頭,因此融合了舞蹈、武學、刺殺等元素,這是中國武術技擊和東方民族元素的有機結合。
(三)功夫元素中的哲學思想
中國功夫不僅是外在的表達,其中還蘊含了諸多哲學思想內容,包括道家、儒家等思想,這些思想的滲透為中國武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例如,《一代宗師》中就闡述了“功夫”對于武林中人的生存之道與生存哲理的意義。葉問同宮羽田比武時并未使用刀槍,而是通過冥想作戰,而宮羽田想傳位給葉問,因為他看中的是葉問身上的謙卑與樸實。在武俠電影中,俠客的入世與出世是道家“有”與“無”哲學思想的另一種體現。俠客馳騁于江湖之中,所求的不外乎懲奸除惡、快意恩仇,此類行為背后的根本動機是對于自由和公正的追求。
四、結語
綜上所述,華語武俠電影是我國獨特的電影類型,其融入了“功夫元素”,是對于功夫元素的內涵與作用的發揮。在武俠電影的變化發展歷程中,中國功夫元素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電影創作者。此外,武俠電影作品還展現出了舞蹈美學、暴力美學以及各種特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功夫元素更加符合武俠電影的深層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