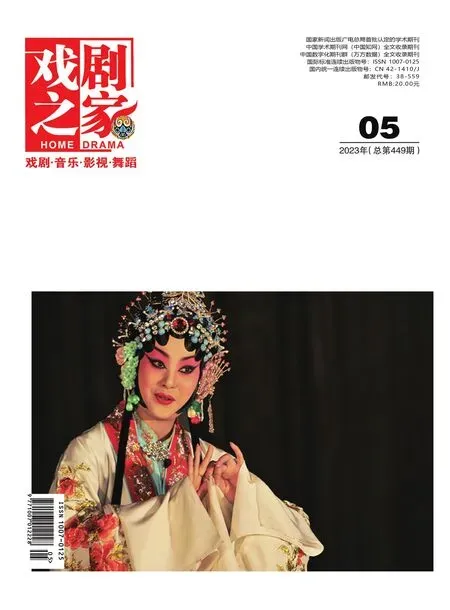古箏教學中“情景式”的表現方式分析與演奏技法探究
——以箏曲《大漠行》為例
李思靜,胡婷婷
(江漢大學 音樂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0)
《大漠行》原是唐代胡皓所作的樂府詩,詩人用強勁的筆觸描繪出大漠雄壯的美感,夾敘夾議地表現出空間的開闊和時間的久遠。曲作者將《大漠行》創作成古箏曲,把文字內涵幻化成音樂美感,豐富了這一主題的深層意義,同時讓歷史以多維形式繼續流傳。這首箏曲以阿拉伯音樂為創作基礎,中外結合,新上加新,進一步挖掘了古箏這一傳統樂器的藝術表現力,同時采用“情景式”的創作表現方式,調整了聽眾與箏曲溝通的單一性,運用通感手法,使聽眾身臨其境。《大漠行》的象征意象十分豐富,吸引了筆者對其持續關注與探索,因而筆者將主要分析這首作品如何運用情景式的表現手法,從而使更多古箏學習者能夠了解“情景式”表現手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更好地在這首箏曲及其他箏曲的演奏中予以展現。
一、作者與樂曲背景
魏軍,1947 年11 月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祖籍為山東,古箏演奏家、教育家,西安音樂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陜西箏派的代表人物,陜西秦箏學會創建人之一。
《大漠行》創作于2010 年,是曲作者根據阿拉伯音樂元素、阿拉伯民族風格特征創作的一首古箏獨奏曲。樂曲以充滿阿拉伯民族特色的旋律將聽眾帶入茫茫大漠中,并描繪出了阿拉伯人民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
《大漠行》是曲作者創作的三部組曲中的其中一首。這首樂曲的創作動機是曲作者曾聽到的一段阿拉伯音樂,這段音樂的風格非常新穎,與我們所熟悉的中國五聲調式、西方的調性調式都不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曲作者就將這段音樂元素作為箏曲《大漠行》的音樂動機。在音樂創作中,曲作者想起年輕時看過的《一千零一夜》《葉塞尼亞》等小說和影視作品,這些作品所描寫的吉普賽人對生活的熱情和對自由、浪漫的向往都帶給曲作者很大的觸動。于是他將這些畫面和人物形象一并寫進了《大漠行》中,如此便增強了樂曲的音樂感染力,使聽眾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
二、教學中“情景式”演奏技法的處理
(一)定弦
這首樂曲在定弦上沒有運用古箏傳統的五聲音階,而是采用了21 弦制的七聲音階。(見譜例1)在樂曲演奏到89—90 小節時,演奏者需要在演奏中移碼轉調,將小字一組的還原fa 與降ti 轉至升fa 與還原ti。
譜例1:

(二)樂曲結構
這首樂曲的結構可以被分為五個部分,包括引子和尾聲。引子:1—13 小節;第二部分:14—53 小節;第三部分:54—101 小節;第四部分:102—173 小節;尾聲:174—182 小節。
(三)樂曲中“情景式”的演奏技法
這是一首具有阿拉伯民族音樂風格特征的樂曲,樂曲引子開頭由四組琶音組成,加上自由的節奏,描繪出一幅茫茫大漠圖。在樂曲的引子部分出現了“∽”(見譜例2),這個記號在古箏的記譜中被稱為回滑音。回滑音分為上回滑音和下轉滑音,彈奏方式是右手先撥弦,然后左手將弦按到標準音位,最后讓其回到本音。“阿拉伯音樂的滑音獨具特色,使人聽了以后產生共鳴。”在這首箏曲里,曲作者大量使用回滑音,模仿阿拉伯民族音樂中哀傷憂愁的音樂情緒。
譜例2:

對于阿拉伯人民來說,長期生活在寬廣的沙漠中,這使得他們的生活節奏十分緩慢。所以在阿拉伯音樂中,長曲長調成為其一大特色。(見譜例2)右手的旋律都是二度進行的音程,左手連續的三連音體現出阿拉伯音樂中長曲長調的單一性特點,給人的感覺就像是走在茫茫的沙漠中,享受這里緩慢的一切,似乎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
行板開頭的右手部分在彈奏中強拍弱拍結合,左手用小拇指勾彈出渾厚的低音,加上中音區清脆短促的短琶音,模擬打擊樂的節奏,讓樂曲開頭的旋律具有了舞蹈性和律動性。第48—53 小節中出現了本曲的一個技法難點:雙手搖指,左右手旋律同時進行,左右手搖指的頻率要統一。運用雙手搖指這一古箏技法既拓展了樂曲技術的表現空間,又增強了該曲的音樂表現力。
93—101 小節是樂曲極具特色的第三樂段(見譜例3)。此段運用了效果型演奏技法,模擬打擊樂的音效。演奏方式為先拍擊琴弦和琴碼的左側,接著一個八分音符用手掌拍擊琴蓋,之后左右手交替用手掌拍擊琴弦、琴蓋以及握拳叩擊琴蓋,并將掃弦和用指甲輪刮琴蓋結合在一起,最后三小節左手用小拇指勾彈第21 弦,右手按節奏拍擊琴蓋及其側面,在一個小節之后右手變化為用指甲輪刮琴蓋,最后用左手大指與食指義甲捏住第21 弦分別向手臂內外側快速反復刮弦。這一樂段將箏與打擊樂完美結合在一起,將音樂推向了高潮,產生鮮明的節奏感,使樂曲的層次感、動力感得到增強。
譜例3

轉調后的旋律較之前的旋律更加明亮。這一段旋律在技法上運用了大量的十六分音符,密集的音符結合明亮的旋律走向,使聽者似乎看到了熱情的載歌載舞的阿拉伯人民。167—173 小節,右手在勾、托、抹三指交替的指法中快速演奏,左手使用大撮伴奏。第174 小節至最后一小節為樂曲的尾聲部分。右手強烈的搖指配合左手刮奏,全曲結束。
三、箏曲中“情景式”的表現方式
(一)聽覺感染力
這首樂曲的引子節奏十分自由,使箏曲在一開始就體現出了作品整體的音樂風格與魅力。
樂曲在行板的開頭使用了單拍子與復拍子的律動轉換。第二樂段在速度上的提升和附點節奏的大量使用使得音樂更加具有律動性。第三樂段延續第二樂段的速度,并吸收了阿拉伯音樂長曲長調的特征。三連音和附點的運用讓節奏變得更加歡快,讓人感受到阿拉伯人民積極熱情的民族形象。連接部節奏較自由,最后由弱漸強的刮奏引出了樂曲的第二部分。
樂曲的第二部分為熱情的快板。節奏復雜多變,并且要實現自然干凈的轉換銜接。這一段運用了大量的四十六節奏,使音樂更加具有律動性,并表現出了阿拉伯人民積極豪爽的性格。93—101 小節模擬打擊樂音效,用拍板的方式將箏與打擊樂完美結合在一起,產生鮮明的節奏感,使樂曲的層次感、動力感得到增強,并將音樂推向了高潮。
樂曲的第三部分與之前的音樂素材比較相似,左手的節奏類似打擊樂,并運用大量的十六分音符,使樂曲節奏變得更為緊湊,仿佛讓人看到了阿拉伯人民載歌載舞的畫面。
尾聲與開頭相呼應,右手節奏自由強烈的搖指配合左手刮奏,全曲結束。
(二)視覺表現力
在演奏箏曲《大漠行》時,演奏中的情感表達對于作品表現出的意境和藝術效果的塑造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在演奏時不僅要掌握精湛的技法,也應該具備肢體語言表現力,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將整首箏曲所營造的音樂意境表達出來,聽眾既可以得到聽覺享受,在視覺上也會產生更加強烈的代入感。
在引子部分,曲作者描繪出了一片茫茫的大漠,我們在演奏時應當注意呼吸和氣口問題,不能著急,氣口要留得充足一些。在行板部分,節奏逐漸變得歡快,我們在肢體上也要隨著節奏和旋律的變化而予以展現,使得整個部分具有舞蹈性和律動性。對于快板部分,雖然我們在演奏技法上需要多加注意,但是在一些重音點上的肢體語言也不能夠被忽略,特別是其中的拍板樂段,要模仿打擊樂的音效,在演奏時一定要突出打擊樂的拍打方式。結尾時也要注意演奏者的肢體動作,不能過于慌張,氣口一定要給足。
因此,演奏者在演奏中需要注重對肢體語言的運用,這樣才能更充分有效地實現情感的傳遞,讓觀眾走進整首樂曲所營造的畫面中并產生情感共鳴。
四、結語
西安音樂學院魏軍教授創作的箏曲《大漠行》使用人工調式的定弦方式,打破了傳統五聲音階調式,并且運用了阿拉伯民族音樂元素,在定弦方式、演奏技法、節奏處理、箏曲意境上都進一步挖掘了古箏這一傳統樂器的藝術表現力,同時也采用了“情景式”的創作表現方式,調整了聽眾與箏曲溝通的單一性。
本文分別從箏曲《大漠行》的背景及樂曲的創作、作品的演奏技法和樂曲中“情景式”的體現這三個方面論述了古箏作品《大漠行》中使用“情景式”的表現手法的獨到之處,并通過聽覺感染力和視覺表現力這兩方面深刻認識到“情景式”表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更好地在古箏演奏中予以展現。
筆者希望通過對箏曲《大漠行》中“情景式”的表現方式與演奏技法分析,使古箏演奏者在演奏“情景式”的古箏作品能夠更好地把握與理解,并對《大漠行》這首中外結合的現代箏曲產生更深刻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