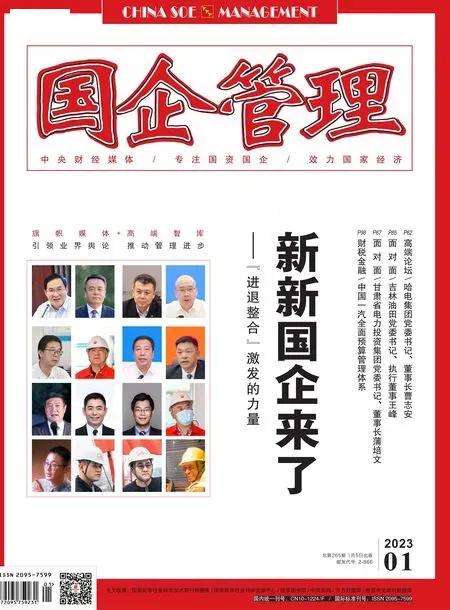農場歲月
文/常建軍
那是一九八五年,我隨父母搬到了勝利油田二分場。
二分場,是油田為安置職工家屬設置的農業點。當時,油田每個二級單位都有農業點,都有著工農村、豐收村、稻香村等不同的稱謂。這些名稱無不散發著濃濃的農村氣息,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這里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村,但有著和農村一樣的生活方式。職工們坐上班車,到油田上班。家屬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間地頭不辭辛苦地勞作著。
初到農場,我們一家人都有著諸多的不習慣。沒有油田基地的繁華,不通公交車,出行也極不方便。逢年過節,置辦年貨,就要到幾公里外的集市上采購。
再多的不適應,生活還是要繼續的。父親找來磚頭和水泥,圍起了院墻,搭起了涼棚。母親開辟菜地,種上茄子、辣椒、西紅柿。一番收拾下來,生活氣息漸漸濃郁了起來。
無論是春種夏長,還是秋收冬藏,都要跟著節氣走。春日里,翻地播種,引水灌溉。炎炎夏日,冒著酷暑,除草施肥。金秋時節,又要翻曬糧食,人抬肩扛,顆粒歸倉。寒冬時節,短暫休整,為來年做好準備。
有一年夏天,玉米長到一人多高,將田地擋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人在里面彎腰施肥拔草,悶熱難耐,不一會兒全身就得濕透。稍不注意,身上還會被葉子劃出道道血痕,汗水一出,那叫一個生疼。
母親對我說:“明天你幫我去拔拔草吧!”當時的我,正是貪玩的年紀,本想拒絕,又怕母親責怪,就極不情愿地跟著去了。起初,我學著母親的樣子,蹲在地上干了起來。隨著氣溫升高,看著望不到頭的玉米地,我索性一屁股坐下,哭了起來。
聽到哭聲,母親走了過來,看著我賭氣踢倒的玉米,本想責罵,但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你不愿意干,就回去吧!”說著,撿起草帽,給我戴上,接著又轉身繼續忙碌。我也止住了哭泣,從模糊的眼睛里,看到母親不斷抹著眼睛,我知道,母親也哭了。時隔多年,每每想起,自責萬分,后悔當時少不懂事,體諒不到母親的辛苦。

八月末,玉米成熟,母親和其他家屬要將玉米掰下,也稱“掰棒子”,再用包袱背到地頭。如此往復,直至將玉米掰完。接下來,就要將玉米運到場院,進行晾曬,再將玉米脫粒,裝進麻袋。半人高的麻袋,幾千斤的玉米,裝完卡車,母親早已累得直不起腰,她的腰病就是在當時落下的。
夕陽西下,結束勞作,算是難得的輕松時刻,母親和伙伴們,三三兩兩,結伴而行,汗水在晚風中漸干,疲憊在笑聲中消解。落日、晚風、笑臉構成了一幅最美的畫面。
一九八九年,是搬到農場的第四個年頭。母親用汗水浸潤著年輪,用堅韌訴說著歲月,不服輸、不懊惱、不抱怨。“準備準備搬家吧!咱們要搬到采油廠駐地了”,一日,父親一回到家就帶來了搬家的好消息。聽說要搬家,心中竟然有著幾分不舍。從剛來時的不適應,漸漸喜歡上這里的田園生活,習慣了這里的清晨黃昏。聽父親說,搬家后母親就不用從事農業勞動了,心里情不自禁地感到高興,也沖淡了那份不舍。
后來才知道,搬家是因為勝利油田東營地區的采油單位分為三個采油廠,分到不同采油廠的職工要搬往屬于自己的單位駐地,家屬自然也要跟著搬遷。隨著時代更迭、經濟發展,勝利油田體制悄然改變,農業點也完成了歷史使命。
家屬職工,在將近三十年的時光里,伴隨著油田的發展,見證了歲月的變遷,油田功勛簿上有她們的名字。如今,和母親年紀相仿的阿姨們,大多進入了古稀之年,她們的子女,已經成為建設勝利油田的主力軍,為打造百年勝利油田接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