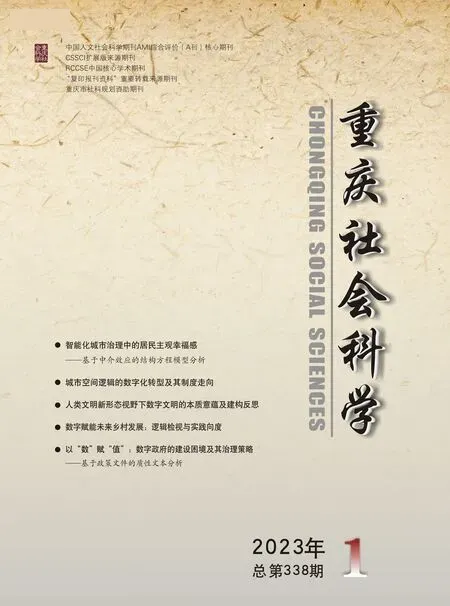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觀幸福感
——基于中介效應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劉 瑋 柳婉睿
(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
數字技術的發展正深刻影響著城市治理的革新。黨的二十大提出,要不斷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當前,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正悄然開啟一場時代變革,人類社會逐步走進數字化轉型的第三階段, 即數字技術對政府和治理的變革, 智能化城市治理作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城市治理體系更具系統性、整體性和全面性[1]。 智能化城市治理的價值將在改善民生、提升政務服務、應對公共問題等多個方面進一步得到激發[2]。例如,在應對公共衛生事件時,建立常態化數據監測體系,預警風險區域、找到風險人群,健康碼便是數字治疫的典型;智能政務系統利用互聯網和人臉識別技術改變傳統生活繳費方式和業務辦理方式; 遠程問診、 視頻會診和網絡掛號等智能醫療方式突破了時空限制和資源不均; 基于智能運算和共享技術的城市交通可以有效緩解道路交通壓力等。
數字技術應用于城市治理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深層次地影響著個體對社會需求的滿足感, 這種感受作為人們對生活質量的直接感知和評價, 通過幸福感表現出來,幸福感源于人類自身需求得到滿足,獲得幸福是人類生存的美好追求[3]。 城市居民對幸福的感知源自城市環境、生活便利等多方面的體驗,是城市治理效果的直接反映[4]。 人工智能時代下數字技術以新的途徑和方法改變著城市治理的形式,那么傳統治理方式轉變下的直接受眾——城市居民, 是否對智能時代的城市治理更滿意? 是否因智能化城市治理而提高了主觀幸福感? 這些問題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一、文獻回顧
城鎮化代表著地區生產力和社會文明的發展,城市建設與治理在開放的復雜巨系統[5]中經歷了多個階段,每個階段伴隨著不同的時代特征。 2008 年IBM 公司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理念后,智慧城市建設在全球掀起了一次新浪潮。 21 世紀初,中國城鎮化發展進入快速階段,機遇下的挑戰也隨即而來,城市治理問題亟待解決,此時,國外有關智慧城市的聲音和經驗開始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6]。 在技術進步和國家推動下,中國緊緊跟上了時代潮流,在數字化城市建設的基礎上不斷拓寬網絡覆蓋面和物聯網覆蓋率, 將新的數字技術應用于城市治理,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開始進入快車道[7]。 2012 年以來,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先后公布三批智慧城市試點名單,累計超過290 個城市(區、鎮)納入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區域,積極推進城市更新行動[8]。
為進一步提高城市韌性,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人工智能為導向的“社會5.0”時代逐漸興起[9]。 “智能城市”被稱為是智慧城市的高級階段,龐大的數據平臺是城市運營和管理的基站,PC 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是將站點連接起來的鏈條,海量的信息通過鏈條傳播,將兩個或是多個原本毫無關系的基站聯系起來。 而人工智能的重要作用,則是運用“聰明”的算法對信息進行處理從而作出決策[10],并分擔城市管理中一些反復又簡單的人工工作[11]。 除此之外,在“5G”的輔助[12]和人工智能的自主學習及深度學習下[13],城市治理逐漸從“離線決策”轉變為“實時在線管理”[14-15],“智能化城市治理”的概念進入了公眾視野。 智能化城市治理可以概括為利用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優勢,以優化城市管理和服務、滿足居民需求為目標[16-17],涵括城市生態、資源、經濟、民生、政務等多方面的城市治理革新[18-19]。
城市是居民生活的空間載體[20],城市治理方式的變革、生活環境的變化必然影響居民的感受[21]。 幸福感一直以來都是國際和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熱點。 幸福感可以分為主觀幸福感和客觀幸福感,前者是綜合性的心理指標[22],是評價者個人根據自身的生活狀況作出評判,后者是觀察者基于一定的評判標準,從國家、地區等宏觀層面作出主觀判斷。20 世紀50 年代,主觀幸福感進入國際學者的視野,之后的半個世紀,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的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研究,積累了豐厚的研究成果[23-24]。 然而,1974 年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幸福悖論”[25]再一次引發了學術討論的熱潮。 伊斯特林在比較研究中發現,盡管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居民幸福感卻不升反降,這一情況同樣在中國出現[26]。
隨著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深入思考,學者們對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研究范圍也不斷擴大。 國外研究中,涵蓋了地理環境、家庭因素、人際交往、收入、階層、城鄉差異等多個方面[27-29],也有學者提出城市建設、城市治理和居住環境會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30-31]。 國內對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在國家層面對“為人民謀幸福”的強調下,越來越多學者的目光聚焦于此,在國外學術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從社會支持、地理環境、經濟發展、心理層面等多個方面探究了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也有學者開始關注城市的更新發展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32-33]。 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數字技術正深刻影響著城市治理的變革,智能化城市治理成為趨勢,而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是城市發展的最終目標,兩者不論是從現實角度還是從學術貢獻層面,都具有啟發意義。
綜合國內外,盡管將城市發展與幸福感相結合的研究絡繹不絕,但或是集中于城市規劃、生態環境、社區管理等宏觀層面,或是以綜述形式描述人工智能時代下的城市治理情況。 以融入人工智能時代特征、以城市治理為視角的居民主觀幸福感實證研究尚為稀少。 因此,本文收集一手數據,通過整合相關理論模型構建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al Equation Modeling,SEM),對智能化城市治理下的居民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整合主觀幸福感理論和顧客滿意度理論,分析居民滿意度、積極情緒、消極情緒、感知質量、感知價值和主觀幸福感的內在邏輯,形成研究假設。
(一)理論框架
心理科學的發展,使得“幸福”不再局限于語言描繪,可進行量化實證。1967 年,威爾遜(Wilson)所著《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被視為幸福感研究的首部著作[24],借鑒哲學中快樂論所述觀點,心理學領域逐漸形成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理論。 初始的主觀幸福感被認為可以由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進行測量[34]。1976 年,測量主觀幸福感的第三個維度即生活滿意度由安德魯和維蒂(Andrews & Withey)提出,使SWB 理論模型得到補充和完善[35],并逐漸成為測量主觀幸福感的主流理論模型。
有關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的研究,最早形成于20 世紀60 年代的歐美國家并應用于商業領域。 顧客滿意度在商業領域的突出表現,吸引了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部門的眼球。 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推動下,發達國家政府部門開始嘗試將顧客滿意度理論引入政府管理。1989 年,世界上第一個國家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建立,即瑞典顧客滿意度指數。 隨后,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多個國家相繼建立起適合本國國情的公眾滿意度指數。 目前,較為成熟且具有代表性的公眾滿意度指數測量模型有美國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歐洲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以及清華大學2001 年提出的中國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36]。 綜合各類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來看,雖有所不同,但核心大都集中在感知質量、感知價值、顧客期望和滿意度方面。
考慮到顧客期望與情緒之間存在正向的相互影響關系[37],剔除重復無用因素,本文對SWB 理論模型和CSI 理論模型的核心概念及關系結構進行整合(圖1),以揭示智能化城市治理與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圖1 SWB 理論和CSI 理論整合模型
(二)研究假設
滿意度指個人對生活總體狀況和生活質量的體驗感受及評估[38],在學術研究領域應用廣泛, 常被看成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關鍵指標。 智能化城市治理下的居民滿意度體現為居民對智能技術應用于生活的感受。 近年的研究中,主觀幸福感多被認為由滿意度、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構成,滿意度正向影響主觀幸福感[39]。 據此,本文在居民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方面提出以下假設:
H1:居民滿意度顯著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
感知質量指居民在切身感受智能化城市治理后對其服務質量的綜合評價。 感知價值指居民參與智能化城市治理、使用城市治理中智能產品后,對獲得收益和付出成本的主觀評判。 普遍認為,居民感知質量越高,說明居民對此項服務的綜合評價越高,總體滿意度越高。居民感知質量提高時, 居民的收獲感越強,感知價值也隨之提高[40]。 據此,本文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質量(以下簡稱智能質量)、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價值(以下簡稱智能價值)和滿意度方面提出以下假設:
H2:居民感知智能質量顯著影響居民滿意度;
H3:居民感知智能質量顯著影響居民感知智能價值。
智能化改革在城市治理中的應用,不僅表現為將智能產品融入城市建設,改善居民生活環境,還體現在居民可以通過智能產品辦理個人業務、參與政民互動。 例如,通過App 辦理社保、生活繳費、參與監管、發表建議等。 對智能城市治理的便利感、辦事效率感、獲得價值感等評價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公眾的滿意度[41]。 據此,本文在居民感知智能價值和居民滿意度方面提出以下假設:
H4:居民感知智能價值顯著影響居民滿意度。
情緒,是人的一種心理感受,是基于對客觀事物的感知而產生的心理活動。 積極和消極是情緒中兩種最明顯的心理反應。 積極情緒作為樂觀的人格特征,表示對未來的期許、敢于挑戰生活的壓力以及對目標的持續追求。 消極情緒作為積極情緒的對立面,有著憂愁、痛苦、恐懼等特征。 學者研究發現,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可以很好地預測個人的幸福水平,并且與幸福感有顯著的相關性。 積極情緒有助于提升個人幸福感,消極情緒則不利于提升心理幸福水平[42]。據此,本文在城市居民的情緒感知和主觀幸福感方面作出如下假設:
H5: 居民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積極情緒顯著正向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
H6: 居民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的消極情緒顯著負向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
綜合感知智能質量、感知智能價值、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四者之間的關系,厘清主觀幸福感的形成路徑。 感知智能質量和感知智能價值會影響個體滿意度,感知智能質量同時影響感知智能價值,而滿意度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組成因素,據此,本文就中介效應提出如下假設:
H7:滿意度在感知智能質量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H8:滿意度在感知智能價值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H9:感知智能價值和滿意度共同在感知智能質量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綜合上述理論和假設,構建出智能城市治理下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整合模型(圖2)。

圖2 SWB 理論和CSI 理論整合模型假設路線
三、研究設計
根據本文的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選取指標變量、收集樣本數據,探尋智能化城市治理下的居民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
(一)問卷設計與指標選取
本文采用問卷調查收集一手數據,在參考相關書籍和文獻的基礎上,通過咨詢專家和預先測試完善問卷,形成最終問卷量表。 問卷整體包括標題、調查目的、智能化城市治理的含義并舉例說明、問題主體。 問題設計均采用Likert 5 級量表,即1、2、3、4、5 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感覺、同意、非常同意”。
在前文理論和假設的基礎上,共設置6 個潛變量和24 個觀測變量,潛變量為幸福感、積極情緒、消極情緒、滿意度、感知智能質量和感知智能價值。 觀測變量設計及題量參考其他學者研究確定(表1)。 其中,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觀測變量借鑒由Wosen 編制的積極情感/消極情感量表(PANAS)。

表1 人工智能時代城市治理居民幸福感指標體系表
(二)數據收集與樣本
考慮到智能城市是以智慧城市為基礎的更高級形態,本次問卷調查以湖南省進入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的19 個地區為調查范圍,以城市居民為調查對象,采取現場發放問卷和線上收集問卷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簡單隨機抽樣,調查時間為2019 年11 月—2020 年1 月。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600 份,回收有效問卷527 份,問卷有效率為87.83%。 其中,女性占55.79%,男性占44.21%,年齡主要集中在19~50 歲,占比為67.36%,高中(中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85.77%。 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總體感到幸福的人數占比為55.60%;和沒有實現智能化治理的城市居民相比,感到幸福的人數百分比較未感到幸福的人數百分比多31.49%;與過去相比,對智能化城市治理幸福感提升的人數占比為52.56%,具體樣本信息統計如表2。

表2 樣本基本信息統計表
四、實證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假設,以收集樣本數據為支撐,通過信度檢驗、效度檢驗和模型擬合檢驗,檢測調查問卷的可靠性、有效性和科學性,進一步測量潛變量路徑系數及中介作用,分析潛變量之間的關系。
(一)信度與效度檢驗
信度檢驗和效度檢驗是評價問卷指標科學性的必要步驟,本文采用AMOS 21.0 軟件及SPSS 20.0 軟件檢驗模型信效度。 信度檢驗包括非標準化參數顯著性估計值、標準化因素負荷量、題目信度(SMC)、Cronbach's α 系數及CR 值代表的組成信度。 一般認為,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大于0.6 為可接受,題目信度(SMC)大于0.36 為可接受,Cronbach's α 系數和CR 值大于0.7 為可接受、大于0.8 為良好。 由表3 可知,模型信度均符合要求,題目顯著,總體樣本Cronbach's α 系數為0.85,表示從總體上、構面上及題目上看,信度檢驗均達到良好。
效度檢驗包括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收斂效度指同一構面觀測指標結果的相似程度,用平均方差萃取率(AVE)表示,通常認為平均方差萃取率(AVE)大于0.5 為可接受,代表構面有足夠的內部一致性。 區別效度指不同構面觀測指標的顯著差異性,各變量相關系數小于其AVE 的平方根代表區別效度較好。 如表3 和表4 所示,問卷收斂效度均大于0.5,區別效度基本符合要求,表示問卷通過效度檢驗。 綜合信度檢驗和效度檢驗, 問卷模型具有不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表3 問卷信度與收斂效度

表4 問卷區別效度
(二)模型擬合、路徑系數與中介效應
信、效度檢驗后,進行模型擬合度檢驗,模型擬合度代表參數估計能反映實際問題的高低程度,即預測結果對實際情況的吻合程度。 擬合結果如表5 所示,絕對擬合指數即卡方統計量比自由度,擬合值為2.817,小于推薦值3;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小于0.08 為可接受,越小表示擬合度越高;比較擬合指數(CFI)、增量擬合指數(IFI)、擬合優度指數(GFI)、調整后擬合優度指數(AGFI)、規范擬合指數(NFI)大于0.8 為可接受,越接近1 擬合度越好。 綜合來看,各項指標均在推薦值范圍內,表示模型擬合度良好。

表5 模型擬合結果
基于以上模型信度檢驗、效度檢驗及擬合檢驗均符合要求,研究繼續利用AMOS 21.0 軟件測量潛變量路徑系數,結構方程模型路徑結果如圖3、表6 所示。 由表6 結構方程模型假設檢驗結果可知,有關智能化城市治理居民幸福感的6 個假設均為顯著,假設路徑H1、H2、H3、H4、H5、H6 得到驗證。 由路徑系數可知,滿意度、積極情緒對幸福感有直接的正向影響,消極情緒對幸福感有直接的負向影響,感知智能質量與感知智能價值對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

表6 結構方程模型假設檢驗結果

圖3 標準化系路徑系數
巴倫和肯尼(Baron & Kenny)在1986 年提出逐步法[47]進行中介效應的檢驗,奠定了中介檢驗方法的基礎。 麥金農(Mackinnon)提出bootstrap 法[48],重新估計中介效應的標準誤及信賴區間,計算中介效應的顯著水平(Z 值),彌補了逐步法、Sobel test 等中介檢驗方法存在的局限,也可應用于多重中介模型檢驗[49],是目前使用更為前沿的方法。 利用AMOS 21.0 軟件執行bootstrap 5 000次得出檢驗結果,如表7。由表7 可見,總中介效應為0.494,中介效應的Z 值均大于|1.96|,Bias-Corrected置信區間與Percentile 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假設路徑中的中介效應顯著存在,H7、H8、H9 得到證實。 滿意度在感知智能質量、感知智能價值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到多重中介作用。

表7 中介效應
五、結論與建議
在整合CSI 滿意度理論模型和SWB 主觀幸福感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構建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研究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城市治理融入智能后的居民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模型信度、效度均達到要求,整體擬合情況較好。 研究發現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總體感到幸福的居民百分比比未感到幸福的居民百分比多40.23%,相比過去而言,幸福感有所提升的人數占52.56%。 滿意度、感知智能質量、感知智能價值和情緒對主觀幸福感都有顯著影響,具體如下:
第一,居民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的滿意度是直接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路徑系數為0.615,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H1 得到驗證。 在智能城市建設中,居民對智能政務、智能醫療、智能教育、智能交通、智能社區等城市治理方式的滿意度正向影響居民的主觀幸福感,這與以往有關城市治理與幸福感關系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50]。 滿意度和幸福感都是對現有生活質量的評價和心理感受的表達,二者來源相近、受影響因素相似,因此,二者的關系更加密切,居民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的滿意度直接決定了居民的幸福體驗。
第二,感知智能質量和感知智能價值直接影響居民滿意度,通過滿意度的中介作用進一步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 感知智能質量(路徑系數為0.453)對居民滿意度的影響稍高于感知智能價值(路徑系數為0.417),且感知智能質量對感知智能價值的影響較大(路徑系數為0.581),三條路徑均為顯著,H2、H3 和H4 得到驗證。 高質量的城市管理可以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和更優質的服務,居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獲得感提高,感知利用智能方式進行城市治理的評價也越高,即感知價值增長。居民對城市治理質量、城市治理價值提升的認可將提高居民的生活滿意度。
第三,情緒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直接原因,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對幸福體驗的影響存在差異,積極情緒(路徑系數為0.354)相比消極情緒(路徑系數為-0.278)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更加強烈。積極情緒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幸福感,而消極情緒則會降低居民幸福感,H5和H6 都達到1%的顯著水平以上,假設得到驗證,這與以往有關情緒與幸福感的研究結論一致[51]。 積極的情緒使個體對未來抱有美好的期待,對新事物予以嘗試和接納,這類情緒和意愿可以有效地幫助個體適應新的城市治理方式,也有利于增強個體在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生活質量提高帶來的幸福感。 而消極的情緒會讓人因傳統生活方式改變而產生厭惡和排斥,導致個體難以適應,因此,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的消極情緒會減少居民的幸福體驗。
在國家不斷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數字技術融入并應用于城市治理成為時代浪潮。 本文以人工智能時代為背景,研究智能化城市治理與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并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提升智能技術水平,優化體驗增幸福。 首先,數字技術是城市治理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也是城市治理中各類智能服務產品的基石。 智能技術的便捷優化程度決定了使用者的使用意愿和滿意程度。 因此,總體上要不斷提高智能化水平,充分利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醫療、教育、社區服務等居民生活需求更大范圍地融合,“技術過得關,技術應用范圍廣”才能提高公共服務質量。 其次,智能化城市治理以城市為載體,以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 因此,在更新和改進技術時,要始終堅持“不忘初心,以人為本”,以如何真正便利居民生活、合理利用城市資源、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真正實現精細化、動態化管理。 再次,智能應用于城市治理體現在信息龐大復雜的數字世界中,也會體現在物理世界的智能產品上,因此產品體驗是關鍵。 產品的使用感會直接影響居民滿意度,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提高產品易用性,對于涉及居民隱私的智能產品,如監控、信息追蹤,則要在提高質量的基礎上提升友好度和安全感。 持續提升智能化城市治理服務產品質量和體驗感,全面提高居民智能化城市治理的滿意度。
第二,完善引導機制,提升居民技術滿意度。 首先,完善宣傳引導機制,是營造良好氛圍的重要一步。可以通過網絡科普等方式,讓居民了解智能技術應用于城市治理的益處。 以對未來生活美好的期待增強對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積極性, 使居民在面對城市治理從傳統轉向智能時,更愿意接受和嘗試。 其次,由于居民的技術使用感受是居民幸福感的直接來源,因此,要加快智能化城市治理數字化轉型,加強基層治理智慧化水平,通過智能應用場景的建設,使居民體驗到智能化帶來的便利,滿足居民需求,從而精準地解決城市治理難題,提升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