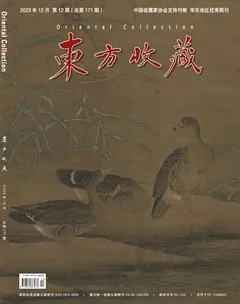對新時代戲曲文物保護傳承的思考
摘要:山西省長子縣文化底蘊深厚,能為“文化發聲”的文物古跡恒河沙數。其中,長子縣下霍護國靈貺王廟作為該縣保存較好的古建筑之一,成為我們研究當地信仰及演劇活動的歷史見證。古戲臺是研究神廟劇場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作為觀演場所的古戲臺,不僅說明了戲曲演員與民眾之間的觀演關系,更表現出了傳統戲曲的藝術形態。文章以長子縣丹朱鎮下霍護國靈貺王廟為例,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運用民俗學等學科相關知識,探析其產生的民間信仰、形成發展的建筑特色,以及神廟與戲臺間衍生的禮樂觀,期以此在城鄉建設中能夠加強對戲曲文物所承載的文化的保護和傳承。
關鍵詞:長子縣下霍村;神廟劇場;三嵕信仰;文物保護
長子縣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博大精深,享有“精衛之鄉、丹朱封地”的美譽。其“丹朱封地”之名源于堯帝的長子丹朱在此受封,故得縣名。下霍護國靈貺王廟位于長子縣丹朱鎮下霍村村南的白云山上,始建于金明昌五年(1194),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重修,現存正殿為金代遺構。下霍護國靈貺王廟自南向北依次為山門戲臺、廊房、側殿、獻殿、正殿及其耳房,其規制完整、布局和諧,是長子縣護國靈貺王廟保存較為完整的一座,反映了金元以來長子地區地方神靈信仰和祭祀的繁盛。國務院在2013年3月5日公布該廟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保護范圍以下霍護國靈貺王廟圍墻為界,東、西、北各至大殿外30米;建設控制地帶以保護范圍為界,向南延伸300米,向東延伸150米,向西延伸50米,向北延伸100米。此外,長子戲校也在此創立,形成了濃厚的戲曲氛圍,為當地培養了無數的戲曲棟梁。
一、神廟劇場視角下的三嵕信仰
(一)信仰之源
護國靈貺王廟,俗稱羿神廟、三嵕廟,從而衍生出三嵕信仰,在正殿主要祭祀的神靈為羿。對于羿的身份界定,學界的看法不一、褒貶不一,但無論說法有何不同,其共同點都是“以善射而聞名”。有關羿最早的神話記載,見《管子·形勢解》中的“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描述了在古時羿就冠有“擅長射箭”的名號,可穩穩地握著弓箭,并有調節弓箭的力量,能防守也能攻擊,且操弓射箭時能夠百發百中。之后的古籍文獻也大多記載了羿的善射技能,如《楚辭》的“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還有《荀子·儒效篇》的“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在這些典籍中,羿都是以善射者的身份出現。從古籍文獻中可知,在堯時,十只三足烏搶著上天遨游并吐出強烈火焰,植物都因太陽(吐出來的火焰)曬得干枯而死,河水干涸,炎熱無比,眾生皆苦。于是,帝堯命令羿將其射下,羿一下就射掉了九只三足烏,瞬間火氣全無、清涼無比,萬物由此復蘇,天下蒼生得以生存。《淮南子》中有“堯乃使羿射九烏于三嵕之上”的記載,《大明一統志》則記載三嵕山位于長治市屯留縣內。羿憑借自己高超的射日本領,解除了旱災,在正統思想的影響下,百姓自然而然地將他作為保護地方的大英雄,為此將羿譽為“三嵕之神”。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羿被封為“靈貺王”,這正是護國靈貺王廟也被稱為三嵕廟的原因。為祭拜這位英雄,朝廷在每年的六月初六都會派專人到三嵕山為羿舉行宏大的祭祀儀式。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百姓祭祀的過程中,這位有射日本領的羿神卻被百姓當成水神來祭拜,祈求雨水充盈并賦予他司雹的職能。羿從民族神話中的英雄轉變為民間神祇,最后轉型為地方性水神,并產生和發展成為晉東南地區獨特的三嵕信仰文化。
(二)射神向水神轉變
晉東南屬溫帶季風區,略帶大陸性特征,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并由于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春旱現象頻發,旱澇災害處于兩個極端。在科技、信息尚不發達的年代,自然環境對農業播種和食物采摘具有很大影響,因此靠天吃飯的百姓只能將對于雨水的需求寄托在神靈身上,這也是射神向水神功能轉化的因素之一,于是祈求風調雨順、旱澇保收是當地神靈主要的功能。除了旱澇,雹災的出現也不容忽視,由于晉東南地區夏季雨水較多,產生強對流空氣,與空中的水汽結合形成冰雹,直接對農作物生長和百姓生活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在長子縣內,三嵕廟的數量是多于其他廟宇的,這與當地的自然災害有著直接關聯。面對這樣無情的災害,無計可施的古人只能將美好愿景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之上。相對于普遍化的神靈,地方獨有的羿神更能走進百姓心中,并將“致雨司雹”專屬職能賦予給這位“三嵕之神”,所以當地羿神身兼數職,這也為其轉化為水神奠定又一基礎。總而言之,人地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信仰提供了最基本的自然根源,對于羿射日,百姓認為其既能射日也必能除旱,這也為羿轉化為水神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神話傳說與民間信仰彼此聯系、彼此相依,富有傳奇色彩的神話傳說在人們耳畔中流傳,便一定程度上在人們的腦海中形成了初步的神靈形象和觀念。筆者在考察的過程中,發現在下霍護國靈貺王廟正殿北側墻壁上就繪有羿射蛟龍的圖畫。
三嵕廟建筑群作為三嵕信仰的載體,表現出的是民眾信仰的凝聚力,這種無形的力量維系著廟宇與地方、民眾、神靈。三嵕廟作為關系媒介,將村中百姓與神靈相連,從祭祀空間進而轉向民神共處空間。宋代之后,祀拜神靈的儀式活動獲得封建統治階級的支持和推廣,在晉東南地區廣泛并快速傳播,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成熟的信仰體系。
二、下霍護國靈貺王廟神廟劇場的建筑形制
下霍護國靈貺王廟的院落坐北面南(圖1),中軸線上存山門戲臺、獻殿與正殿,整體呈二進四合院形制。正殿供奉羿和嫦娥二神。獻殿東側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重修碑記》和康熙五十六年(1717)《重修白云山神廟碑記》兩通壁碑,以及清光緒十二年(1886)《白云山禁止票傳支戲碑記》一通。據前述《重修碑記》記載,中軸線上現存的正殿為金代遺構,清代重修。
正殿為懸山頂且為單檐建筑,并有琉璃脊飾,建在高為1.2米的臺基上。殿身面闊五楹,通寬11.06米,明間2.45米,進深七椽,為7.06米,廊深2.8米,通高9.1米。第一層架為五架梁并雙步梁,雙步梁呈前出昂形式;第二層為五架梁上置三架梁,中間置有雙蜀柱和叉手承托頂層的脊檁,檐柱上置額枋,額枋上再置普柏枋,普柏枋上置櫨斗,櫨斗上置三跳斗拱,其中第二跳和第三跳作假昂形狀。正殿前東西兩側山墻上有浮雕,為風、雨、雷、電四神像。在正殿內的兩側山墻上繪有彩色圖畫,其表現內容是護國靈貺王正在行云布雨。正殿兩側各有耳房五楹,臺基高0.09米,硬山頂建筑,灰脊筒瓦鋪就,面闊15.34米,進深3.51米,通高5.57米,柱礎高0.09米,呈素覆盆柱礎,前有垂帶式臺階,基高0.64米。
獻殿為六檁卷棚建筑,面闊五楹,長12.72米,進深5.54米,通高6.07米,梁架為五椽栿搭三椽栿,頂瓜柱上承托羅鍋椽,斗拱為一斗二升交麻葉。前有垂帶式臺階,基高1.18米。東西山墻上塑有浮雕,其中東側山墻浮雕內容為后羿射日,西側山墻浮雕內容為嫦娥奔月。
戲臺與正殿遙遙相對,坐南朝北,為懸山頂建筑(圖2)。戲臺為五架梁結構,戲臺下方以高為2.72米的過路臺為臺基,戲臺上方面闊五楹,長13.11米,通進深5.50米,明間3.28米,通高5.11米,臺口高為2.33米,戲臺中有屏風將其分為前后臺,后臺進深1.13米。戲臺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而是從它身上我們能夠聯想到曾經作為演出場所的熱鬧和祭拜儀式的莊嚴性,感受到千年文化所賦予戲臺的文化魅力,體驗到戲曲文化在千百年歷史洪流中的璀璨光輝。戲臺使神靈與民眾生活更加密切,在所有的戲曲娛樂和祭神活動中,百姓們都積極響應參與,使戲臺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公共場所,極大地填補了民眾娛樂生活的空缺,豐富了民眾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體現了強烈的集體認同和公共意識。
三、神廟戲臺
戲曲文化之所以能夠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成為經典、國粹,除了其自身的生命力外,最重要的是神廟戲臺作為重要載體,與戲曲表演相輔相成地呈現在大眾面前。戲曲最初的功能是為娛樂神靈,所以在建造廟宇時,人們為了尊敬神靈,在正殿前取一塊空地進行表演,這是神廟戲臺最初的發展樣式——露臺;后考慮到天氣原因,在露臺的上方加蓋房頂,再到后來逐漸形成山門戲臺或戲臺在廟宇外的樣式。廟宇是祀拜神靈而建的空間載體,神廟戲臺也已然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考察戲曲的功能作用時,我們要結合其所承載的宗教屬性。而要準確認知戲臺所承載的歷史民俗文化,我們需要對戲曲表演進行探討。在我國古代,戲曲是為了尊敬神靈、娛樂神靈而表演,所以神廟戲臺的坐落位置與廟宇的位置呈相對方向。民眾將對神靈崇拜在潛移默化影響中表現出民間信仰,成為傳統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并融入我國的禮樂文化中。戲曲表演與廟宇融為一體,在敬神娛神過程中戲曲的內涵被注入了宗教化。伴隨著這種演戲獻神的宗教儀式被固定下來,戲曲的教化功能或淺或深地在戲曲藝術呈現目的上表現出來。清光緒十二年(1886)《白云山禁止票傳支戲碑記》中記載:
從來廟堂之設,原所以奉祭祀:而祭祀之道,莫先若獻諸戲……九村輪轉報賽,有獻戲兩班者,亦有獻戲三班者,盡心力而奉神,誠盛事也……每年逢賽之期,差役執票而來,假借傳喚官戲需索戲班錢文,以至于梨口等借此端倪,逢白云山寫戲,要求戲價之大,否即不來唱。則此害不已,有誤于神事呼……自今以后,不準票傳支戲。
據廟中碑記所載內容得知,神廟信仰依靠在人們心中的權威和威懾力,對獻戲百姓進行忠告和勸誡,謂之“盡心力而奉神”,否則“此害不已,有誤于神事乎”。面對神靈信仰,眾人自然而然地進行自我約束、自我管理,這種自覺的管理辦法是宗教屬性和藝術屬性相結合的體現。與戲臺相對的神殿,是宗教的延伸體,表現出“禮”,而戲臺在歷朝歷代中都被看作是娛樂的具化表現,表現為“樂”。因此,王潞偉認為“神廟中舞樓之設是禮樂觀念民間滲透的結果”。筆者在田野調查中也認為,神廟舞樓之設是神廟劇場中必不可少的禮俗配置,在其他的碑記中也有大量關于修建或重修神廟舞樓的記載,究其原因是因舞樓位置或偏或缺或小。不難看出,在關于舞樓修建中體現出的是對所祭神靈的崇敬,也是對禮樂文化禮俗的遵守。而下霍護國靈貺王廟碑記中所體現出來的也正是民眾對于禮樂觀念的接受和重視,表現出神廟戲臺的宗教和藝術在神廟劇場中和諧共生。
自三嵕廟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后,每年的農歷二月十二是下霍村舉行廟會的時間,敬神演戲的活動及精神還在經久不息地傳承和保護著。在科技水平和思想文化高速發展的今天,演戲活動已然成為老百姓的日常民俗活動,不難看出,當今時代“新潮”的禮俗文化正如雨后春筍般與民眾融合交織。
在鄉村地區,戲臺代表一個村、一個鎮乃至一個縣的信仰文化和精神源泉,同時它又是中華優秀戲曲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戲臺的地理位置、建構形制以及戲臺上所載有的舞臺題記等信息,我們可以穿越古今了解到古代的歷史和民俗活動,這對于今天的歷史學、民俗學、戲曲學和傳播學等學科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漢]韓嬰撰.韓詩外傳(詩外傳卷第五)[M].四部叢刊景明沈氏野竹齋本.
[2]車文明,王福才.中國戲曲文物志三·戲曲碑刻卷(上)[M]. 太原:三晉出版社, 2016.
[3]車文明.中國神廟劇場概說[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8(03):16-35.
[4]王潞偉.上黨神廟劇場研究[D].山西師范大學,2015.
[5]王崇恩,段恩澤.晉東南地區羿神信仰源起及神廟分布考[J].山西檔案,2015(06):23-26.
[6] 夏征農,陳至立主編.大辭海第3卷·宗教卷[M].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7]王潞偉,姚春敏.精英的尷尬與草根的狂熱:多元視野下的上黨三嵕信仰研究[J].民間文化論壇,2016(05):90-99.
[8]李婷.后羿:從民族神話中的射神到地方信俗中的水神[D].溫州大學,2017.
[9]李燕.晉東南英雄神話傳說及信仰研究[D].山西大學,2020.
作者簡介:
解雯捷(1999—),女,漢族,山西臨汾人。山西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戲劇戲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