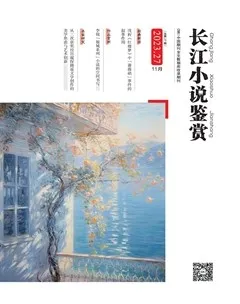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吝嗇鬼形象探析
[摘? 要] 明代小說戲曲中存在許多吝嗇鬼形象,他們視財如命,既苛待自己又苛待他人,成了不少作家集中刻畫和諷刺的對象。這些吝嗇鬼形象生動飽滿又各具特色,蘊含著特定時期的現實文化內容,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吝嗇鬼形象的形成原因有四點:一是明代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造成空前的金錢崇拜,二是傳統節儉守財經濟思想的影響,三是明朝社會的不穩定與不平衡促使吝嗇行為產生,四是作家對吝嗇鬼形象藝術性的發掘和塑造。本文試圖分析明代小說戲曲中吝嗇鬼形象的心理狀態及成因,進而對吝嗇鬼群體的形象進行價值判斷。吝嗇鬼的行為令人鄙視,但我們也應看到他們身上的可喜、可憐與可悲的一面。研究特定時期的吝嗇鬼形象對社會時代的演進仍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 明代小說? 明代戲曲? 吝嗇鬼? 成因? 價值
[中圖分類號] I207.3?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7-0007-04
一、吝嗇字源釋義
“吝”,形聲字,從口,文聲。《說文解字》:“吝,恨惜也。”其本義指遺憾、悔恨。后引申指吝惜、吝嗇義。《說文解字》:“嗇,愛濇也。”《韓非子·解老篇》又云:“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知識也。”這里“嗇”有愛惜、節儉的含義,后來引申為吝嗇。本文所說的吝嗇鬼,是指那些既貪圖錢財又極度節儉到變態地步的人。
二、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吝嗇鬼形象綜述
1.明代小說中的吝嗇鬼形象
《醒世恒言》卷十七《張孝基陳留認舅》中塑造了過善這一儉吝人物,“田連阡陌,牛馬成群,莊房屋舍,幾十馀處,童仆廝養,不計其數。”“那后房約有兩千馀金。”[1]過善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但他對自己十分苛刻,一輩子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從來不同朋友外出游玩,也不滿足自身的口腹之欲。他把后房裝積蓄的箱籠鑰匙貼身攜帶,鑰匙一刻不離身,取東西放東西都要親自過目,一分錢都不敢多花。過善得知兒子偷錢在外揮霍,極為暴怒,連忙一頓棍棒教育。“此時銀子為重,把憐愛之情,閣過一邊。”[1]
《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則的主角張富是典型的吝嗇鬼,他家財萬貫卻吝嗇如鐵公雞:“虱子背上抽筋,鷺鷥腿上割股。古佛臉上剝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著點燈,捋松將來炒菜。”[2]小說一開頭就形象生動地描寫了張富的吝嗇特質。他還許下四個愿望:“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夢鬼交。”[2]張富因為一文不使,得了“禁魂張”的外號。“禁魂”是符咒的意思,舊時為避免財富被鬼神搬盜,須在錢庫上貼上符咒。“禁魂張”引申為守財奴張富之意。張富見有人施舍乞討的人兩文錢,馬上上前制止并施以暴力。后來,張富家中部分錢財被路見不平的宋四公盜走,自己又陷入“偷玉帶”的案情之中,最后因舍不得家財自縊而死。其悲慘結局也體現了作者對吝嗇鬼強烈的批判態度。
《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的主人公賈仁是吝嗇鬼形象中的典型。小說是這樣描述的:“雖有這樣大家私,生性慳吝苦克,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要他一貫鈔,就如挑他一條筋,別人的恨不得劈手奪將來;若要他把與人,就心疼的了不得。”[3]在買周秀才的兒子時,賈仁一直強調自己是個“財主”,實際卻虛偽吝嗇,不僅賴皮地只付一貫鈔,還反問衣食艱難的周秀才要“恩養錢”,可見其無賴狡猾。最后,賈仁落得一文不值,其養子賈長壽復了周姓,賈仁白白為周家守了二十年錢財,到頭來只是一場空。
《警世通言》卷二十五則《桂員外窮途懺悔》中的桂富五經商失敗、窮途末路時,是他兒時的好友慷慨解囊,助他擺脫危機。桂富五后來又靠私吞好友棗園中挖出的錢財發家,可在好友死后,他竟只帶了一只雞一斗酒前去悼念。當好友的孩子向他討要錢財時,桂富五只打發了他“兩錠白銀”,其貪婪吝嗇的丑惡面目躍然紙上。《警世通言》卷五中的金鐘也是雖富但吝的人,他怨恨“秋風冬雪”,因為還得費錢買衣服;他怨恨自身不吃飯就會餓,因為還得費錢買糧食;他怨恨皇帝,因為要繳納錢糧;他還怨恨家中的親朋好友,來時還得費茶費水……
明代小說中還有另一類吝嗇人物。在《醒世恒言》卷三十四《一文錢小隙鬧奇冤》中,邱長兒、再旺兩個孩子因為一文錢而爭吵打鬧,引發了楊氏和孫氏相互罵街,到故事結尾竟因此事斷送了十三條性命。這類人物固然吝嗇,但她們身上體現出來的,更多是人物本身眼光的狹窄和局限。
2.明代戲曲中的吝嗇鬼形象
明代沈采所作《還帶記》中的劉二頗有家資,但在自己的親姐姐需要幫扶時,劉二不僅表現冷漠,還嘲笑譏諷了姐夫。姐夫趕考需要盤纏,劉二卻想謀求姐夫準備典當的衣服。當姐夫高中,劉二又一改往日嘴臉,“盤纏少,我家盡取”表現了他的勢利和吝嗇。
《一文錢》是明代戲曲家徐復祚的代表作品,他創作了盧至這一典型的吝嗇形象。“累世仕宦,家道富饒。區宅僮牧,何止數百千;水碓膏田,不下億萬計”[4],可見其雄厚家底,但他視財如命,為錢所困,即使對待自己的家人也苛刻至極。盧至只準妻兒每日吃二合米,孩子若偷吃了李子,就會被扣去二合米。盧至害怕妻子吃自己的飯,要等妻子走后再偷偷吃。盧至總是盤算如果在外吃飯時碰上熟人就可以蹭飯,省下自己的錢;盧至在路上撿到一文錢也十分珍惜,認為將這錢攢起來就可以錢生錢,把錢藏在袖子里怕掉了,藏在巾子里怕漏了,經過漫長的心理斗爭才決定買芝麻吃。可盧至吃芝麻的時候居然因為怕芝麻被鳥叼走、被狗搶走,索性躲到人跡罕至的山林中一粒一粒地品嘗。佛祖安排假盧至散盡真盧至的家財,最后盧至被佛祖點化,才摒除了貪念,修成了正果。
三、吝嗇鬼形象的形成原因
1.明代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下的金錢崇拜
四民制度指士、農、工、商。士排第一等,農排第二等,工排第三等,商排末等。在傳統社會中,農業才是國民經濟之“本”。墨子固本的觀點是:“固本而用財,則財用足。”[5]各個朝代都推行過打壓商人的“賤商令”,“重農抑商”成了歷代統治者治國強民的指導思想。但在明代中后期,隨著商品經濟高速發展,商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逐漸提高,大量儒士由于經濟窘迫也開始經商。王陽明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企圖打破傳統的“榮宦游而恥工賈”的價值觀[6],可見四民制度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明代中后期的社會價值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從重義、貴義轉向追求和崇拜金錢,卷入“一切向錢看”的潮流中。清河縣的西門慶十分有錢,不僅在當地呼風喚雨、一手遮天,而且能與政治中心的人物攀上關系。“東京蔡太師是他干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與……”正如《金瓶梅》中所說,“世上錢財,乃是眾生腦髓,最能動人。”[7]再加上明代社會興起了一股張揚個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使得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李贄主張順從人的個性,滿足人的欲望。湯顯祖、袁宏道則肯定“情”的解放,使之與“理”相對立。因此,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不難理解吝嗇鬼為何對金錢如此貪戀。
2.受中國傳統的節儉守財思想影響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主要發展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小農經濟規模狹小,生產力低下,財富增長極為緩慢和艱難。小農經濟也叫自耕農經濟,日常經營要承受封建地主階級沉重的租稅。小農經濟一旦遇到較為嚴重的自然災害就可能顆粒無收,具有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只能通過節流來緩解。因此,早在春秋時期儒家就十分關注如何節省金錢。《尚書》有言“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左傳》也曾指出“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8]。孔子則提倡寧儉勿奢,認為“儉可養德”。儒家崇尚節儉,主張量入為出,開源節流,大至治國,小至為人的修身養性,都應該節儉有度。戰國時期墨子甚至把節儉的重要性與國家的存亡興衰相提并論,他認為:“儉則昌,逸則亡。”不僅要精打細算地消費,就連穿衣吃飯也應該做到能省就省,滿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就夠了。幾千年來,崇尚節儉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代代傳承。在明代家訓中,隨處可見要求后代節儉的家訓。周怡說:“由儉入奢易,出奢入儉難。”呂坤認為家庭興旺需靠儉:“興家兩字曰儉與勤”[9]。許多民間諺語也反映了中國人的節儉:“想拾橫財一世窮”“要想找著活財神,省吃儉用免求人”“平時省分文,用時有千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守財是為備不時之需,平時積累小錢,需要用錢時才不會茫然無措。吝嗇鬼們受到傳統節儉守財思想的影響,但沒有把握好“適度節儉”的原則,不斷病態地節儉,把積累金錢視為人生最大目標。
3.社會不穩定及經濟不平衡導致吝嗇之風
明朝初期,“靖難之役”涉及整個華北和華東地區,反復的拉鋸戰使得淮河以北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的破壞。明朝末期,政治日益腐敗黑暗,伴隨著天災人禍,社會處于極大動蕩之中。動蕩之中的百姓的經濟選擇趨于保守,經濟的保守觀念映射至文藝作品中,便涌現出諸多吝嗇鬼的形象。
在明朝,隨著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財富的積累,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根據史料記載,當時“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10]。并且,明朝官宦和地主兼并了大多數的土地,土地占有不平衡致使貧富分化更加嚴重。《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三中指出,大凡富人沒有一個不慳吝的,也正是因為他們視錢如命,所以“錢神有靈也愿意跟著他們走……若是把來不看在心上,東手接來西手去的,觸了錢神嗔怒,豈肯到他手里來?故此非慳不成富家,才是富家一定慳了。”[11]上述吝嗇鬼大部分都是足夠富有的人,這些富有的人貪婪地想要擁有更多財產,他們一方面通過控制自己的物欲節省金錢,另一方面通過壓榨克扣他人的錢財不斷積累財富。
4.作者藝術性的刻畫
這群吝嗇人物的出現,離不開作者的精心塑造和刻畫。作者在塑造這類人物時,首先觀察到金錢對人的異化。金錢對人的異化反映在人物的性格、品性上,明代小說戲曲主要以滑稽戲謔的方式對此類人物進行諷刺,具有持久的藝術魅力。
這類作品往往通過結構巧妙地塑造吝嗇鬼形象。《一文錢》共六折,前兩折直接寫盧至的吝嗇,后四折則著力描寫佛祖開化、盧至頓悟,神佛的介入使作品的思想更加深刻。六折環環相扣,銜接自然。不難發現,這些人物的吝嗇形象大多都是通過構建細節并使用夸張的藝術手法凸顯出來的。“禁魂張”要把“痰唾留著點燈”“要在佛像刮金”,因為兩文錢就對乞討的人施以暴力;盧至因為一文錢思前想后、糾結不已,買了芝麻后“逐粒吃、慢慢吃”,盧至為了防止芝麻被鳥獸叼走一路跑到山上,連連“喘氣”;劉二在外面吃酒席時,憋著屎要非要“熬到自家茅廁”。這些描寫雖有夸張之處,但卻為讀者展現了多個被金錢異化的文學形象,用幽默的筆法生動刻畫了他們的丑態。
四、吝嗇鬼形象的深層價值
1.文學價值
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吝嗇鬼形象十分生動且富有戲劇性。這些形象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吝嗇人物群像,他們的經歷和生活狀態讀來令人發笑卻又令人深思。《張孝基陳留認舅》中的過善,雖然對自己苛刻,但可以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財產囑托給女兒女婿,體現了過善對家庭的責任感。《訴窮漢暫掌別人錢,看財奴刁買冤家主》中的賈仁和《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的張富,奸詐狡猾,一文不使。他們吝嗇了一輩子,走到生命的盡頭才發現自己在金錢上的汲汲營營只是一場空,不免使人唏噓嘆惋。吝嗇鬼之所以吝嗇,與其獨特的生命體驗不無關系。做財主之前的賈仁“幼年父母雙亡,別無親眷”“有早飯沒晚飯,朝不保夕”,“每日燒地眠、炙地臥,衣不遮身,食不充口”“晚上在破瓦窯中安身”,正是因為賈仁一直過著艱辛的生活,面對大量錢財時才不知如何使用,又因為不懂使用錢財,才極度恐懼錢財的流失。對這類吝嗇鬼而言,聚斂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動力和心靈支撐。
更辛酸的是,這些人不僅沒有得到物欲的享受,精神上也緊張不安,錢財的積累并沒有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到頭不過是一場徒勞。田曉菲在《田與園之間的張力》中說:“觀眾是用不著同情一個丑角的,可以盡情嘲笑他的無知,他的笨拙。但是,這里的幽默十分脆弱,很容易就煙消云散……投下一道陰影。”[12]吝嗇鬼的丑態人盡皆知,但這種“丑的美”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它存在的意義便是使人們從中得到理性的啟發。讀者應試圖以“同情者”的目光給予吝嗇鬼群體關照,而不是一味地對其進行不留余地的批判。只有擺脫偏見,吝嗇鬼形象背后隱藏的意蘊才能日益顯現[13]。
2.現實價值
這些吝嗇鬼形象富有生活氣息,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吝嗇鬼只懂得用各種手段斂財而不顧及他人感受,自我意識濃重且缺乏集體責任感,其吝嗇行為是道德低下、無仁無義的表現,與儒家所倡導的推己及人的“仁之方”原則背道而馳。方弘靜認為:“慳,貪者也;儉,廉者也。貪則污矣,廉則善矣。不能儉,焉能廉?慳與儉,相似者也;廉與貪,則相反者也。世有以廉為辱者乎?茍以是自省焉,何避之有?”[14]他揭示了“慳”和“儉”的本質區別,并指出慳吝與貪的必然聯系。明代小說戲曲的作者創作了許多吝嗇鬼形象,并抨擊和諷刺此類人物形象,是為了警醒教育讀者不犯同樣的錯誤。對這些吝嗇鬼形象,我們不能一味地嘲笑,而要辯證地看待。現實生活中,我們要樹立正確的金錢觀,秉持“適度節儉”的原則,一味追逐利益就會變成金錢的奴隸,更不能為人刻薄、貪婪狡詐、算計他人。當然,節儉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不應摒棄。吝嗇鬼們小心謹慎地守護來之不易的財富,但卻不知如何運用財富,不知如何善待他人、回饋社會,在批判吝嗇鬼的同時,讀者必須反思并避免這樣的行為。精打細算的生活方式沒有錯,崇尚節儉的精神也體現了老一輩人對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認同。在消費主義橫行的當下,我們仍應以節儉為榮,適度消費。
五、結語
明代處于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動蕩不穩定、財產分配不平均的時代,這時一部分人選擇積累金錢,以滿足其對金錢的渴望。但他們節儉過頭、追求過頭,甚至吝嗇到了變態扭曲的程度。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吝嗇鬼形象是可鄙的,同時也有些凄涼和可悲,這些吝嗇鬼形象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還起到了警示當下的作用,我們應當從中獲得教訓并觀照現實社會。
參考文獻
[1] 馮夢龍.醒世恒言:注釋本[M].武漢:崇文書局,2015.
[2] 馮夢龍.喻世明言:注釋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4.
[3] 馮夢龍.初刻拍案驚奇[M].北京:中華書局,2014.
[4] 張玄.徐復祚集[M].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22.
[5] 王煥.墨子校釋商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6]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M].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
[7]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9] 張然.明代家訓中的經濟觀念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8.
[10]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11] 馮夢龍.二刻拍案驚奇[M].北京:中華書局,2014.
[12] 田曉菲.留白:寫在《秋水堂論金瓶梅》之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13] 許中榮.中國古代吝嗇鬼及其故事的“尚趣”傾向試析——兼及對其創作與詮釋問題的思考[J].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5(1).
[14] 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續修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特約編輯 劉夢瑤)
作者簡介:陳方潞,寧夏師范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