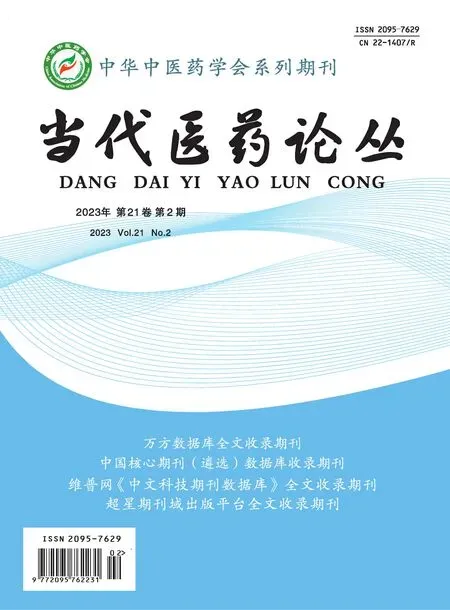正坤散聯合睡眠干預對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的治療作用分析
張小利,馮春輝,王學翠,唐燕秋,陳 程,蘇翠婷
(南寧市中醫醫院,廣西 南寧 530001)
研究證實,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的發病機制為在感染基礎上,免疫、遺傳、飲食、環境、不當治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小兒脾常不足,一旦外感溫熱之邪,則傷津耗氣、健運失司,不能運化水谷,從而引起氣血生化無源等脾虛癥狀;如果濫用苦寒清熱之劑或抗生素,就會加重脾虛綜合征病情,造成病程遷延。該病外因在于外感濕邪,病機在于脾失健運,內因主要是臟腑功能失調,特別是脾胃受損。故治療應從調理氣機入手,通過調暢中焦氣機來恢復人體正常的生理狀態[1-2]。該病持續時間較長,可達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對小兒的健康影響很大,其原發感染以呼吸道感染最為多見。相關研究[3]顯示,該病的發生與飲食不當、精神壓力大及生活無序等因素密切相關。目前臨床西醫治療該病,多采用輸液及口服腸道黏膜保護劑、腸道菌群調節劑等方法,臨床效果不甚理想。中醫認為,該病分為腹瀉型、便秘型、便秘與腹瀉混合型[4-5]。本文主要是探究正坤散聯合睡眠干預對該病的治療效果,現報道如下: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隨機抽樣法將2020 年7 月至2021 年12 月期間本院收治的120 例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患兒分為觀察A 組、觀察B 組及對照組各40 例,本次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病例納入標準:1)能接受治療及各項檢測者。2)病歷資料完整,中途未退出者。3)符合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診斷者。病例排除標準:1)合并心腦血管、內分泌和造血系統的嚴重原發性疾病。2)未按規定治療、資料不全、無法判斷療效者。3)在療程中發生其他疾病需另行治療者。三組的基線資料無顯著差異(P>0.05)。見表1。

表1 基線資料的對比
1.2 方法
觀察A 組采用正坤散聯合睡眠干預法進行治療,方法是:正坤散(組方為:香附0.4 g、九節菖蒲0.8 g、獨活0.6 g、蒲公英0.7 g,由本院制劑室提供,將以上中藥打粉后混勻裝袋制作成茶包形式),每次1 包,開水50 mL 泡10 分鐘,溫服,3 次/ 日。睡眠干預:晚上21:00 上床睡覺,禁止睡前喝咖啡、濃茶或吃刺激性食物,養成良好睡眠習慣,日間適當活動及鍛煉。共治療1 個月。觀察B 組僅給予正坤散治療,治療方法與治療時間與觀察A 組一致。對照組給予雙歧桿菌乳桿菌三聯活菌片(內蒙古雙奇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治療。雙歧桿菌乳桿菌三聯活菌片的用法是:<6個月,每次1 片(0.5 g),口服,3 次/日;6 個月~3 歲,每次2 片(1 g),口服,3 次/日;3 ~6 歲,每次3 片(1.5 g),口服,3 次/日。溫開水或溫牛奶沖服,嬰幼兒可將藥片碾碎后溶于溫牛奶沖服。共治療1 個月。
1.3 觀察指標
1)實驗室指標:分別在治療前和治療結束后檢查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A(IgA)的水平。2)療效指標:參照孟仲法[6]所制定的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療效標準和衛生部藥政局制定的《中藥治療脾虛證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的療效判定標準[7]制定本研究的療效判定標準,具體如下:顯效:經上述方法治療后,患兒的主要癥狀和體征消失,實驗室檢查結果基本正常,在治療期間及隨訪3 個月內未見復發。有效:經上述方法治療后,患兒的主要癥狀和體征基本消失( 消失1/2 或以上者)或有明顯改善,實驗室檢查結果有所改善或部分恢復正常;治療期間有輕度反復,隨訪3 個月內未見復發。無效:治療后,患兒的主要癥狀和體征無變化或加重。總有效率=(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3)不良反應評定:記錄患兒惡心、嘔吐、腹脹、腹痛等不良反應的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 標準差(±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免疫球蛋白指標的對比
治療前,三組的免疫球蛋白指標相比無顯著差異(P>0.05)。治療后,三組的免疫球蛋白指標均與治療前存在顯著差異(P<0.05)。觀察A 組治療后IgM及IgA 水平恢復正常,且均高于觀察B 組、對照組(P<0.05),觀察B 組的IgM 及IgA 水平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免疫球蛋白指標的對比(g/L,±s)

表2 免疫球蛋白指標的對比(g/L,±s)
注:①表示與觀察A 組相比,P <0.05 ;②表示與觀察B 組相比,P <0.05 ;③表示與對照組相比,P <0.05。
組別 例數 IgG IgM IgA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A組 40 6.54±0.87 16.82±1.52②③ 0.59±0.12 2.41±0.22②③ 1.26±0.28 3.51±0.76②③觀察B組 40 6.29±0.78 13.62±1.06①③ 0.61±0.10 1.43±0.64①③ 1.19±0.26 2.87±0.35①③對照組 40 6.39±0.89 10.26±1.04①② 0.57±0.08 1.03±0.15①② 1.23±0.25 2.07±0.29①②F 值 0.880 285.960 1.560 125.900 0.710 79.650 P 值 0.417 0.001 0.215 0.001 0.494 0.001
2.2 療效對比
觀察A 組的治療總有效率為97.50%,明顯高于觀察B 組的85.00% 及對照組的65.00%,差異顯著(P<0.05)。觀察B 組的治療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療效對比
2.3 不良反應對比
各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無顯著差異(P>0.05),見表4。

表4 不良反應對比
3 討論
脾虛綜合征是一種功能性疾病,其發病機制與諸多因素有關,如胃腸道刺激、內臟敏感性升高、炎性腸病、胃腸道感染、先天遺傳及腸道菌群感染紊亂等,患者常伴有腹痛、腹脹及大便性狀異常等癥狀[8-9]。該病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臨床尚無特效治療方案。該病屬于中醫學“泄瀉”“腹痛”范疇,病機為脾胃虛弱及肝郁脾虛,因此治療以益氣止瀉、疏肝解郁及理氣健脾為主[10-11]。
西醫治療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多采用免疫增強劑、助消化藥、維生素等對癥治療,但遠期療效均不理想,效果欠佳[12];而中醫藥對本病的辨證施治有一定優勢,如健脾益氣中藥可改善患兒癥狀,促進胃腸道功能恢復,減少并發癥發生,縮短病程,提高生活質量。睡眠干預可增加新陳代謝,促進藥物吸收,提升身體機能,且保持良好的睡眠,可避免勞逸失當,改善脾虛。在對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的認識上,中醫認為脾虛綜合征雖致病之因眾多,但主要可歸為先天不足、后天失養、外感侵襲、飲食所傷、情志失調等[13]。中醫提出的“脾虛濕熱”理論認為脾虛綜合征的病機主要為脾虛。《景岳全書·泄瀉論證》有云:“泄瀉之本,無不由于脾胃……若飲食失節,起居不時,以致脾胃受傷,則水反為濕,谷反為滯,精華之氣不能輸化,乃致合污下降而瀉痢作矣。”當今之人喜食辛辣刺激、肥甘厚膩之品,起居無節,勞逸失當,因致脾虛;脾虛失運,清濁不分,水走腸間,發為泄瀉。故病程日久患者多有大便稀溏、神疲乏力等脾虛癥狀。根據當代人陰病陽治的需要,趙世校教授在郭志辰教授的“藥量越小,走得越快,效果越好”的核心理念中依據“去味留氣”的處方思路,進一步探索,將中藥“氣”的效用發揮到極致,創建了完整的中醫小小方的理論、臨床體系。他根據河圖洛書和易經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取其數8,以《黃帝內經》中“法于陰陽,和于術數”及《易經》中“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為綱則,根據中醫五行理論與八卦術數的對應,確立了劑量標準,小小方每味藥的劑量在0.1 ~0.8 g。正坤散的組方中香附0.4 g,4 為震,為木,為肝,肝的疏泄功能是脾胃氣機疏通暢達,脾氣升清的一個重要條件。劑量取數字4 即可達到肝的疏泄功能。九節菖蒲0.8 g。8 為坤,為土,為脾,劑量取數字8 即可達到健脾作用。獨活為0.6 g。6 為坎,為水,為腎,可以起到補腎的作用。蒲公英為0.7 g,根據八卦中7 上8 下用藥理論,7 在后天八卦里是艮位,是左升的起點。藥物和劑量都可以起到增加下焦蒸騰之力的作用。本文采用正坤散聯合睡眠干預法治療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后發現,治療前,三組的免疫球蛋白指標相比無顯著差異(P>0.05)。治療后,三組的免疫球蛋白指標均與治療前存在顯著差異(P<0.05)。觀察A 組治療后IgM 及IgA 水平恢復正常,且均高于觀察B 組、對照組(P<0.05),觀察B 組的IgM 及IgA 水平高于對照組(P<0.05)。觀察A 組的治療總有效率為97.50%,明顯高于觀察B 組的85.00% 及對照組的65.00%,差異顯著(P<0.05)。觀察B 組的治療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各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無顯著差異(P>0.05)。分析其原因:正坤散組方中香附之效起于中焦,越膈而上到達上焦,具有土生金的作用。它能提升膈下中焦部位能量,使之經公轉路線越膈而上至膻中,有承上啟下、疏通三焦的作用。飲食入味化為五氣,變成五味上輸于肺,經過肺的宣發肅降把精微物質輸送到全身,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胃腸的消化吸收,脾散精于肺。也就是中焦能量向上運動到上焦的過程,即香附的升清作用。把中焦的精微物質輸送給上焦補充肺臟的能量,達到脾土生肺金的五行相生之理。九節菖蒲之效起于膻中,經過大椎向下運動到命門。獨活之效起于百會,通過大椎、命門、尾椎,到達足。它運行于外焦空間,能夠引頭部能量至足,化解外焦空間的能量積聚。蒲公英之效起于會陰,經過下焦、中焦、上焦,到達頭部。它可以增加下焦的蒸騰之力,增加下焦動力。四味藥共同運用,可起到“清除污染、疏通河道、能量搬家、公轉暢通”的作用。
綜上所述,用正坤散聯合睡眠干預法治療小兒感染后脾虛綜合征可顯著改善患兒的免疫球蛋白指標,提高其免疫力,減少其生病次數,療效確切,且安全性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