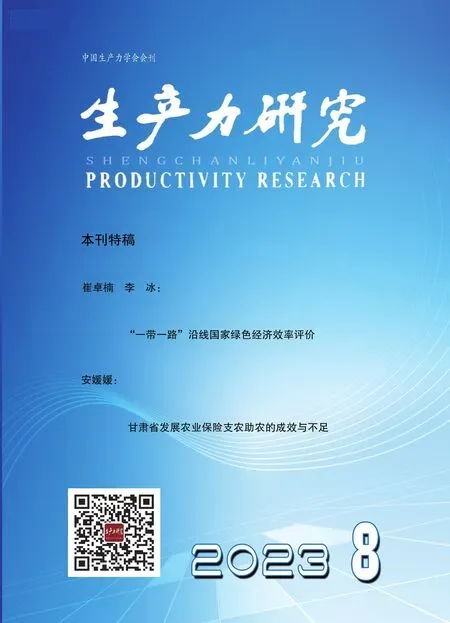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關系的研究綜述與展望
刁伍鈞
(西安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4)
一、引言
股權激勵作為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業績的一種方式,一直備受推崇。股利政策是財務管理的主要內容之一。隨著股權激勵的興起,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股權激勵與股利發放意愿、股利支付水平之間的關系。研究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的關系旨在揭示股權激勵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公司的股利政策,即實施股權激勵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公司股利支付的傾向和支付水平。這對于規范股權激勵,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研究現狀
根據股利種類不同,學者分別研究了股權激勵與股票股利、現金股利、股票回購之間的關系。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上市公司常常放棄現金股利而選擇股票回購方式進行股利分配(Bartov 等,1998;Fenn 等,2001;Kahle,2002)[1-3]。一方面,股票回購減少了股東個人所得稅。這種稅收收益有利于增加管理者財富。據此,Kahle(2002)提出“管理者財富假說”。另一方面,向公開市場回購公司股票不但為管理層提供了股權激勵的股票來源,而且緩解了因股票期權行權對每股收益的稀釋作用。實證研究證明股票回購數量與管理者股票期權數量正相關(Dittmar,2000;Bens 等,2003)[4-5]。據此,Kahle(2002)提出“期權提供假說”。肖淑芳和張超(2009)[6]、肖淑芳和喻夢穎(2012)[7]、韓慧博等(2012)[8]研究發現,相比現金股利,我國管理者更熱衷于分配股票股利,特別是高額股票股利;并且股權激勵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發放高額股票股利。隨著股權激勵計劃實施的增加,上市公司采取高送轉股利政策也明顯增多(李桂蘭和榮孟靜,2016)[9]。即使企業實際達不到送轉水平還會采取“異常高送轉”。這表明送轉股是管理層最大化其股權激勵收益的“理想”的掘金工具(呂長江和張海平,2012)[10]。而從非現金股利發放水平上來看,采用限制性股票激勵的上市公司其股利發放水平顯著高于采用股票期權激勵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根據我國股權激勵工具的趨勢變化,陳紅和郭丹(2017)[11]得出上市公司會選擇更有利于激勵對象的股權激勵工具。以上研究顯示股權激勵與非現金股利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文獻關于股權激勵與現金股利關系的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分歧。不同國家和地區股權激勵與現金股利關系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陳紅和郭丹,2017)[11]。在美國,管理層股權激勵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Lambert 等,1989;Fenn 等,2001;Hual 和Kumar,2004;Chetty 和Saez,2005;Cuny 等,2009)[12][2][13-15]。在芬蘭,1996—2001 年赫爾辛基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41%樣本公司的股權激勵計劃與現金股利分配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其余樣本公司股權激勵計劃與現金股利分配負相關(Liljeblom和Pastenach,2006)[16]。在歐洲,與美國企業非常相似,股權激勵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負相關(Eije 和Megginson,2008)[17]。以中國臺灣地區2000—2005 年間1035 家企業數據為樣本,Ming-Cheng 等(2008)[18]研究得出管理層股票期權與現金股利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因為我國存在半強制性分紅的規定,所以有關現金股利支付水平的文獻資料相對較多。但是國內研究結論也存在較大分歧。以2006—2009 年股權激勵公司為樣本數據,與非股權激勵公司相比,呂長江和張海平(2012)[10]發現公布股權激勵方案公司更傾向減少現金股利支付;股權激勵公司在激勵方案推出后的股利支付率小于方案推出前的股利支付率;進一步研究發現,具有福利性質的股權激勵公司對公司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更顯著。卓敏和李勇(2017)[19]研究發現股權激勵公司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權越多,其現金股利分配率更低。以2006 年1 月1 日至2011 年6 月30 日滬深兩市公告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數據,肖淑芳和喻夢穎(2012)[7]研究了股權激勵與股利分配的關系。研究發現,從股權激勵計劃公告前一年起,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現金股利和送轉股水平顯著高于非股權激勵公司;雖然股權激勵對送轉股水平和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均存在正向作用,但是實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選擇的現金股利政策比較符合自身的特征。也就是說,上市公司是否支付現金股利以及支付多少現金股利還是根據企業自身的盈利能力、投資機會、資本成本、籌資能力、現金流量以及所處的行業周期等實際情況來確定。并非總是利用現金股利為股權激勵對象進行利益輸送。根據2006—2012年樣本數據,葉繼英和張敦力(2014)[20]驗證了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相比未實施公司更傾向于高比例現金股利;公司股權激勵水平越高,現金股利分配的意愿越大,現金股利支付水平也越高。陳紅和郭丹(2017)[11]以2006—2015 年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確定非股權激勵上市公司樣本進行對比研究,研究結論支持施行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支付傾向和支付水平更高。由于匹配模型選定的比較對象更具有說服力,所以陳紅和郭丹(2017)[11]的研究結論進一步驗證并強化了葉繼英和張敦力(2014)[20]的觀點。雖然以上這些研究采用不同歷史時期的數據、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均得出相似的研究結論,這些研究結論表明股權激勵對象有增加現金股利發放獲得機會主義私利的動機。顯然,相較股權激勵與非現金股利之間的關系,股權激勵與現金股利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
股權激勵根據激勵對象不同分為高管股權激勵與員工股權激勵。2005 年《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簡稱《試行辦法》),規定激勵對象可以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技術(業務)人員,以及公司認為應當激勵的其他員工。2016 年《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明確股權激勵對象范圍包括所有員工。《試行辦法》實行后,股權激勵的水平和范圍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呈現逐年增加的變化趨勢。雖然絕大多數股權激勵對象同時包括高管和非高管員工,但是國內有關股權激勵的研究文獻還是主要集中在高管股權激勵。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員工股權激勵。根據2005—2012 年的樣本數據,陳艷艷(2015)[21]研究了員工股權激勵的實施動機與經濟結果。實證結果顯示:員工股權激勵存在吸引和留住員工的實施動機,與國外研究結果(陳艷艷和郭然,2017)[22]是一致的;員工股權激勵具有較強融資約束和激勵員工的解釋力,而國外研究(陳艷艷和郭然,2017)[22]對于激勵動機和融資約束的實施動機存在分歧。關于員工股權激勵的經濟結果,中外研究都尚無統一的結論。從員工薪酬角度出發,股權激勵與薪酬收益的比例也許是導致員工股權激勵經濟結果不一致的一個因素。因此,在研究員工股權激勵的時候,考慮員工薪酬情況也許有助于揭示員工股權激勵的真實結果。
文獻顯示研究方法日趨完善,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采用了比較分析方法。研究選擇的比較對象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比較股權激勵公司與非股權激勵公司的股利政策差異(肖淑芳和喻夢穎,2012;陳紅和郭丹,2017;卓敏和李勇,2017)[7][11][19];另一種是通過比較公司股權激勵實施前后的股利政策差異(徐政華等,2015;劉星等,2016)[23-24]。呂長江和張海平(2012)[10]在一篇文章中同時采用以上兩種比較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如何選擇非股權激勵公司樣本是分析股權激勵與非股權激勵公司股利政策差異的關鍵。大多數文獻給出樣本選擇的標準并無明確具體的選擇方法。陳紅和郭丹(2017)[11]則明確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選擇非股權激勵公司樣本,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其次,實證研究模型不斷改進。大多數研究采用單一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肖淑芳(2012)認為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是相互作用的,二者屬于內生性變量。單一模型沒有考慮內生性問題,研究結論可能不夠嚴謹。肖淑芳和張超(2009)[6]、肖淑芳和喻夢穎(2012)[7]建立了兩組聯立方程研究高管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的關系。聯立方程(1)和聯立方程(2)分別研究股權激勵(EI)對送轉股(SD)和現金股利(CD)的影響。在聯立方程(1)中,自變量上市時間TIME、股權性質PRIVATE、每股盈余EPS、成長機會GROWTH 不僅影響內生變量SD,也影響內生變量EI;在聯立方程(2)中,自變量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每股盈余EPS、成長機會GROWTH 不僅影響內生變量CD,也影響內生變量EI。因此,建立一個EI 影響因素的回歸方程以解決股權激勵的內生性問題。在此模型中,送轉股SD、現金股利CD和股權激勵EI 屬于內生變量;其余變量屬于外生變量。公式(1)中ONCF 是現金流量、PX 代表是否派現、SALARY 是管理層平均薪酬、AGE 為管理層平均年齡、TEC 為是否屬于信息行業、SH10為股權集中度。
聯立方程(1):
聯立方程(2):
最后,學者在研究股權激勵對股利支付意愿影響時一般都采用Logit 模型;對股利支付水平影響時,既有采用OLS 模型,還有采用Tobit 模型(陳紅和郭丹,2017)[11]。由于股利支付是非負的,所以采用Tobit 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更為合理。
總結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關系的研究結論,主要包括三種:(1)股權激勵與股利分配之間具有負向相關關系,即股權激勵的實施導致股利分配意愿和支付水平的下降(Lambert 等,1989;Fenn 等,2001;Hual 和Kumar,2004;Chetty 和Saez,2005;Cuny等,2009;呂長江和張海平,2012;卓敏和李勇,2017)[12][2][13-15][10][19];(2)股權激勵與股利分配之間具有正向相關關系,即股權激勵的實施導致股利分配意愿和支付水平的上升(Liljeblom 和Pasternach,2006;Ming-Cheng 等,2008;肖淑芳和喻夢穎,2012;強國令,2012;葉繼英和張敦力,2014;陳紅和郭丹,2017)[16][18][7][25][20][11];(3)股權激勵與股利平穩性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由于存在更大的可能性是高管將股權激勵作為掩飾其尋租行為的面具,從而引起公司股利政策的不穩定(劉星等,2016)[24]。
三、文獻評析
從現有研究結論來看,盡管上文結論(1)和結論(2)的觀點相反,但是二者其實都印證了股權激勵對公司股利分配是有影響的。結論(3)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影響性,并且結合代理沖突,說明管理層尋租是導致平穩性降低的重要因素。因此,進一步研究結論(1)和結論(2)的差異是揭示股權激勵與股利分配關系的關鍵。本文認為以下幾方面導致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分歧。
(一)股權激勵是否對股利進行保護
非股利保護型股票期權又被稱為固定計劃期權,指的是在期權計劃被授予時股票期權行權價格就確定了,并且行權價格不隨之后股利分配等除權除息事件而調整。如果公司采用非股利保護型股權激勵,那么任何現金股利都不會支付給股票期權的持有者(肖淑芳和喻夢穎,2012)[7]。也就是說,支付現金股利會導致公司股票期權價值下降。因此,上文中提及的美國、歐洲和芬蘭59%樣本公司的股權激勵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負相關,與股份回購正相關;而上文中提及的中國臺灣和芬蘭41%樣本公司因為沒有采用非股利保護,所以股權激勵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顯著正相關。美國實施的是非股利保護型股票期權計劃,所以美國實施股權激勵企業股利政策偏好股票回購。我國實施股利保護型股票期權計劃,并且對股權回購實施嚴格監管,所以中美兩國關于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關系的實證結果存在明顯差異。
(二)股利支付水平指標變量的選擇差異
現有文獻主要采用每股現金股利、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收益率三類指標進行實證分析。在股利保護型股權激勵條件下,股票期權行權價格的調整是根據每股現金股利進行的,調整公式為P=P0-V,其中,P0調整前的行權價格,R 是調整后的行權價格,V 是每股的派現額。我國實施股利保護型股權激勵,采用每股現金股利比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收益率來衡量現金股利支付水平更為合理。如果研究目標是非股利保護型股權激勵,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選擇每股現金股利、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收益率都是合理的。
(三)研究依據的理論基礎不同
激勵效應(即最優契約論)和代理效應(即管理權力論)是股權激勵成效的理論基礎。最優契約論認為,薪酬、股權激勵是解決代理問題的重要手段,股權激勵將股東和管理層的利益聯系在一起,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自由現金流過度投資或者在職消費,現金股利則相應增加。管理層權力論認為高管的尋租動機及道德風險會導致激勵的無效性(劉井建等,2017)[26]。由于管理者具有影響或實現關于董事會或薪酬委員會制定薪酬的意愿和能力,所以股權激勵則成為管理層尋租的途徑。比如,在授予和行權時,操縱短期信息,導致股票價格壓低或提高從而達到獲利目的(Bartov和Mohanram,2004)[27]。高管還可能利用股權激勵設置低行權標準謀取福利。此外,道德風險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比如激勵不足可能是由于股權激勵強度較低,而股權激勵強度過高則會由于“塹壕自守”的高管防御行為引起過度投資。Flor 等(2014)[28]發現,權益薪酬對投資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股票期權是一種接近有效的激勵經理人承擔風險投資的方式,但限制性股票并沒有這一效應,并且股權激勵可能導致過度的風險承擔行為。為了實現過度投資和管理者防御,高管勢必會減少現金股利、增加股票股利,從而達到掌控企業更多現金的目的。顯然,在股權激勵背景下,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實質上已成為薪酬契約的一部分。馮媛媛(2014)[29]以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動機差異為切入點,分析了最優契約和管理層尋租動機下,股權激勵計劃對股利政策的影響差異。研究認為:最優契約動機下公司公布股權激勵方案后現金股利支付率提高,而管理層尋租動機下公司公布股權激勵方案后現金股利支付率降低,送轉股水平將有所提高。因此,高管的私利行為會引起公司股利平穩性降低。無論最優契約論,還是管理權力論,研究對象都是高管股權激勵。員工股權激勵與高管股權激勵的動機不同,其激勵成效自然存在差異。
由于高管股權激勵和員工股權激勵實施一前一后,美國學術研究是先研究高管股權激勵后研究員工股權激勵。在我國,高管股權激勵和員工股權激勵是同時出現的,許多學者沒有區分二者,而是采用股權激勵數量占企業股本的比例數據進行分析。一是這種處理方式事實上是混淆了高管股權激勵與員工股權激勵的動機差異。盡管二者的一些解釋觀點是一致的,即高管股權激勵和員工股權激勵均具有激勵作用、吸引與留住人才以及緩解融資約束的作用,但是其他一些解釋觀點存在較大差異,比如管理層尋租理論和搭便車理論,前者僅適合解釋高管股權激勵,后者僅適用于員工股權激勵。二是由于高管與普通員工面臨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和薪酬結構,所以能夠解釋員工股權激勵的理論并不一定適用高管股權激勵(陳艷艷和郭然,2017)[22]。為了區分員工股權激勵與高管股權激勵的動機差異,在現有研究模型的基礎上,增加員工股權激勵數量與高管股權激勵數量的比例指標。之所以采用比例指標而不是員工股權激勵數量的絕對指標是由于我國股權激勵對象大多數同時包括高管和員工。股權激勵對象同時包括高管和員工,采用二者的相對指標,兼顧了高管和員工激勵動機的差異,更有利于揭示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的關系。如果股權激勵計劃只有員工沒有高管,那么采用員工股權激勵的絕對數量指標進行研究即可。因此,根據股權激勵對象,選擇恰當的研究指標,才能客觀地揭示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
四、研究展望
為了進一步完善不同激勵對象對股利政策的影響,本文建議構建員工股權激勵與高管股權激勵的比例指標(EIY/EIG),借鑒肖淑芳和喻夢穎(2012)[7]的研究模型,建立聯立方程(3)和聯立方程(4),旨在研究員工股權激勵與高管股權激勵之比對股利政策的影響。
聯立方程(3):
聯立方程(4):
雖然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員工股權激勵,但有關員工股權激勵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隨著員工股權激勵的逐步增加,明確員工股權激勵與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關系,不僅有利于完善股權激勵與股利政策的關系理論,還為政府制定合理的監管政策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