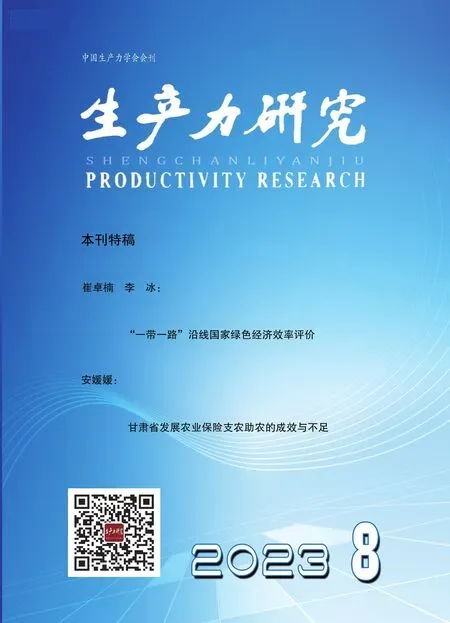碳排放權交易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研究
趙 峰,鄒 悅
(山東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 266590)
一、引言
作為一項典型的市場激勵型的環境規制工具,碳排放權交易推動我國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制度安排。長期以來,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居高不下,要想控制溫室氣體的過量排放從而推動綠色發展,就必須堅定不移的進行綠色創新,而企業是綠色創新的微觀主體,這就迫使企業不僅與國際接軌,響應國際關于綠色發展的號召,還要迎合國家政策,著力發明綠色技術,提高本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最終實現節能減排的目的。目前,很多學者對碳排放權交易能否促進企業綠色創新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主要概括為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
微觀層面的研究主要針對碳配額的分配方式以及碳價格機制。首先,對于配額分配方式而言,Cramton和Kerr(2002)[1]認為拍賣法在一定程度上比免費分配法更能促進綠色創新;Fischer 和Fox(2007)[2]則進一步將免費分配法分為基準法和歷史法,發現前者比后者更能促進企業的節能減排;宋德勇等(2021)[3]認為企業采用的配額分配方法會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其次,在碳價格信號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方面,Hoffmann(2007)[4]認為在碳排放權交易過程中形成的碳價格會對污染型生產技術起阻礙作用,而對清潔低碳技術起促進作用;Taylor(2012)[5]認為合理的碳定價機制能夠發揮對企業綠色投資和綠色創新的激勵作用。易明和程曉曼(2018)[6]基于碳價格視角研究了綠色供應鏈企業的最優產品定價機制以及企業的綠色創新策略,發現碳價格能夠在本質上決定供應鏈的綠色創新程度。
宏觀層面的研究主要針對碳排放權交易整體政策視角。Porter(1995)[7]提出環境規制越合理,其對創新的激勵作用越強,環境與經濟的雙贏越容易實現。郭捷和楊立成(2020)[8]探究了我國各個省域的環境規制對其綠色創新的影響,發現環境規制能顯著提高省域的綠色創新水平。郭蕾和肖有智(2020)[9]深度剖析了碳排放權交易能否誘發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相關結果表明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的創新行為具有誘導作用,企業會增強研究并產出新產品的動力。
總而言之,現有文獻研究比較充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未通過某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的作用來考慮前者對后者產生影響的路徑,并且也尚未從某一具體的行業出發來考慮二者之間的關系。基于此,本文以中國的制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收集了2011—2020 年典型制造業企業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碳排放權交易是如何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產生影響的,能夠為企業有效減少碳排放和進一步發展其綠色創新能力提供參考與指導。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碳排放權交易與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內在關聯
根據波特假說的相關理論分析,環境規制政策設置越合理和恰當,企業提升綠色創新能力的動力越足[10]。Jaffe 和Palmer(1997)[11]認為靈活型的環境規制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強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碳排放權交易在靈活類的環境規制工具中算是比較典型的,其不僅能促使減排成本高的企業在碳交易市場上購買碳配額從而激勵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提高綠色創新能力,而且能為那些減排成本低的企業提供在碳市場上出售盈余配額的機會,促使這些企業獲取額外收益從而更加激勵企業采取綠色創新行為。由此,本文提出了假設1:
H1:碳排放權交易會促進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發展。
碳排放權交易是如何影響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呢?Wu 和Zhu(2014)[12]從企業生產率的角度出發探究了當企業在面臨環境規制時其在技術抉擇方面存在的區別,其認為環境規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誘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發展,在碳交易平臺里,如果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低下,無法更新治污技術,那么該企業會處于劣勢地位,相反,那些積極開展環境治理投資的企業會盡最大可能提高本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以有充足的資金可以進行綠色創新。由此,本文提出了假設2:
H2:碳排放權交易會通過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進而推動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發展。
(二)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在碳排放權交易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作用分析
一般而言,各種環境規制手段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作為強制性的約束措施能夠對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產生極大影響,進而影響企業的決策行動及其綠色創新能力。徐開軍和原毅軍(2014)[13]綜合分析了這兩種環境規制手段,發現兩者的相互配合能夠明顯推動綠色創新的發展。張平淡和張慧琳(2021)[14]則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劃分為環境立法以及執法兩個變量,發現這兩個變量均可以正向調節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過程。由此,本文提出了假設3:
H3: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能夠在碳排放權交易推動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
三、變量選擇與模型構建
(一)雙重差分模型
要想分析某一政策所產生的效應,雙重差分法無非是應用最普遍的,這種方法能夠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處理組在政策前與政策后的差異。具體而言,以2013 年為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節點,將處于政策地區的制造業企業列為處理組,則對照組便是那些處于其余非試點省市的制造業企業,然后通過雙重差分模型來分析我國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能力在政策實施前與后的變化與差異,從而對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實施效果進行有效的評價。反映碳排放權交易和企業綠色創新能力關系的雙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1.被解釋變量。將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Green_ability)設定為被解釋變量,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可利用的數據庫來表征綠色創新,因此本文將借鑒相關學者對綠色創新的概念分析及其分類方式(李江濤和陶思源,2022)[15],采用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獨立申請和聯合申請)數量之和作為基礎指標測度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
2.解釋變量。碳排放權交易政策是本研究的主要解釋變量,具體而言,深圳、天津、上海、廣東和北京在2013 年首先被納入該計劃,然后湖北和重慶在2014 年被納入,緊接著福建在2016 年加入,所以對于隸屬天津、上海、廣東和北京這四個省份的制造業企業而言,2013—2020 年其Post 值均應取為1,隸屬湖北和重慶這兩個省份的制造業企業在2014—2020 年將 值取為1,而隸屬于福建的制造業企業的 值則在2016—2020 年取為1,除上述情況外,其余均取值為0。
3.控制變量。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地區的確立并非是隨機的,相反,國家在選擇試點地區時會綜合考慮各個地區的各種因素,可能會違背處理組和對照組選擇的隨機性,所以必須控制那些可能影響最終結果的額外因素以盡最大可能降低誤差。綜合前人的研究(游達明和李琳娜,2022)[16],本文納入模型體系的控制變量有: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企業規模(Size)、總資產凈利潤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資產負債率(Lev)、企業性質(SOE)以及現金流比率(Cashflow)。
(二)中介效應模型
制造業企業參與碳排放權交易時,其會因為買進或者賣出碳配額而對企業的經濟績效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是反映企業生產效率及其經濟利潤的關鍵指標,生產率高的企業會有更多的資金和精力進行技術研發和綠色創新,而生產效率低的企業更關注企業的基本盈利水平,面對環境污染和高度的碳排放量只能投入資金盡量減少排放強度,而不會從根本上進行綠色創新。因此,本文假設碳排放權交易會通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來影響企業綠色創新能力。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為中介可構建相關模型為:
其中,TFP 代表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此將借鑒文獻[17]的測算方法來測度該變量。α1表示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發揮的總效應,γ1表示當把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納入模型體系時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發揮的直接效應,γ2則表示當考慮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這一中介變量后碳排放權交易對該中介變量產生的直接影響。
(三)企業綠色創新能力測度模型
以企業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與企業申請的全部專利數量的比值來衡量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與專利授權量相比,專利申請量的滯后效應幾乎不存在,且更能清楚地反映企業當期的綠色創新能力,因此在測度企業綠色創新能力時選擇的是專利申請數量。本文所采用的綠色專利是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對綠色專利的分類標準,從中挑選與碳排放權交易和企業能源節約與污染治理相關的綠色發明專利以及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加總而得。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測算模型可以表示為:
在公式(4)中,Green_abilityi,t代表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Green-Pi,t表示綠色專利的總申請數量,Pi,t則是指全部專利之和。
四、實證分析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了體現數據的完整性和合理性,本文收集了2011—2020 年的上市制造業企業研究樣本,企業名單根據企業的證券代碼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及各個碳交易所的CSRC 行業分類中查詢后整理而得,相關數據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和Wind 經濟數據庫。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詳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雙重差分模型回歸分析
根據雙重差分模型基準回歸結果,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回歸系數為0.100 且顯著,因此碳排放權交易能夠顯著提升我國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假設1 成立;接著采用逐步回歸法來實證分析碳排放權交易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作用機制,也就是檢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在該過程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如果三個模型中的β1、α1、及γ2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則說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在碳排放權交易和企業綠色創新能力之間確實具有中介效應,若γ1也顯著,則說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在兩者之間起的是部分中介作用,但若γ1不顯著,則說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起的是完全中介作用。由表2 列(2)與列(3)可知,β1、γ1、α1與γ2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碳排放權交易能夠顯著促進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提高且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在該過程中會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設2 成立。

表2 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分析
(三)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假設檢驗。雙重差分模型具有應用合理性的前提便是要通過平行趨勢假設檢驗。以2013 年為政策沖擊點,考慮納入碳排放權交易政策試點前后的1、2 年并觀察其是否具有顯著性,由圖1 平行趨勢圖可知,在實施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前兩年,碳排放交易試點并未對兩組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產生顯著差異,而實施政策后兩組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發生了顯著差異,這表明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回歸結果有效。

圖1 平行趨勢圖
2.PSM-DID 檢驗。本文將利用核匹配進行估計以驗證結果的穩健性。首先對控制變量做Logit 回歸以獲取傾向得分值,然后選取傾向得分值與實驗組更接近的樣本作為對照組,圖2(a)和(b)分別指示傾向得分匹配前與后2 個研究樣本所對應的核密度圖像,可以看出匹配之后兩組的核密度值差距大幅縮小,且具有相似的變化趨勢。根據采用核匹配得到的PSM-DID 估計結果,實驗樣本的雙重差分值為正值且顯著,因此該檢驗通過。

圖2 匹配前后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核密度圖
(四)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的調節影響
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能否調節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運作過程呢?為了探究該問題,以各地區在各年度的環境標準和環境法規文件累計頒布數的對數值來表征當年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變量,并將該變量用ER 來表示,然后將解釋變量替換為碳試點指示變量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的交乘項,即Post*ER,并實施回歸分析。由表3 可知,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能夠調節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積極作用,所以假設3 成立。由此可見,只有聯合運用不同層面的環境政策工具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企業綠色創新能力實現更高程度的進步。

表3 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的調節影響
五、研究結論
碳排放權交易能夠利用市場機制助推企業提高其綠色創新能力,是迎合國際低碳倡議和響應我國綠色發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2011—2020年為研究區間,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分析了碳排放權交易對我國典型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路徑,并探究了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在該影響過程中所起的調節作用。由此本文得出兩點重要結論:
一是碳排放權交易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能力具有正向且顯著的直接效應和總效應,同時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也是顯著的,這表明碳排放權交易能夠對制造業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發揮顯著的促進效能,且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能夠在該過程中充當部分中介。
二是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納入模型體系以實證檢驗其是否會對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作用過程產生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能夠調節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而且該調節效應是積極的。因此,在多種環境規制政策的協同合作下,企業綠色創新能力能夠實現更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