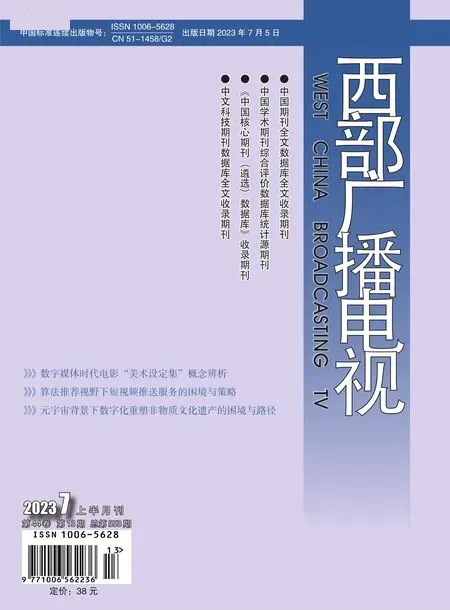電視劇《狂飆》人物建構與時空敘事分析
張馨月 馮驛博
(作者單位:吉林藝術學院新媒體學院)
反黑刑偵劇《狂飆》是2023年爆火的電視劇,主要講述了以一線刑警安欣為代表的正義力量與黑惡勢力之間展開的長達20年較量的故事。該劇采用跳躍式的時間線進行敘事,以一根錄音筆作為全劇的主要線索,督導組在破案過程中不斷被黑惡勢力干擾,劇情撲朔迷離。通過一樁案情的浮現,隱藏在京海市20年的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逐步被揭開。面對正義與邪惡、堅守與抗爭時,人性的復雜得以體現。導演徐紀周對人物善惡轉變的刻畫十分深刻,劇中的許多小角色都令人記憶猶新,這部作品中無論是敘事手法還是人物建構都值得探究。
1 復雜與矛盾交織的深刻化、藝術化人物構建
電視劇的創作是藝術情感和現實生活的高度結合,通過視聽語言對敘事和人物角色進行處理,能夠使其更符合現實生活中人物的情感。一部優秀的影視作品中,除了高質量的劇本和過硬的技術團隊,人物角色的塑造往往起著關鍵性作用。在《狂飆》這部劇中,不僅主角個性鮮明、立體豐滿,就連配角都給人一種現實社會的寫實感。
1.1 多角度人物構建使角色更具真實性
該劇最開始黃翠翠被拋尸,安欣與李響調查黃翠翠的人物關系時,并沒有因為黃翠翠的身份而對她抱有歧視的目光,在發現她還有一個女兒黃瑤時,為了保護黃瑤幼小的心靈,就對黃瑤說了善意的謊言。后來,安欣還自費為陳金默與黃瑤做親子鑒定,體現了執法者安欣溫情的一面。陳金默作為全劇中冷血的殺手,入獄后,黃翠翠騙他說要把孩子打掉,他從此恨上黃翠翠。但是,當安欣告知陳金默還有一個女兒時,他的人生重新點燃了希望。在出獄后,為了感激高啟強,陳金默為高啟強解決了許多見不得光的事,淪為高啟強的殺人工具。出獄后本應該重新做人的陳金默,因為感激高啟強再次步入歧途,最后又被高啟強用黃瑤威脅從而聽從他的安排。導演通過表達舐犢之情,把這個冷酷殺手的反派角色塑造得更具人性,增加了戲劇的張力。劇中講到莽村拆遷時,李順有一個身體不好的兒子李青,為了給兒子治病,李順一把年紀還出來干力氣活。李順與陳金默吃飯交談時,還告誡陳金默趁年輕多學點技術以免老了吃虧,但最后還是慘死在陳金默手中。李順這個角色的構建也是導演的一種對比手法,在逆境時李順仍然沒有放棄對人生的希望,仍然努力工作救治李青,從側面襯托了反派的無情,讓觀眾產生共情心理。
1.2 家庭關系構建使人物角色聯系更加緊密
“苦難敘事”較為容易表現個體的道德倫理,考驗家庭成員的友愛與孝悌,所以往往成為家庭倫理劇的常用敘事模式[1]。電視劇《狂飆》中的家庭關系主要圍繞高啟強、高啟盛和高啟蘭兄妹三人展開,三兄妹從小父母早亡,家境清貧,相依為命,哥哥高啟強在菜市場賣魚供弟弟妹妹上大學,卻被唐氏兄弟欺負,大年三十被打進派出所。雖然家境貧寒,但是哥哥高啟強對弟弟和妹妹仍十分寵愛,一碗豬腳面三個人吃,妹妹吃肉、弟弟吃面、自己喝湯。由于家境貧寒,高啟盛自小養成了自卑且敏感的性格,他經常替同學曹斌做作業,卻發現自己背地里被同學瞧不起,這讓高啟盛長期以來的壓抑突然爆發。當高啟強被李宏偉羞辱時,高啟盛為哥哥解決問題時的辦法也十分極端,這也是弟弟高啟盛最終走向毀滅的助推器,而高啟強也是在弟弟的慫恿下一步一步走向深淵。在傳統刑偵劇中,一般都以案件為主線敘述,而在刑偵劇中融入家庭情感元素可以更好地平衡敘事節奏,為角色之間的情感變化建立關系紐帶,從而為觀眾帶來了新的議題。
1.3 情感敘事使人物構建更加豐滿
情感敘事可以使人物角色更加豐滿,增強人物間的戲劇沖突,使劇情發展更復雜,同時運用視聽語言能夠引起觀眾共鳴,讓觀眾與劇集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系。黑格爾認為:“戲劇性存在的基礎在于劇中人物之間不再以純粹獨立的抒情和孤獨身份表現自己,而是通過性格和目的的矛盾聯結若干人物,彼此發生一定的關系。”[2]在這部劇中,導演將沖突與對抗放在了安欣與高啟強的關系設定上,從大年夜的一碗餃子并舉杯慶賀,到二人在大街上擦身而過,最終在監獄里隔窗相望,安欣又為高啟強遞上了餃子,高啟強隔空做舉杯手勢,導演把人性與感情融入故事情節中,把二人的人物形象刻畫得十分豐滿,呈現出了他們微妙的情感變化。黃瑤的人物設定充滿了審判的意味,故事的開端是黃瑤之母黃翠翠的錄音筆事件,高潮是黃瑤之父陳金默為高啟強賣命身亡,結局是黃瑤收集強盛集團的犯罪證據后親手將高啟強送入監獄。導演對黃瑤前期的刻畫是乖巧聽話的小女孩形象,與后期為父親復仇時的角色反差之大令觀眾大吃一驚,也側面將該人物成長的隱忍、壓抑刻畫了出來,增加了人物關系的復雜性,使劇情變得更加緊湊。安欣的徒弟陸寒在追查高曉晨的槍擊案時找到了王力,并希望他出面作證,但是遭到拒絕,最后失蹤。陸寒與譚思言一樣,一直不畏壓力去搜集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的犯罪證據,是該劇中守護正義的溫暖人心的角色,他們勇敢堅毅的行為讓觀眾心生敬畏,容易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
電視劇《狂飆》在人物構建時突破了傳統的角色構建,為角色去除了標簽,讓角色更加豐滿、更具人性。黑格爾認為:“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正是人類惡劣的情欲,也就是貪欲與權勢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3]該劇在對正、反兩面人物的構建上注重結合現實,對人性進行更深入的挖掘,使人物形象具有真實性、復雜性與矛盾性,讓觀眾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故事情節發展對角色人物內心的影響,看到人物的成長蛻變,加強了正向價值觀的傳遞,引發了觀眾的情感共鳴。
2 正義與邪惡對抗的多角度、多視點敘事維度
文學敘事學中的敘事視角通常與敘述者緊密相關,主要從敘述者敘述、觀察、感知的角度出發,但在影視作品中,視角通常被稱為“視點”,僅指“視點鏡頭”[4]。從敘事的角度來說,警察與罪犯的人物設定在刑偵劇中是固定的,無論是在敘事方面還是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要給觀眾帶來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信念感。隨著無數的優秀作品不斷涌向市場,觀眾的審美需求發生了變化,渴望看到更有內涵的節目。電視劇《狂飆》對角色背后的人性刻畫得入木三分,無論是警察還是罪犯,都刻畫了他們的人性,既豐滿了角色,又不脫離現實。除此之外,還對他們的家人、同事以及朋友等多角度的敘事視點進行了刻畫,并通過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將其串聯起來。在穿插回憶的敘事中,故事內容更加撲朔迷離,任務沖突和對抗更加激烈,給觀眾留下的印象也更加深刻。
2.1 正義與邪惡對抗的主線,堅持與迷失的支線
《狂飆》導演徐紀周曾擔任多部優秀刑偵懸疑題材作品的導演、編劇,擅長刑偵題材創作,擅長對真實事件進行改編。《狂飆》將安欣警官與黑惡勢力之間的博弈與對抗作為故事發展的主體框架,以黃翠翠案為起點、錄音筆為線索,形成了緊湊的敘事主線。該劇開篇就交代了安欣警官正直善良的正面人物形象,不愿在領導面前爭搶功勞,同事們避之不及的臥底行動他毅然參加,這集中展現了現實社會中許多守護人民的無名英雄的優秀品質。該劇通過安欣警官對賣魚販高啟強一次意外的善意搭救,以及徐江兒子的意外身亡作為助推器,讓高啟強一步一步走向了犯罪。從賣魚商販到建工集團總經理最后到強盛集團董事長,高啟強完成了人物角色的蛻變,導演通過三個部分講述高氏兄弟的“發家史”,看起來更像是一種黑色幽默手法,不同于傳統刑偵劇中的暴力美學,而是側重刻畫人性,給觀眾帶來了良好的觀劇體驗。
該劇沒有像傳統刑偵劇一樣以懸疑推理探案作為主要的情節線索,而是以展現掃黑除惡常態化背景下人情社會與法治社會的碰撞為主。在這部劇中,許多黑惡勢力的保護傘隱藏在暗處,為了增強了劇情的神秘色彩,有的演員在殺青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劇中不止一位像安欣警官堅守自己不被黑惡勢力所腐蝕的正直人員,如市政府辦公室的譚思言同志不斷收集、整理材料,向有關部門舉報趙立冬的違紀行為;刑偵大隊隊長李響充當間諜打入趙立冬、王秘書等人內部,收集趙立冬的犯罪證據,在譚思言失蹤后預測到自己的結局,把所有證據留給安欣;安欣被調離刑警隊后,他的徒弟陸寒仍然選擇和師傅安欣一樣堅守正義,對高曉晨的犯罪事實追查到底。相反,安欣的師傅曹闖對權力的渴望讓他迷失自己,甘愿充當趙立冬的爪牙;楊健離開了禁毒支隊,在供電局工作后與高啟強勾結在一起,掌握了整個京海市的供電工程。該劇通過兩種不同的選擇展現了人性堅持本心與迷失自我的沖突,也為無數像安欣、譚思言、李響和陸寒等正義化身的無名英雄正名,向觀眾傳遞了正向的價值觀。
2.2 多線交織的非線性敘事策略
傳統的線性敘事一般沿著一條時間線將故事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四個階段完整交代出來,符合故事發展邏輯,故事之間的情節有關聯性,故事線索清晰。而數字媒體藝術的出現改變了影視行業的創作手段,非線性敘事手法和蒙太奇剪輯手法被應用于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中,以此來優化觀眾的觀影體驗,激發觀眾的觀影興趣。非線性敘事是將傳統線性敘事的故事結構打散,通過蒙太奇剪輯的手法實現隔空對話,常被應用于懸疑、刑偵等類型片中,能夠使故事節奏更加明快,激發觀眾對未知真相的好奇心。《狂飆》通過縱向時間結構的三段式敘事來講述故事,以反派人物高啟強的三個不同發展階段作為劃分依據,使用大量的插敘和補敘手法,在關鍵時刻設置懸念,再通過插敘和補敘的手法解答懸念,激發了觀眾的好奇心,讓觀眾更深層次地理解了劇中的人物形象。
《狂飆》采用三段式的敘事策略,以回憶與現實相結合的手法,將掃黑除惡常態化背景下督導組查辦京海市強盛集團作為故事發展線索,最后揪出盤踞在京海市數十年的黑惡勢力及其背后的保護傘。“一般來說,事件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人物性格成長的過程。因此在情節模式中,人物與事件是相輔相成的。”[5]在督導組入駐京海后,該劇通過插敘和補敘的手法將三個階段不同時空的案件串聯起來,剝絲抽繭般地推進案件的偵辦過程。第一個階段以2000年為開端,講述了賣魚販高氏兄弟的“發家史”,徐江之子意外被電身亡后分贓時,整場戲高啟強只用一句臺詞“我一個人去的嗎,咱們不是三個人一起去的嗎”,就把言外之意的威脅和利益綁定給交代清楚了。在唐家兄弟離開后,導演用一個180°環繞鏡頭從高啟強的背后轉至正面,象征著高啟強的人物角色發生了轉變。這一時期的安欣警官仍然是一個勇往直前、不懼艱險的正義形象,在表彰大會上將內鬼推出了水面。第二個階段是從2006年開始,主要講述了高啟強進入建工集團后與泰叔的較量,以及在高啟盛墜樓身亡后高啟強加入趙立冬陣營的故事。在這個階段,劇中有一個場景是攪拌機倒出了一根斷指,導演運用了隱喻蒙太奇的手法暗示了譚思言同志的結局,也把高啟強這一人物角色徹底喪失了人性刻畫得更加深刻。此時的安欣在經歷了孟鈺被綁架、李響墜樓身亡以及譚思言失蹤后,被沉痛打擊后并沒有放棄正義,而是選擇暗中整理材料、靜待時機。第三個階段是2021年督導組入駐京海后,高啟強此時已與趙立冬決裂,高啟強在經歷了喪弟、喪妻后已收斂鋒芒,偽裝出熱衷慈善事業、關愛老人和小孩的“慈善家”形象。作為正義一方的安欣,經歷了20年風雨,終于抓捕了黑暗深淵中的高啟強,二人在獄中的對話也形成了戲劇張力。該劇敘事節奏緊湊,給觀眾帶來了良好的觀劇體驗,引發了觀眾新的思考。
2.3 平行敘事推動故事發展
在徐江走投無路全城被捕時,趙立冬假意為他策劃出逃路線,實際上是讓曹闖解決掉徐江。趙立冬安排全市公安系統召開表彰大會,讓安欣上臺領獎拖住他,卻沒有預料到高啟強和陳金默會突然出現。這場戲采用了平行敘事的手法,一條線由孟德海和安長林為安欣頒獎展開,另一條線由李響跟蹤師父曹闖到鋼鐵廠展開,這兩條線通過安欣和李響在電話里的對話形成了聯系。安欣站在主席臺上發言時,用真情打動了李響,李響最后報告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二人在不同空間對話的這場戲在剪輯手法和視聽語言上都將第一階段的故事情節推向了高潮,利用配樂營造了嚴肅的氛圍,吸引了觀眾的眼球。同時,還運用特寫鏡頭捕捉到了李響當時內心的糾結與緊張,利用移動鏡頭加快了敘事的節奏,該場景也與禮堂內的莊重嚴肅形成了對比,通過音樂的鋪墊增強了平行敘事的整體感。
3 結語
電視劇《狂飆》以三段式敘事為主,多種敘事手法并行,將作品的文本內容與藝術創作手法高度結合,呈現出了掃黑除惡常態化背景下國家掃黑除惡的決心。導演徐紀周在創作過程中沒有脫離現實,而是站在現實主義的角度,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關注社會問題,探討了人性的復雜,得到了觀眾的認可。該劇為我國反黑刑偵劇的創作開辟了新的方向,相信此后這類題材的優秀作品仍會不斷出現,給觀眾帶來更好的視聽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