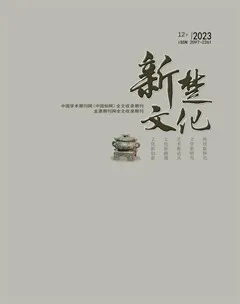時代癥候與精神經驗
【摘要】里爾克《杜伊諾哀歌》通過“它不再認識神殿”展示了現代世界整體性不再、主客體分離、神性喪失的時代癥候,并通過對“動物”“戲子”“木偶”“戀人”等意象的描繪,深入揭示了現代人動蕩不安、內省與糾葛的精神經驗,為現代性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詩性言說文本。
【關鍵詞】里爾克;《杜伊諾哀歌》;現代性;時代癥候;精神經驗
【中圖分類號】I106.2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36-0030-04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3.36.009
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下稱《哀歌》)是20世紀現代主義詩歌的璀璨杰作。《哀歌》由十首長詩組成,文字壯美,意義深遠;自《哀歌》誕生以來,諸多如海德格爾、漢娜·阿倫特、伽達默爾等思想家以及許多學者都做出了各自別開生面的闡釋。然而其浩大的篇幅、豐富的哲學背景以及內省式的詩風,使得任何一個人要走進《哀歌》的世界都是一件難事。本文通過具體文本段落的細讀與意象分析,結合現代思想家海德格爾、韋伯等人的理論,對《哀歌》所展現的現代世界的時代癥候以及現代人的精神經驗做出初步把握。
一、《哀歌》展現的時代癥候:“它不再認識神殿”
現代都市生活不斷地為現代人提供新鮮而快速的刺激,同時又使現代人走向多樣性與安定性的反面。這種兩面性如同馬歇爾·伯曼為現代性下的定義:“所謂現代性,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一種環境之中,這種環境允許我們去歷險,去獲得權力、快樂和成長,去改變我們自己和世界,但與此同時它又威脅要摧毀我們擁有的一切,摧毀我們所知的一切,摧毀我們表現出來的一切。”[1]這樣的現代性的“大漩渦”體現在里爾克的《哀歌》中,是他在第七哀歌中所描繪的“力的寬敞的倉庫”:
“我們的生命在嬗變中流走。外部之物/在一點點縮小。一座持存著的房屋曾在之處,/臆想成的形體在自薦,橫亙著,完全/屬于臆想之物,似乎依然完整地立在腦中。/時代精神將自己塑造成力的寬敞的倉庫,無形地/如同它從一切中贏得的繃緊與繁忙。/它不再認識神殿……”[2]879
在都市空間不斷縮小的境況下,古代“持存著的房屋”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建筑,即“力的寬敞的倉庫”。現代化進程推進著新的建筑空間崛起,將“臆想之物”變為現實,同時也推倒了舊的存在,生命成了“嬗變”而“流動”的物體,在日新月異的“繃緊”中,都市空間中能夠被確定的事物也在悄然消逝著。也就是說,里爾克描繪的現代世界,脫離了前現代的傳統根基,形成了以“進步、流動、緊張”等為特點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神殿”的樣子——即那些古老的價值與精神——已經無法被現代人所辨認。
(一)天使的遠離與“世界圖像時代”
在第二哀歌,里爾克展現了一個歷史與現在、神話與現實相對立、相隔離的現代:
“每位天使都是恐怖的。然而我還是,哀哉,/還是要歌唱你們,幾乎致人死命的靈魂之鳥,/因為我熟悉你們。多俾亞的歲月去往了何處?”[2]855
曾經的天使在圣經故事中能夠整飭了衣裝,成為年輕人的引導者,今日天使的身影卻會將我們“擊斃”。這樣的世界究竟是如何到來的?海德格爾在《詩人何為?》中說,“上帝的缺席”意味著“不再有上帝顯明而確實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圍……把世界歷史和人在其中的棲留嵌合為一體”[3]269。相反,在“人”成為主體之后,世界成了被客體化把握的圖像,人從世界中剝離了出來成為世界的主體,世界成為人認識與觀看的對象。這樣的對立狀態,一方面確立了西方近現代的人本思想與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卻也遮蔽了存在的本真狀態,人們試圖用理性去認識世界時卻發現無法真正地把握其整體。這正是海德格爾所說的“世界歷史和人在其中的棲留不再嵌合為一體”,同時也是里爾克在第二哀歌所寫到的現代人的境遇:
“而我們,我們開始感覺,就開始消散;啊我們/被自己的呼吸呼出,去往彼處;薪火相傳中,/我們發出更弱的氣味。/……難道天使……/仿佛出于疏忽,我們的本質才得以/零星地接近他們?”[2]855-856
在呼吸中,即每分每秒的存在中,我們都將自己呼向“彼處”,即作為客體的圖像世界;然而,“我們開始感覺,就開始消散”,在被視覺觀看的幻覺包圍中,我們難以使存在澄明,而只能“發出更弱的氣味”。面對現狀,里爾克發出了痛苦地詢問:我們到底怎么做才能重新融入世界空間,探尋萬物的本質,去接近作為超越者的天使?正因如此,曾經能夠與年輕人多俾亞一同遠行的天使,如今成為“恐怖”的存在,因為它對現代人來說已是不可理解的事物。
當諸神隱遁,“紀念碑”(墓碑)“爆裂”了,人成為理性主體卻無法把握整體之時,里爾克與海德格爾一樣陷入了追憶性的沉思。“多俾亞的歲月去往了何處?”馬克思說,“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即愈益將世界作為客體對立——“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卑鄙行為的奴隸”[4];“一切堅固的東西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正如里爾克想要描繪與呈現的世界一樣:天使形象的親和性已經徹底地遠離我們,現代人從和諧的、整體性的神性世界中抽離,來到了一個對立的、危險的世界圖像時代。科學與理性認知的圖像,“假設的實在只是符號工具,它們的作用(比如在地圖上滾動的距離測量工具)只是幫助我們在世界中尋找自己的道路,但是卻無法描述任何實際的對象或者過程”[5]12。世界理性化后,它自足的實在性與神秘性都被遮蔽了,在工具主義的轉化中成為被設定的對象與被利用的現代空間。
(二)神性消隱與工具理性
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化進程同時伴隨著理性化的過程,即理性主體的價值理性不斷萎縮、工具理性不斷擴張的過程,這個過程與資本積累、科學技術發展密不可分。它起源于笛卡爾的理性主體的確立,在笛卡爾那里,主體擺脫了自然與上帝的陰影,一切事物都將作為客體接受理性主體的評判;然后,“理性”成了現代社會組織形式的根基,以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主宰的自由市場最具代表性。當人們致力于為城市運作、政治體制構建以及人生規劃制定愈加清晰的規章,當“理性人”在經濟學中剔除了一切其他價值評判而只剩利益與效率導向,這樣的理性化過程就愈發接近極致。在理性觀念主導的時代,世界被祛魅了,它不再需要人們通過宗教與巫術去接近它的神秘,而成了主體能夠用“理性”這個工具把握、能夠認識與改造的對象。因此,世界的靈韻喪失了,如同海德格爾的思索那樣,神性消隱了,人們從上帝與天使的身邊退去,進入了一個世俗的、主客體割裂的現代世界。于是,里爾克這樣寫道:
“神殿,心的被浪擲之物,/被我們更隱秘地儉省著。是的,何處一個事物依然/承受,那曾經受禱告、受侍奉、受跪拜的一個……許多人不再覺察到它,但是無心于利益,/他們如今在內心將它建筑,以墩柱與雕像,更巨大!”[2]879
曾經鼎盛的神殿遁入了不可見之域,它作為一種“價值理性”的信仰,是“心的被浪擲之物”,許多人不再察覺到它,而是醉心于“利益”,受工具理性驅使,“生命在嬗變中流走”。事實上,啟蒙理性所提供的一種世界理解與進步主義如同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中所述的那樣,只不過是一種新的神話罷了:
“啟蒙對迷信的破除只是重新恢復了神話……啟蒙通過竭力犧牲神話,重復了神話的犧牲。”[5]59-60
然而,里爾克講述了他那微薄的希望:“心的被浪擲之物,被我們更隱秘地儉省著……他們如今在內心將它建筑,以墩柱與雕像,更巨大!”歷史的神殿成了久遠的懷戀,在現代性的“鐵籠”里,我們能做的是:在個體內向的運思中重建失落的整體性,并且這具有超越歷史的向度(“更巨大”)。這是里爾克所持有的希冀,整篇《哀歌》將圍繞這一點做出屬于詩人的努力。“在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里爾克的回答是,為一個整體的、非物化的、有機的世界的逝去作一首哀歌;即海德格爾所說的“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的蹤跡”。
二、《哀歌》展現的精神經驗:
“我們的棲居不太可靠”
我們已經認識到了里爾克針對現代都市社會所指出的精神癥候:在工具理性支配的現代社會里,人從整體世界里被剝離,不得不身處主客體對立、神性消隱的“世界圖像時代”。那么,在個體的遭遇與精神經驗的角度,現代人將面臨怎樣一種處境?下文通過分析幾個重要的詩歌意象“動物”“戲子”“木偶”“戀人”,來探究《哀歌》展現的現代人精神經驗。
(一)人與動物:“我們不和諧”
里爾克在作為開篇的第一哀歌中就如此點明:
“啊,我們究竟能夠求靠誰?天使不行,/人也不行,機靈的動物已經察覺,/在這個被人闡釋的世界,我們的棲居/不太可靠。”[2]849
“我們的棲居不太可靠”,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了堅實的大地,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被人闡釋的世界”。人往往利用語言闡釋世界,為萬物命名,可為何里爾克認為棲居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不太可靠”呢?因為在里爾克看來,語言僅僅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命名(“對一個習慣的扭曲的忠誠”),詞語與其所指的關系是任意的,無法照見物的本質性,不僅無法讓我們接近本質,反而會使我們與整體性的自然產生割裂,因此,人在這一點上反而不如不具備語言能力的動物(“機靈的動物已經察覺”)。里爾克在1926年2月的一封信件中說道:“動物的意識程度把動物投入世界,但動物沒有每時每刻都把自身置于世界的對立位置(我們人卻是這么做的)。動物在世界中存在;我們人則站在世界面前……”[3]322動物正是里爾克在第八哀歌提出的重要形象“敞開者”的代表。與之相對,我們人類卻面臨著難題:“我們從未曾,一天也未曾面對過內有繁花無盡綻放的純粹空間。”[2]這樣的難題,引出了我們在生存中的“不可靠”的狀態:
“生命之樹啊,何時是冬季的?/我們不和諧。我們不像候鳥/那樣得到告知。過時而遲晚地,/我們驟然強與風為伴,/落入冷漠無情的池塘。”[2]863
春去秋來,“候鳥”作為“在世界中存在”的動物,能夠得到自然變換的告知,安定地遷徙與回返,這在我們眼中幾乎是接近永恒的;人類卻不能,面對變動不居、無法把握的現代世界,我們需要發問:“生命之樹啊,何時是冬季的?”并且往往得不到答案。里爾克簡潔而深刻地指出人們的精神處境——“我們不和諧”,我們與我們所處的世界無法相識相融。這一節詩以一種真誠的悲劇性貼近了讀者的經驗:這種“驟然”的短暫性,以及“過時而遲晚”的不和諧的偶然性,構成了我們現代生活的獨特體驗。我們能在這里感受到來自波德萊爾的審美現代性傳統。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波德萊爾從畫家居伊描繪現代生活的畫作中提煉出了審美現代性的特征,他說道:“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6]這種現代主義審美體現在了波德萊爾《給一位過路女人》的“最后一瞥之戀”中,同時,也籠罩了《哀歌》對變動不居的人生的表述:“就這樣我們活著,總在別離中。”[2]886
(二)“戲子”與“木偶”:對世界與自我的觀看
為了以詩歌的形式更豐富地深入他想表達的主題,里爾克發揮了隱喻的力量。緊接著第四哀歌的第一節關于現代生活境遇的描繪,里爾克寫到了一組“戲子”與“木偶”的對比:
“誰不曾惶恐地坐在自己的心幕之前?/帷幕拉開:場景是別離。/容易理解的。熟悉的花園,/輕悄搖曳……”[2]863-864
每個人在面對生活的抉擇時都需要審視自我的內心,而這樣的時刻往往惶恐不安。里爾克將內心世界具象化為一個“舞臺”,深入描繪其中劇場性的發生。當進入自我內心的舞臺后,“帷幕拉開,場景是別離”。“別離”的主題成了心靈舞臺上的一出悲劇,我們坐在帷幕后對其觀看,正如同我們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無所棲居的羈旅與鄉愁之感。然后,“戲子”形象出現了,他卻成了里爾克否定的對象:
“然后首先出現戲子。/不是他。夠了!即使他動作如此輕松,/他化了妝,他變成一個小市民,/穿過廚房走進居室。”[2]864
一方面,作為心靈舞臺的觀眾,我們與演出著的客體處于間離狀態,我們明白“戲子”的本質是虛偽的,他戴著“半滿的面具”;另一方面,“他變成一個小市民,穿過廚房走進居室”。舞臺上的“戲子”正是市民生活中的普羅大眾,正是觀眾本身,觀眾正是舞臺上那個虛偽的角色,進行著表演。意味深長的是,里爾克在這里使用“觀看-被觀看”的關系鏈,而兩端其實都是我們自己:一端是一個與舞臺間離的主體(觀看者)、一端是一個身處客體世界但進行著虛偽表演的“主-客體”(被觀看者)。這兩端出現在“惶恐地坐在自己的心幕之前”審視自我的時刻,它們對應的是審視時的自我與被審視的自我。
于是,與被否定的“戲子”形象相對,里爾克提出了他所肯定的一種形象——“木偶”。木偶形象帶給人的傳統含義一般是負面的:失去感情、失去表達、受人操縱……但在里爾克筆下,在與“戲子”的對比中,“木偶”形象具有了“敞開者”的影子:
“我不想看這半滿的面具,/我寧愿看木偶。木偶是全滿的。我愿/忍受木偶的皮囊、提線和那張/只有外觀的臉。”[2]864
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里爾克認為居于被語言闡釋的世界中是不可靠的;因此,用語言進行表演的“戲子”被里爾克批判。相對的,木偶的沉默反而是“全滿的”,木偶的沉默使它置于存在之中,接近了真實,木偶的純粹物質性標示著它存在的統一性,不像“戲子”被分裂為自我的兩端,木偶“由物質填充和包裹的身體就是它們的本質……它的內在毫無保留地呈現了出來”[7]140。
里爾克在這里并沒有繼續深入“木偶”的形象,卻花了更多的筆墨在描寫“我”的觀看,他用了連續的四個“即使”來堅定地展現“我”觀看的持久性。這是里爾克最終想要說明的東西,不論是“戲子”還是“木偶”,最終都將置于我們的觀看之下,我們心靈的帷幕將世界與自我——這兩個可以合為一體的東西——劃分為舞臺與觀眾席。一方面,里爾克在描繪著現代人的現狀,仿佛我們能做的不過是不具有介入性的觀看行為,“空虛……撲面而來”,并且陪伴者不斷地更換;另一方面,不論周圍的世界正在發生什么,“我”都始終倔強地堅持著觀看,里爾克想說的是:只要觀看的動作持續下去,那么也許在內向的審視中就有接近真實的可能。里爾克通過“戲子”與“木偶”的對比展現了現代人豐富的內心糾葛狀態,內向的內省與外向的觀看都是現代人難以擺脫的境遇,時時刻刻籠罩著現代人的精神生活。
(三)“戀人們”:互相掩飾或互相持存?
在詩中,里爾克繼續探討了一個問題:身處窘困的黑夜,我們為世界的不可知性所惶恐,然而,“戀人們”卻在黑夜相互依偎——難道“夜可讓戀人們更覺輕松”?難道作為戀人,用互相慰藉的愛情能夠更好地面對時代的貧乏嗎?
“……夜可讓戀人們更覺輕松?/唉,他們只是在用對方掩飾自身的運數。/這你還不知道嗎?且將雙臂里的空虛/拋向我們呼吸著的空間吧;或許鳥/會以更由衷的飛翔感受那延遠的空氣。”[2]849-850
里爾克很快提出了他的看法:“唉,他們只是在用對方掩飾自身的運數。”在戀人的對話中,雙方尋求著對方的聲音來“掩飾”著個人的蒼白,戀人們依舊要面對人類所處的被語言闡釋的世界,只是“在愛的瞬間,愛的對象遮蔽了這個現實,但這種遮蔽只是暫時的”[7]61。作為動物的再次在此處出現,里爾克認為鳥還能夠用自身持有的飛翔能力去感受更豐富的“延遠”,戀人們應當像鳥一樣,將視線從戀人對象上移開,而看到“我們呼吸著的空間”。在里爾克那里,“偉大的愛者”往往擁有一種不及物的愛,她們愛的對象往往沒有一種具體性,而是“從某個愛的對象那兒解脫,超越他……面向敞開”[7]68。
“……向你們我探問我們。/……但是,你們承受/第一道目光的驚恐與窗邊的渴望,/還有那第一次同行,一次花園里的漫行:/戀人們啊,這時還會是你們嗎?你們彼此/將自己舉到對方的嘴邊——:飲料對著飲料:/啊這時吸吮者何竟異樣地逃離了行動!”[2]857
里爾克其實依舊肯定了戀人們接近真實的可能,并且也認為能夠向戀人的存在狀態來“探問”我們的存在,但他仍提出了他的憂慮,關于這種“合二為一”的關系的持久性與確定性。里爾克看到了戀人們能夠從雙方充滿愛意的愛撫中感受到一些永恒,“在遮掩的地方”(即第一哀歌中所說“用對方掩飾自身的運數”)戀人們能夠“覺察到純粹的延續”,這是戀人們依靠雙手合十的姿態接近了一種合二為一的整體性,似乎時間在愛意纏綿中消弭而具有了瞬間的永恒;“但是”,里爾克以轉折打破了這一夜晚的烏托邦:他讓戀人們回憶那些愛情中的“第一次”的異樣時刻,再想想經受了這些時刻后的自己:“這時還會是你們嗎?”在熾熱、狂烈的愛情漩渦般經過后,難道戀人們可以保證自己不會發生改變?里爾克指出了戀人相互依偎關系的短暫、不確定。在現代主義作品中常常能看到無法持存的戀情,這與背后個體主義的現代經驗直截相關,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的隱憂》中談及個人主義時指出:“我們受害于激情之缺乏……人們因為只顧個人生活而失去了更為寬闊的視野。”[8]哪怕我們置于相互依存的親密關系中,現代人的個體化、原子化境遇也很難改變。
盡管在第二哀歌中,里爾克對戀人們的生存狀態做出了以上的反駁,但這樣的反駁更像是為了引出對于我們作為個體的生存困境的闡述,其實,“戀人們”是里爾克筆下具有接近“彼處”力量的人類形象。在第五哀歌的結尾,里爾克構造了一種關于戀人的理想場景:“天使會有一個廣場,我們并不知道的,在那里,/在不可言說的絨毯上,戀人們在展現此處/從未成為能夠的、他們/心之跳躍勇敢而更高難的造型……”[2]871這是里爾克關于戀人形象美好的希冀之一,盡管里爾克在戀人的行動中嗅到了諸多矛盾,但他也希望戀人們通過人與人之間聯系的構造與結合邁出接近精神超越的一步。
三、結語:未來屬于敞開者
里爾克在《杜伊諾哀歌》中通過對“它不再認識神殿”的思索與對天使、戀人、孩童、動物等意象的描寫,對個體存在和人類命運進行叩問,認為“我們的棲居不太可靠”。在詩歌中,里爾克最終提出:我們這些“無以復加的逝者”應當擔負起轉化大地的使命,只有通過將人類的命運置入作為存在者之整體的存在中,成為“敞開者”,人才能貫通生死之領域,可靠地棲居于大地之上。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以其復雜的象征,充滿神秘氣息的語言展現了基于愛、痛苦和死亡基礎上的美與崇高,用包含質疑的痛苦語調敘說大地之上詩意存在的人類經驗,昭示了人類超越的可能性。
通過細讀《杜伊諾哀歌》文本,體會里爾克宗教式語言下的批判性,我們能夠更加明晰地體悟里爾克的書寫實踐,以及里爾克關于人的存在、現代人的處境和對“整體”與“敞開”的追求的這些詩學思想在當代的哲學與詩學意義。“在貧困的時代里,詩人何為?”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典的詩性言說文本,深入《杜伊諾哀歌》的世界,我們會對里爾克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自身的時代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參考文獻:
[1]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M].徐大建,張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5.
[2]里爾克.里爾克詩全集:第1卷[M].陳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3]馬丁·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5]雷·布拉西耶.虛無的解縛:啟蒙與滅盡[M].聶世昌,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
[6]汪民安.現代性[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14.
[7]里爾克.蔡小樂,撰.《杜伊諾哀歌》箋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8]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M].程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24.
作者簡介:
沈卓成(1999-),男,浙江德清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