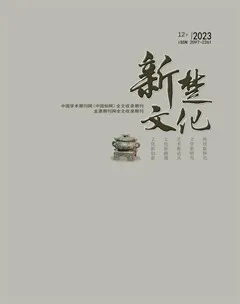《詩經》“雞鳴”意象之探析
【摘要】“雞鳴”意象最初產生于《詩經》。檢點《詩經》文本,共有四首詩涉及此意象,但因作者描寫對象、生活背景和情感寓意等不同,詩篇的“雞鳴”意象也表現出不同的內涵特征趨向,其中《鄭風·女曰雞鳴》以雞鳴報時交代時間,《鄭風·風雨》以風雨中的雞鳴起興,《齊風·雞鳴》體現了雞鳴的向純人文化的表達,《小雅·庭燎》則完全是“雞人呼旦”禮樂制度的內涵體現。“雞鳴”作為具有豐富內涵的意象,在《詩經》中已初步構建成功,并在后世的文學創作中得到豐富和純化。
【關鍵詞】《詩經》;“雞鳴”意象;報時;起興;人文意涵
【中圖分類號】I222.2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36-0017-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3.36.005
雞作為農耕社會的家禽之一,其雄雞旦午而鳴的特性在先民的生活中顯示出特殊意義,它們在歌詠中被賦予了不同的文化內涵。《詩經》作為先秦農耕時代記錄生活的百科全書,也是文學意象的源頭之一,而本文論述的“雞鳴”意象也為其中之一種。《詩經》中共有三篇詩歌較直觀地涉及“雞鳴”意象,分別是《鄭風·女曰雞鳴》《鄭風·風雨》和《齊風·雞鳴》,而《小雅·庭燎》雖未直面雞鳴一詞,但其表達得卻是“雞鳴”意象的內涵。
一、《詩經》中“雞鳴”意象的發生基礎
(一)“雞鳴”意象自然發生基礎
《詩經》時代已進入典型的農耕社會,因為是定居生活,先民們飼養家禽,而雞則為常見家禽之一。最初人們便將野生的原雞馴化為家雞,人們對雞的馴化過程也是對其生活習性不斷了解的過程,人們在飼養過程中發現公雞有定時打鳴的習性,具有一定的表時功能。
公雞之所以會按時打鳴,是其具有溝通陰陽的稟賦,它的鳴叫總是處在陰陽之氣的交會點上。午夜正是陰盡而陽起之時,雄雞鳴也。所謂“雄雞一唱天下白”,一天之正午,正是陽極而陰起之時,雄雞鳴矣。
古詩記錄此現象較多,如北宋歐陽修的“雞啼日午衡門靜”,南宋范成大的“轉午雞啼日正長”,清王士禛的“日午聞啼雞”等。正是雄雞這種溝通陰陽的屬性,古人在祭祀時,雄雞才會被作為祭品使用。雄雞除晨午啼鳴之外,在其他時間覓食、呼伴、驚恐等也會鳴叫,但其發聲明顯沒有晨午時氣足力滿。
古人熟知雄雞報曉的自然現象,將雞命名為知時鳥、司晨鳥,如《說文解字》中“雞,知時畜也,從隹奚聲”,《玉篇》中“雞,結兮切司晨鳥”,這兩部辭書就是從雞的自然屬性對“雞”字進行定義。清晨的一聲雞鳴,它不僅是農耕社會勞動生產的時鐘,也是農耕社會居家生活的時鐘。
(二)“雞鳴”意象社會發生基礎
農耕社會,先民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太陽的東升西落成為人們判斷時間的主要方式之一,但人們并不能在天氣變化的情況下還能依據日出和日落來確定時間。故智慧的先民將雞鳴時間和生活勞作時間相關聯,總結出一套計時方法,以雞鳴關聯日出作為起床勞作的開始。
另一方面雞鳴又與先民飲食的定時性有密切聯系,古人日食兩餐,早餐稱朝食,一般在晨雞鳴叫之時,開始做飯,故《禮記·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午餐稱哺食,在正午雞鳴之時。古人過午不食,故日食僅兩餐。所以雞鳴是兩餐時間的提醒。
當如上所述,這些都是“雞鳴”意象社會發生基礎。“雞鳴”意象的社會發生基礎形成是其在自然發生基礎上不斷人文化的結果,也是“雞鳴”這種自然現象被人文化后,便賦予了人的色彩。
二、《詩經》中“雞鳴”意象的內涵分析
“雞鳴”意象發端于《詩經》,其內涵大致包括報時和起興、人品之喻和人文儀式等。以下試析之:
(一)報時意味
報時是《詩經》“雞鳴”意象的基本內涵,但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常常與其他內涵糅合一處。《詩經》“雞鳴”意象涉及報時意味的有《鄭風》中的《女曰·雞鳴》和《風雨》。
1.《鄭風·女曰雞鳴》之報時意味
該詩首二句“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其中的“雞鳴”和“昧旦”就是計時專用名稱。詩中“雞鳴”是丑時,而男子口中的“昧旦”則是寅時。雖然《毛詩序》謂:“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朱熹《詩集傳》也認為“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就是說,這里的雞鳴在涉及報時意味的基礎上蘊含有其他意味。但不管怎么說,其他意味是產生于報時這一基本含義之上的;沒有這一基本意義的存在,其他意涵也失去存在的前提。故報時意味是該詩“雞鳴”意象的基本意涵。
2.《鄭風·風雨》之報時意味
《風雨》采用了《詩經》常用的一唱三嘆、反復吟詠的方式,三次寫到雞鳴——“雞鳴喈喈”“雞鳴膠膠”“雞鳴不已”。其“喈喈”“膠膠”有人解釋為“雞呼伴的叫聲”,這并不吻合風雨環境中雞鳴的常識。一般而言,在惡劣的環境中,雞受到壓抑會停止覓食和呼伴,更不會隨意鳴叫;只是在特殊時間段——天亮和中午才會按時而鳴。故“喈喈”“膠膠”為公雞按時而啼的晨鳴與正午之鳴。正如《毛詩序》所言:“《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也。”這里的“不改其度”就是指雞鳴的晨、午守時,有著不因風雨而改變的執信。總之,《風雨》的雞鳴也和《女曰雞鳴》的雞鳴一樣,其基本意涵是“守時而鳴”。
(二)起興意味
《詩經》在使用“雞鳴”意象時,往往不獨是單純地指稱“守時”,而是在報時意味的基礎上兼帶其起興意味。
先看《女曰雞鳴》,聞一多稱:“《女曰雞鳴》,樂新婚也。”其實,由于論者的時代背景和話語立場不同,歷來學者對此詩有著不同的解讀。筆者認為,此詩中“雞鳴”的主要涵義,除女子聽到雄雞報曉催促丈夫起床勞作外,也暗示了女子為勤儉治家之人。在詩中即有“起”之意,又有“興”之實。
再看《風雨》,其首二句的風雨、雞鳴,既是現實場景述說,又富含起興意味。這些多重意味兼具的興句,交代出一幅寒冷陰暗、雞聲此起彼伏的圖景。詩以風雨為題,三寫雞鳴,以烘托君子的品性和作者的心情變化。盡管此詩中的雞鳴正常情況下是用以報時的,但在這里它又多了一層象征君子不改其度的意涵。《鄭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這樣,“風雨”便象征亂世,“雞鳴”的守時,便象征了君子不改其度的氣節,“君子”則由“夫君”之君變成為德高節貞之君子。所以后世許多士人君子,常以雖處“風雨如晦”之境,仍要“雞鳴不已”自勵。“雞鳴”這一特殊意涵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直流傳至今。這首詩中的雞鳴,可以看作是所期之君子盼而終至這一行為的注釋,即從詩的起興中,就已暗示了詩的主題內容表達。
(三)人文意涵的增衍
隨著人們對雞動物屬性的了解不斷深入,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動物和人具有的相同屬性進行類比。《韓詩外傳》卷二載:“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守時不失正體現了雞的“信”,鄭《注》曰:“雞,取其守時而動。”正因為雞鳴具有這樣的品性特征,因而它直接導致了周禮中雞人呼旦儀式的產生。據《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周代有雞人之職,“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一人”。“雞人”的主要職責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詩經·小雅·庭燎》中的“雞鳴”,盡管該詩沒有出現“雞鳴”物象,但卻反映了雞人呼旦的具體過程。詩中的“庭燎”其實是指古代宮廷中立于地面的火炬。胡承珙《詩經后箋》指出:“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由此可知,詩中問夜之早晚者當為天子,“君子”應指諸侯。從詩的內容可以看出,各方君子由遠及近向朝堂趕來。根據宋朝學者王質考證:“此當是執事之人,夜未央晨未艾而聞車音,夜向晨而見旗色,嘆夜漏之未盡而朝臣已集也。”因而詩中“夜如何其”“夜未央”等句“恐是殿庭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與問答之詞”。
據《史記·歷書》記載:“雞三號,卒明。”周代雞人報時是與雞鳴時間相一致的,所以雞人有“夜必三呼”的做法。據《鄭箋》:“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所以《庭燎》詩文中的“夜未央”“夜未艾”“夜鄉晨”對應了子夜、雞鳴和未旦三個連續的時刻,對應正是雞人呼旦三次報時的時刻。所以說它是周代雞人呼旦情景的真實反映,是“雞鳴”意象的純人文表達。
再如《齊風·雞鳴》,該詩與《庭燎》不同,雖是反映雞人呼旦,但卻有鮮明的“雞鳴”物象出現。全詩以夫妻間的對話而展開,從“朝既盈矣”“朝既昌矣”詩句中可看出,“雞鳴”是與男主人公的“朝會”活動相關,而男主人公應是上朝之人。就詩中的“雞鳴”而言,非雞人呼旦之意無已解釋。雞人通過仿效雞鳴,報時警告,督促人們及時起床。所以詩中“雞鳴”意象也體現了它的純人文表達。
綜上所述,《詩經》中的“雞鳴”意象的內涵具多元性,在周代濃厚的農耕文化背景下,《女曰雞鳴》是純自然的雞鳴之聲,為表時之意;《風雨》是以“雞鳴”起興,賦予了作者的情感色彩,顯示出其向人文化過度的趨向;《雞鳴》同樣也是以“雞鳴”起興,也體現了其向純人文表達的過渡;而《庭燎》中的“雞鳴”意象是真正人文化地表達。
三、《詩經》中“雞鳴”意象在后世文學中的延展和純化
“雞鳴”意象產生于《詩經》,它具有強烈的農耕社會情節,故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中,其意象在文學史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其內涵也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純化。
(一)兩漢至六朝:“雞鳴”意象的豐富期
在漢代,《詩經》中“雞鳴”意象是作為意識形態來解讀的,它影響了一部分階層;同時漢代詩歌文本及作者階層的豐富,是“雞鳴”意象得到充分發展的前提條件。據統計,《漢書》共出現“雞鳴”十二次,《后漢書》也出現十次。由此看來,“雞鳴”在漢代出現的頻率還是較高的。不僅如此,其“雞鳴”意象內涵也得到進一步的豐富。
如東漢班固的《詠史》,這首詩敘事凝練,敘述了緹縈上書救父、感天動地的“至情”,足以使晨風為之傳頌,讓漢文帝深受感動。詩中“思古歌雞鳴”的“雞鳴”意象,作者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使用其涵義的,意指小人當道、忠臣沮折。這也是對“雞鳴”意象內涵進一步地豐富。
又如西晉陸機的《赴洛道中作(其一)》,這首詩描寫了詩人在旅途中的心情和所見的景物。詩的前四句描寫了詩人辭別親人,離開家鄉;由“詠嘆遵北渚”到“野途曠無人”描寫了詩人的憂思,一路上充滿了嘆息和心中滿載著憂愁;由“山澤紛紆馀”到“孤獸更我前”,詩人對山川和草木的景物描寫,旨在烘托“虎嘯”“雞鳴”“哀風”和“孤獸”,故自然景和物的描寫是令人恐怖的,暗示了詩人赴洛陽途中忐忑不安的心境。此詩中“雞鳴高樹顛”中的“雞鳴”既有報時的意味,也含有警醒之意,體現了作者此時戰戰兢兢的驚恐狀態。
(二)六朝后“雞鳴”意象漸趨純化
隨著“雞鳴”意象禮樂制度意義的逐漸淡化,“雞鳴”意象的內涵雖然在漢代至六朝得到一定的拓展,但此后并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只是保留了其中一部分內涵,如司晨午報時等。六朝后,“雞鳴”意象的內涵開始向本初回歸。如唐代杜牧的《早行》,此詩中的“雞鳴”再次回歸到其意象的初始內涵。再如宋代王觀的《早行》,詩中的“雞唱催人早”,也是體現“雞鳴”意象的報嘵特征。元末明初高啟的《雞鳴歌》,詩中“萬家夢破一聲雞”也同樣表達報時意涵;與其相類的還有清代李漁《早行》,這里的“雞鳴自起束行裝”也僅具報晨功能。
以上為雞鳴司晨,再就午時雞鳴聊舉兩例。再如宋代歐陽修的《叔平少師去后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遍綠苔,西堂瀟灑為誰開。
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
雞啼日午衡門靜,鶴淚風清晝夢回。
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名籍在蓬萊。
該詩所寫之積雨荒苔,日午而衡門雞啼之景,主人之簡齋陋室,唯能與道士相往來。雖至日中,而門之客尚無。此處“雞鳴”則是正午報時意涵。雖然報時之雞鳴襯托午時橫門荒庭之靜,表達其寂寥傷心之感,但“雞啼”本身卻是單純的報午之意。
可以看出,唐宋以來“雞鳴”意象未增添新的內涵。即使偶見如元代周巽的《雞鳴高樹顛》,“雞鳴”為表達其奮發向上精神狀態,也仍然僅是對漢“雞鳴”意象內涵的繼承。總之,六朝后“雞鳴”意象內涵并未得到拓展,而是總體趨于萎縮和純化的趨勢,更多的只是保留了報時意涵。
四、結論
雞作為一種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家禽,“雞鳴”自然也被賦予了人類的情感,引入詩歌中便成為一種人與自然相溝通的意象。《詩經》中的《鄭風·女曰雞鳴》《鄭風·風雨》《齊風·雞鳴》和《小雅·庭燎》恰是以賦比興的手法,借助了“雞鳴”意象內涵的表達,才體現出詩人豐富的情感。正是“雞鳴”意象凝聚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帶著特定的時代印記,才對后世文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尤以漢代與六朝,其內涵還得到了豐富和發展;盡管后來其內涵在文學上漸趨簡約,但其意象仍然是詩人筆下表達情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參考文獻:
[1]李賀.李賀詩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9.
[2]逸凡,點校.唐宋八大家全集:第4卷[M].廣州:新世紀出版社,1997.
[3]陸放翁,等.宋元明詩三百首[M].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69.
[4]王金平,鄔小輝,主編.江右書院行之詩文[M].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9.
[5]梁青.“雞”及“雞”參構詞語的語義分析及文化闡釋[J].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6.
[6]許慎.說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陳彭年,等.宋本玉篇[M].北京:北京中國書店,1883.
[8]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1.
[9]詩經[M].王秀梅,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10]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11]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M].成都:巴蜀書社,1996.
[12]陳戍國.周禮·儀禮·禮記[M].長沙:岳麓書店,2006.
[13]胡承珙,撰.毛詩后箋:下[M].郭全芝,校點.合肥:黃山書社,1999.
[14]王質.詩總聞:卷1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作者簡介:
胡賽麗(1984.9-),女,漢族,安徽東至人,本科,講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及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