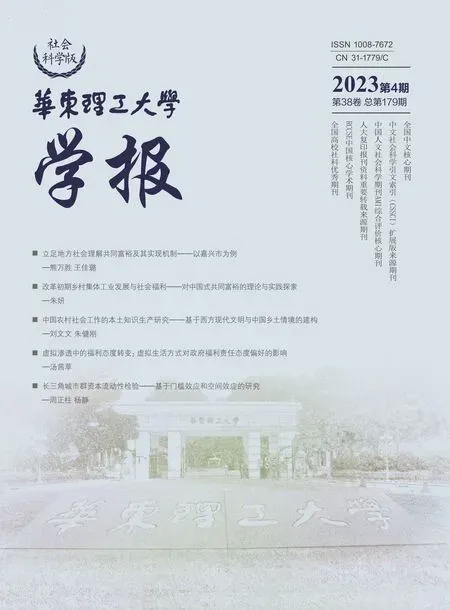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的本土知識生產研究
——基于西方現代文明與中國鄉土情境的建構
文/劉文文 朱健剛(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 300350)
社會工作的產生和發展是西方工業化進程中“公益慈善科學化”的重要后果,其知識體系具有西方文明的顯著烙印。①陳濤:《社會工作專業使命的探討》,《社會學研究》2011 年第6 期。②朱健剛、劉文文:《“科學公益”的社會建構:模型、話語與范例》,《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2 年第5 期。作為一個舶來品進入中國,社會工作順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脈絡,往往是在城市中進行學科建設和開展實務工作,缺少聚焦鄉土情境的討論。在中國,農村的治理與建設始終受到關注。無論是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還是如今的鄉村振興戰略,都是基于中國鄉土的實踐嘗試。在如火如荼的農村建設過程中,社會力量的進入打破了僵化的發展模式,探索另類發展道路。社會工作是作為社會力量參與發展的重要抓手,在開展農村工作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發展模式,并產生了基于本土情境的實踐知識。
農村社會工作本土知識體系的建構存在一個基礎性假設,我們需要討論的是社會工作是不是普適性的話語和行動。①徐選國:《中國社會工作:話語建構與本土知識生產》,《社會與公益》2020 年第10 期。當前,關于這一討論形成了“社會工作全球化”與“社會工作本土化”兩種主張。支持“社會工作全球化”的學者認為,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價值導向的專業,其本身蘊含的自尊、平等、賦權等理念是跨越民族和國界的,而且社會工作主張的“專業敏感性”正是對情境差異性的回應。倡導“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學者則認為,以西方模式為主導的社會工作在廣大非洲、亞洲和南美洲等國家大肆發展,其實質是一種政治殖民和文化霸權,是少數精英利用已取得的知識權力和政治權力,在無視各國本土情境差異性基礎上的一種入侵。這兩種話語基于對社會工作是否具有普適性的判斷,形成觀點截然相反的兩個流派,對社會工作的發展路徑持有不同的主張。本文認為,社會工作的全球化與本土化實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不應將其完全對立或割裂開來,要在吸納基本價值理念的同時探索本土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建構。
事實上,人類社會日益打破地理區隔而聯結成為一個整體,在此背景下,同類型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存在較強差異性,所以社會工作如何應對并建立有效的專業知識來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是當下面臨的重要的挑戰。社會工作知識體系起源于古希臘和基督教傳統,與團體格局的西方社會具有較高的契合性。而中國則具有明顯的差序格局色彩,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呈現出講“人情”“面子”“關系”的熟人社會形態。社會工作在中國農村的發展逐漸不再局限于個案、小組、社區三大傳統方法,而是依托鄉鎮社工站鏈接多方資源、動員多方力量共同推動鄉村建設,形成了基于中國鄉土情境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故此,本文梳理了近代鄉村建設運動的典型模式,總結了當代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經驗,旨在分析影響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形成的要素,并探討其背后的生成機制。
一、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發展的背景
某一具體知識體系的建構常常受到政治權力、經濟水平等社會背景的深刻影響。在關于社會工作發展的討論中,一個重要的議題便是其政治屬性。②Craig G.“,Poverty,Social Work and Social Justice,”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32,No.6,2002,pp.669-682.③Ioakimidis V.,Santos C.C and Herrero I.M.,“Reconceptualizing Social Work in Times of Crisis:An Examination of the Cases of Greece,Spain and Portugal,”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7,No.4,2014,pp.285-300.④Payne M.,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UK:Palgrave Macmillan,2014,pp.27-31.我國的農村建設運動,不同階段的情況映射出中國社會的起伏動蕩,是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交互介入國家建設的縮影。不同歷史階段的鄉村建設運動既具有時代特色,也具有我國鄉村社會的特質,存在一定的共性。其建設經驗可為當代農村工作提供重要的實踐知識。
早在19 世紀60 年代,晚清政府便開啟了現代改良運動,鄉村淪為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被遺棄的對象。①沈費偉:《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流派:興起背景、經典案例與經驗啟示》,《理論月刊》2019 年第5 期。到了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動亂的時局不僅未能有效緩解社會矛盾,還進一步加劇了鄉村衰敗的趨勢,激化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矛盾。鄉村的衰敗在當時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方面,鄉村內部的結構極度不合理,少數地主掌握著絕大多數土地資源,農民遭受到殘酷的壓榨與剝削;另一方面,西方入侵使廉價工業品涌入,打破了小農自給自足的狀態,傳統的鄉村體系趨近于崩潰。
鄉土社會有自成體系的運轉邏輯,熟人社會的“互惠機制”融匯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對于該場域內“默會知識”的掌握使得村民對周遭事物有獨特的理解與認知,并以之規范自身的行為方式。西方文明對鄉村固有的內部秩序產生的沖擊,加劇了中國鄉村的失序與解體。以“科學”與“理性”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內生的本土文化在霸權的影響下逐步喪失了活力,成為“封建”與“落后”的象征符號,部分村民甚至產生自我矮化的心理。不同于西方,中國的鄉村是一個“關系社會”,遵循著“行動倫理”的邏輯原則②周飛舟:《行動倫理與“關系社會”——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社會學研究》2018 年第1 期。,現代文明的進入需要在情境中完成自身的本土化。在親疏遠近決定個體行為取向的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是一種波紋狀的差序樣態,并且是由其固有的宗族關系決定的。換句話說,這樣的社會結構與村民的關系網絡是交織在一起的,很難被打破,外部力量介入只能觸及其表面。如果西方涌入的“民主”“平等”現代思想未能與中國的“關系”社會相交融,只是聚焦于形式上的公平正義,不但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反而會造成“不中不洋”的畸形發展。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一批具有愛國熱忱的知識分子致力于拯救中國的農村,投身于鄉村建設運動。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農村發展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為后世留下了鄉村治理的寶貴經驗,同時也為當代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開創了本土化的實踐先例。
當代社會工作的發展帶有教育先行的特征,然而教育先行并不必然帶來教育引領。③鄭廣懷:《教育引領還是教育降維:社會工作教育先行的反思》,《學海》2020 年第1 期。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開始重建,但發展緩慢。④王思斌:《社會工作人才培養與鄉村振興發展報告》,載楊團主編《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2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235-256 頁。進入21 世紀以來,社會工作的學科建設逐漸體制化、規范化,并隨著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社會工作的發展迎來了“春天”。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首次提出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的意見⑤《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社北京2006 年10 月18 日電,http://www.gov.cn/test/2008-08/20/content_1075519.htm,最后檢索時間:2023 年2 月3 日。,農村社會工作隨之興起。2017 年8 月,《民政部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關于支持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指導意見》進一步規劃了社會工作參與鄉村建設的具體路徑。①民政部、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民政部、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關于支持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指導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17-08/19/content_ 5218659.htm,最后檢索時間:2023 年2 月3 日。隨后,相繼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意見、法規,提出了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在鄉村振興中引入社會工作人才、積極發展農村社會工作、推動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等意見。在行政介入與學科建設的推動下,農村社會工作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然而由于頂層的規劃與體制內的教育和農村實際情況存在較大的差距,因而農村社會工作難以滿足鄉村社會的實際需求,急需一套本土化的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百年來中國農村地區差序格局的底色并未褪去,仍講究“人情”“面子”“關系”,并且注重家的概念。②焦若水:《家的復歸與賦權:農村社會工作整合發展的文化基礎》,《甘肅社會科學》2021 年第2 期。③鄧鎖、李斐:《照顧關系的賦權與重構:基于陜西北村的社會工作實踐研究》,《社會工作與管理》2021 年第1 期。④Johnson Chun-Sing Cheung,“Social Work Guanxi:A Reflexive Account of the Social Work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Context,”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0,No.3,2016,pp.101-111.同時我們也發現,鄉村的社會結構是動態變化的。改革開放后,個體從無所不包的“總體性社會”中脫嵌出來,呈現“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趨勢。⑤吳理財:《論個體化鄉村社會的公共性建設》,《探索與爭鳴》2014 年第1 期。我國鄉村長期以來形成的熟人社會,隨著工廠時代和工地時代的來臨而接近崩離,城鎮化和手機社交將農村的親密感進一步沖淡⑥伍娟、姜萍:《多重增能:社會工作參與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與專業反思》,《懷化學院學報》2019 年第4 期。,傳統的以人情為紐帶進行維系的格局趨弱。在這樣的情境中,我國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傳統的以人情為紐帶的鄉土秩序趨于解體,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深受西方理論體系影響的社會工作如何在這樣的情境中完成本土知識體系的建構,讓農村社會工作成為“盤活”鄉村力量的新手段,使傳統的“鄉土性”“宗族性”與現代的科學理性交融發展,是新時代面臨的新挑戰。
二、農村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基礎
社會工作誕生于工業化推進的過程中,具有西方文明的烙印。它作為一門正式專業進入中國僅短短幾十年,在吸收西方系統化理論知識體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鄉土實踐,不斷進行著本土知識的生產。在此之前,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也積累了一定的鄉村建設實踐知識。鄉村建設運動有三個典型代表:晏陽初主持的華北平民教育運動、梁漱溟開展的鄉村互助和文化建設運動、盧作孚在重慶創辦的鄉村現代化建設。總結而言,這三大模式是以精英群體為主導的,是在當時凋敝的鄉村環境中探求發展的實踐嘗試。其建設經驗可為當代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實踐知識。
傳統鄉村社會的治理,強調通過禮俗教化的方式完成內部秩序的恢復與重建。晏陽初主持的華北平民教育運動著眼于教育,希望通過對平民的“教化”來改善當時鄉村凋敝的現狀。1926 年,晏陽初率領一批有志之士“走出象牙塔,跨進泥巴墻”,在河北定縣安家落戶,開創了“平民教育—鄉村科學化”的建設模式。晏陽初把中國農村問題歸結為“愚”“窮”“私”“弱”四大類別①程美琪、黃瑩:《歷史、經驗與路徑:農村社會工作參與鄉村振興研究》,《知與行》2020 年第1 期。,并提出用四大教育解決這些問題,即用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攻窮,用公民教育攻私,以衛生教育攻弱②彭秀良:《守望與開新:近代中國的社會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77 頁。。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整套鄉村建設方案,主張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大方式并進,實驗研究、分類培訓、表證推廣三項科技工作有序推進,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整體實施的思路。晏陽初主導的鄉村建設模式,是把當時的西洋文明與中國的鄉土國情相結合的典型樣本,試圖通過現代化教育解決農村固有的積弊,呈現出中西文明交融的特征。但這一模式忽視了鄉村傳統的自我組織動力,存在過于理想化的色彩。
與晏陽初對現代文明高度重視不同,梁漱溟主張“老樹發新芽”,即通過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并融入推動發展的新元素來振興鄉村。他認為,鄉村的衰敗是由于西方文明對于傳統文化的摧毀,尚未建立起適用于本土情境的新文化。鄉村建設除了重視經濟扶持,著力開展鄉村救濟運動外,還要重視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積極創造新文化。梁漱溟希望通過建立鄉約來重構儒家的理想社會。他受到宋代呂大鈞《呂氏鄉約》的啟發,設置了鄉約內容的“四大項”,并提出鄉村建設的四個階段:鄉村組織、政治問題、經濟建設、理想社會。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念蘊含著一種文化多元性的倡導與對社會現代性的批判。他反對一味強調“以西洋文明救中國”的理念,否定單獨以經濟發展速度作為評判的尺度與標桿,不能因為西方社會的快速現代化就將其制度簡單地移植到中國。他在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的基礎上,主張注重情義關系、追求職業平等、強調農民自覺和社會系統化發展。這些思想對今天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發展仍有很大的啟發。③張央央、郭占鋒:《論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對農村社會工作的啟示》,《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11 期。
相比較而言,盧作孚更為關注農村的經濟發展,通過興辦實業推動鄉村的現代化進程。他在重慶北碚開展鄉村建設實驗,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振興鄉村經濟。1926 年,盧作孚在重慶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翌年,他主持了四川省江巴璧合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一方面,他大力維護嘉陵江轄區安全;另一方面,又著手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經過幾年的實驗,他認為中國的根本辦法是“建國”,即“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要以鄉村的現代化建設為基礎,要趕快完成鄉村的現代化,以供中國“小至于鄉村大至于國家經營”的參考。④張秉福:《回眸民國時期三大鄉村建設模式》,《領導之友》2006 年第3 期。盧作孚對于鄉村現代化建設的理念從更為宏觀的脈絡看到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其關注點更多地落實到經濟層面,同時是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回應。
可以發現,以晏陽初、梁簌溟、盧作孚為代表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是以精英為主導的鄉村建設的嘗試,因引領者觀念相異,不同地區的實踐有各自的理論脈絡與發展維度。鄉村建設運動作為社會力量參與國家建設的積極嘗試,為外來者理解村莊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材料,同時也為當代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積累了實踐經驗。社會工作發軔于西方,其知識體系經歷了系統化的建構。就發展方向而言,大體分為兩個流派:其一,源于慈善組織會社,以治療取向為代表的“臨床社會工作”,主張從專業技術層面循證治療,是“問題視角”的分支;其二,以簡·亞當斯為代表的“結構性取向社會工作”,從社會環境入手分析貧弱者問題產生的原因,主張從資產建設的角度入手為受助者賦能,是優勢視角的分支。在當代,以精神分析理論、系統理論、賦權理論等為代表的社會工作理論為適應后現代社會的時代特點,在保留其理論合理內核的基礎上發生了范式的轉向,可有效回應中國鄉村社會轉型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為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21 世紀進入后現代主義時代①Gray M.and Webb C.,Social Work Theory and Metho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9,p.201.,復雜性、流動性、不確定性、自反性成為重要的時代特征②Howe D.,“Modernity,Postmodernity and Social Work,”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4,No.5,1994,pp.513-532.,社會工作領域也出現了理論的新發展。從關懷主義、關注價值取向擴展到對于科學理論的關注,在轉向中完成了人文關懷與科學邏輯的統一。③Francis J.Turner,“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A Trans-cultural Resource for Health Care,”Social Science &Medicine,Vol.31,No.1,1990,pp.13-17.系統理論、生態系統理論、優勢視角、增強權能等逐漸在社會工作領域內興起,這些理論逐漸從聚焦微觀發展到對中宏觀層面結構性因素的關注,不再僅僅以診斷的邏輯把問題歸因于個人,同時論及制度性因素,為分析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社會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也使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不局限于傳統的三大方法,可從發展的脈絡尋求新的介入方式。
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的相關性④Sibeon R.,Towards a New Sociology of Social Work.UK:Avebury,1991,p.108.,對理論的賦權與承認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工作獲得合法地位的基礎。當下關于社會工作理論的研究多聚焦于概念歧義的辨析、理論脈絡的分析、倫理議題的討論以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等方面。⑤Hicks S.,“Theory and Social Work:A Conceptu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l.25,No.4,2016,pp.399-414.一直以來,精神分析理論都是“臨床社會工作”的重要支撐,并處在動態發展中。⑥Horowitz J.,“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Work Theory,”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Vol.26,No.4,1998,pp.369-383.在社會工作發展之初,診斷的邏輯占主導地位。其以關注人的本能為焦點,強調“性”與“原欲本能”,以此為根據探尋服務對象問題的根源。隨著時代的發展,精神分析理論產生了范式的轉向:埃里克·埃里克森、弗朗茨·亞歷山大、羅伯特·懷特等學者都曾論及“關系爭議”問題,并將其內核注入精神分析理論。此外,20 世紀50 年代沙利文提出精神分析之人際關系方法、20 世紀80 年代涌現出米勒的關系文化理論和格林伯格、米切爾的精神分析關系學派、21 世紀格根心理學的關系本體論,都呈現出精神分析理論在當代的關系轉向。①何雪松、王天齊:《社會工作的關系思維:三個傳統與新的綜合》,《新視野》2021 年第6 期。“關系思維”成為社會工作理論發展的重要方向,這與中國鄉村場域自身運轉中對“關系”的重視是不謀而合的。
系統理論則主張,個體的問題是由功能不良的社會系統運行模式導致的,是不同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以盧曼和保羅·瓦茲拉威克為代表的系統理論被視為一種建構主義理論,主張采取現實的立場直面社會問題,而現實的立場是系統中的個體通過觀察建構的。②Werner Schirmer and Dimitris Michailakis,Systems Theory for Social Work and the Helping Professions.London:Routledge,2019,p.47.生態系統理論則在系統理論的基礎上更重視外部環境對個體的作用。尤·布朗芬布倫納關注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強調把個體放置在其生存的生態環境中分析行為產生的根源。③馬富成、馬雪琴:《尤·布朗芬布倫納的發展生態學理論與幼兒親社會行為的養成》,《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1 年第4 期。查爾斯·扎斯特羅則主張個人系統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通過使兩者協調來促進個體的成長。④Charles H.Zastrow,Karen K.Kirst Ashman,Understanding Human Behavior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Thmson Brooks Cloe,2004,p.97.優勢視角的擁護者主張社會工作應該改變看待世界的框架,對以往的“病態世界觀”作出調整。薩利比指出,社會工作既有框架中的“病態學詞匯”代表著一系列對困境個體的不利假設,這些假設會導致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面對更糟糕的境況⑤Dennis Saleebey:《優勢視角——社會工作實踐的新模式》,李亞文、杜立婕譯,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108-110 頁。,隨后他提出了聚焦優勢的尋解治療、增強抗逆力和建構優勢的方法。這些社會工作理論均呈現出分析視角的結構化轉向,為從根源上解決社會問題、緩解個人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以精英分子為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呈現出較強的引領者主導的趨勢,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其扎根基層的實踐活動是社會力量進行國家建設的重要嘗試,為當代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實踐知識,可借此進一步分析與探索中國精英群體百年來在鄉土情境中的互動方式,為當下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指明方向。當代西方社會工作知識體系呈現出的“關系化”與“結構化”轉向,與中國鄉村的差序格局更為貼合,并且可以提供更為深入的分析鄉村問題的理論視角。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考察當下農村諸多問題的根源,為社會工作在中國鄉村的發展提供了另類的本土化視角。因此,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既要立足于鄉土情境,看到千百年來仁人志士的建設嘗試,從以往的實踐中汲取經驗,同時也要關注西方社會工作理論的當代轉向,借鑒其“關系化”與“結構化”的新視角,在此基礎上完成中國農村社會工作本土知識的建構。
三、中國農村社會工作本土知識建構的過程機制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農村都進行過各具特色的實踐嘗試。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與21 世紀以來的新農村建設都體現出各種力量在中國鄉土情境中的交互影響,并形成了各自的發展模式。在精英群體的引領下,不同地區的實踐呈現出明顯的個人化色彩,可以說引領者個人的觀念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行動的方向。不同取向的鄉村建設實踐,既是對西方現代化文明的引入,又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是基于本土情境的多元化交融。中國農村社會工作則在實踐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土特性的知識體系,其背后的生成機制與知識建構過程是本文討論的核心議題。
社會工作專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僅強調學理層面抽象化理論的發展,而且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需要系統化知識體系指引實踐,達成“應然性”與“實然性”的統一。其知識體系在實踐過程中被不斷建構與形塑,是宏觀世界發展格局中的構成部分,同時也受到當地情境與不同社會主體的影響,是多方因素交織互動的產物。
社會建構主義的興起標志著社會工作認識論基礎從過去的實證主義一元論轉型至多元范式競爭,對過去的主流認識形成全新的挑戰。①何雪松:《社會工作的認識論之爭:實證主義對社會建構主義》,《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1 期。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論具有復雜的構成,包含分屬不同學派、源于不同流派、具有表面的親和性但在內部又有重大差異的研究②李曉鳳:《社會建構論視角下的社會問題研究及其對社會工作的啟示》,《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 期。,不過其紛繁復雜的組成部分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強調知識的歷史和文化特殊性、知識的社會維系過程、知識與社會行動的交織。③Burr Vivien,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London:Routledge,1995,p.89.在社會建構論的視角下,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要在實踐中被不斷地生成,而在地文化與群族性的知識體系則是這個過程中需被重點考慮的因素。在實踐中產生和發展的知識也有賴于特定的社會設置和社會場景,只有把知識置于具體的情境和關系中才能理解其對人類行為與社會脈絡的重要意義。④Sayer Andrew,“Essentialism,Social Constructionism,and Beyond,”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45,No.3,1997,pp.453-487.
在政府主導和教育先行的現狀下,社會工作學院派的知識體系與實踐存在巨大張力。面對這種情況,社會建構主義為農村社會工作形成適合中國本土的知識體系提供了新視角與新思路。建構取向的社會工作擺脫了聚焦案主問題、不足、缺陷和障礙的治理模式,轉而關注和探究案主的意義、優勢、資源和潛能①王海洋:《邁向實踐范式的社會工作知識觀》,《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1 期。,從“循證治療”到“結構化視角”的轉向使得農村社會工作在中國的鄉土情境中有了新突破,不再僅僅局限于由西方傳入的三大工作方法,而是基于社區整體層面,關注結構性的缺失與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在建構主義詮釋法和辯證法的指導下,經過成形、修正及精煉的階段,研究者與參與者進行辯證的互動和對話,建構共識②Denzin N.K.and Lincoln Y.S.,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1994,p.32.,在多因素互動下生產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
(一)精英群體引導農村社會工作的本土知識生產
知識具有社會性特征的根源是其生成主體為社會中的人。社會場域中的知識都是在行動中產生和再生的,知識通過行動的定義來界定、修改和建構社會。③趙超、趙萬里:《知識社會學中的范式轉換及其動力機制研究》,《人文雜志》2015 年第6 期。建構論認為,知識的社會性包括知識與社會之間的決定關系與互動關系④黃曉慧、黃甫全:《從決定論到建構論——知識社會學理論發展軌跡考略》,《學術研究》2008 年第1 期。,不同的社會主體對于知識的生產具有外部決定作用,同時又受到生成知識的影響。韋伯指出,應當把具有主觀性的由個人展開的社會行動作為研究對象,開展“具有主觀意義的客觀分析”。⑤劉少杰:《國外社會學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89-105 頁。就這個層面而言,知識是具有一定主觀性的社會產物。也就是說,在實踐情境中概括出的知識體系帶有一定的個人主觀意愿色彩。
梳理不同時期的鄉村實踐活動,可以發現精英群體對于知識建構的引導存在普遍性。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精英群體主導著知識生產與實踐的方向。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無論是河北定縣、山東鄒平還是重慶北碚,都帶有濃厚的個人主觀色彩,個體的判斷決定著實踐的方向,同時也影響著基于實踐的知識體系建構。在晏陽初的主持下,定縣的鄉村實驗把問題根源歸結于農民群體自身的“愚窮私弱”,認為從教育入手改善群體的積弊便可拯救鄉村。作為大儒的梁漱溟將其復興傳統文化的主張在鄉村建設運動中進行了實踐,在傳統文化中尋找實踐活動的合理性,以此恢復鄉村社會內部的秩序。盧作孚則主張“實業救國”,以經濟建設為著力點,采取發展經濟的措施來振興鄉村。這三種建設模式各有側重,以個體的判斷為依據,建構出鄉村發展的“理想化”類型。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精英基于自身的立場和主張建構出一套引領運動實踐的“口號式”話語體系,其本質是實踐性知識。
在當代鄉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另類發展模式成為農村社會工作實踐的重要嘗試。⑥何宇飛:《新鄉村建設運動中的困境:另類商品化與合作勞動——基于華南某鄉村旅館項目的案例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17 年第6 期。沿承民國時期鄉村建設的脈絡,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與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中心在學者的支持下繼續運行。此外,以高校牽頭倡導的城鄉互助和公平貿易的農村建設在云南、廣東農村地區陸續開展。由高校知識分子牽頭推動的農村建設嘗試,是在“發展主義”脈絡下探尋鄉村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探索真正適合中國本土情境的農村社會工作模式,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本土化知識的生產,提出調解者社會工作、轉化/轉進社會工作、發展性或發展型社會工作等知識概念。①陳濤:《社會工作專業使命的探討》,《社會學研究》2011 年第6 期。
無可否認,精英群體懷以強烈的熱忱投身于鄉村建設,推動了農村地區的發展,并且也積累了一定的社會工作實踐知識。作為精英群體之一的知識分子具有充足的知識積累、較為敏銳的洞察力、明確的判斷力,并且可通過自身的影響力為農村地區引進外部資源。在實踐的過程中,社會工作者推動地方性知識的生產,積累了大量更為貼近在地村民生活的本土化知識。本土知識的生成,不盲從于學院派的知識體系,實質是對知識權威的解構,但更應該意識到引領者的外來身份屬性,避免對“新權威”的盲從。對于鄉村場域而言,知識分子無疑是“精英式”人物,往往自詡掌握著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扮演著教化的角色。這種灌輸式的知識生產方式存在弊端,缺乏發展主體自身的視角。②呂潔瓊、文軍:《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社區為本的情境實踐及其反思——基于甘肅K 縣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3 期。方向性的引領并不等于全局掌控,本土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仍應以在地居民為主體,警惕產生“落地難、想當然”等弊病。
(二)鄉土情境構建農村社會工作的本土知識
默頓主張知識是一系列的事實或見解,涵蓋從大眾信仰到實證科學的各種觀念和各種思想方式。③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唐少杰、齊心等譯,譯林出版社,2015 年,第209 頁。知識是根據規則構成的話語實踐,話語是隸屬于或來自同一構成系統,或者是從屬于不同領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規則的一套陳述,具有理性或非理性、科學或非科學等本質區分;話語同權力、策略同實踐網絡一同建構了社會事實。④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第75 頁。知識在保證其客觀屬性的基礎上,是人們與世界聯結的方式,具體知識來源于特定情境中的實踐。換句話說,基于特定情境的實踐建構了不同的知識體系。
本土化知識不僅僅是指時間、空間、階級和各種具象問題,也指與生俱來的價值觀、邏輯思維等地方特色⑤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瑄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年,第56-58 頁。,是對所發生事件的本地認識與對于可能發生事件的本地想象的復合體。⑥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載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鄧正來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年,第107 頁。情境對于本土化知識生成具有外部建構作用,知識是在現實的社會情境中產生、發展和傳播的,外部存在是知識產生的源頭。⑦彼得·伯格、托馬斯·盧克曼:《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吳肅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201 頁。中國的鄉土情境有其獨特之處,已有的研究表明如果僅僅用西方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孝”“報”“氣”等概念而不觸及本質,分析的結果只能是將這些觀念中的本土特征消解掉而已,并不能構成深入的認識。故在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構建過程中,鄉土情境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已有的實踐嘗試也可佐證這一論斷。
民國時期政治動亂、經濟凋敝,中國經受著“西洋文明”的沖擊。社會工作在當時由傳教士引入,并以服務社會為目的進行推廣。為了復興凋敝的鄉村,有識之士結合不同地域的特色對西方社會工作進行“改良”,是卓有成效的嘗試。當代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面臨“制度甚為關鍵”的話語體系和政治語境,“黨政領導”的社會工作是本土情境中的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模式。在黨領導一切的現實中,社會工作借助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多以項目化的運作方式進入農村。農村社會工作在實踐中便形成了一套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話語體系,借助“政府背書”的方式快速獲得民間承認。
萬載縣的農村社會工作與廣東的“雙百工程”便是典范。“萬載模式”是“以紅領專”型農村社會工作發展的代表之一,在政府助推下,打造了一個“神話”。萬載社會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曾火爆全國,贏得了社會工作“城市看上海,農村看萬載”的美譽①趙曉峰:《現代國家建構與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長白學刊》2015 年第5 期。,完成了從“試點”到“示范”的跨越。萬載縣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政府主導推動、公眾廣泛參與、廣大群眾受益的模式②陳曉平:《農村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新探索》,《紅旗文稿》2011 年第7 期。,呈現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社會工作組織網絡。萬載農村社會工作在當時獲得極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借助政府的力量,對政治資源加以合理利用。近兩年來在廣東地區如火如荼開展的“雙百工程”亦是在享受政府“制度紅利”基礎上的積極嘗試。在廣東省民政廳的支持下,社會工作者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零距離接觸打通了懸浮式體制下的“最后一米”③李偉:《農村社會工作參與鄉村振興:理念、模式與方法》,《河南社會科學》2019 年第8 期。④何雪松、覃可可:《社會工作參與鄉村振興的目標與定位:以城鄉社會學為視角》,《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3 期。,使政策真正落實到有需要的個體那里,成為鄉村地區“兜底”發展中的重要一環。
“萬載模式”和“雙百工程”既是基于中國鄉村情境的本土化社會工作實踐,又是建構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嘗試。基于中國的鄉土情境,建構本土知識的過程必須重視關系屬性與政治屬性,縮減理論知識與實踐之間的張力,同時要警惕這種依靠行政力量發展的社會工作易產生專業性危機——缺乏內生動力而難以可持續地發展。社會工作者要在發揮中國特色制度優勢的基礎上,結合西方社會工作系統化的理論體系,建構基于本土情境的知識。一方面,在“熟人社會”的鄉土情境中,村民常講親疏關系的重要性,而這樣的親疏關系和普遍正義往往存在張力。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就是在討論親屬關系本身的善。但是,善和正義并不總是一致的。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正是要使二者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恢復村莊的秩序。另一方面,在黨政領導體制下的中國社會對政府有天然的親和性與依附性,社會工作的介入既要認識到這樣的現實情況,配合黨政工作,又要保證自身的專業性。總之,基于在地情境的“關系屬性”與“政治屬性”是構建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重點考慮因素。
(三)全球化融通農村社會工作的本土知識體系
曼海姆指出,要把人類的認識活動放在社會歷史過程中考察,追溯知識在人類發展不同階段呈現的形態。①Mannheim K.,Ideology and Utopia.London:Kegan Paul Trench,1936,p.101.他指出,具有相同社會基礎的群體共同生產與生活,面對時代的挑戰,知識在群體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不斷產生。換句話說,客觀經驗、社會過程、物質條件、互動方式等外在因素影響著知識的產生。不同的政治體制、傳統文化、社會形態等因素形塑了差異較大的在地化文明。
在承認在地化知識具有差異性的前提下,我們同時應意識到人類在不同階段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正如開篇所提到的,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價值導向的專業,“平等、尊重、接納”等專業核心價值在人類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在社會工作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實踐可以為某些具有共性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法,只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歸納與總結,才能提煉出適用范圍較廣、具有普適性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
在當代中國鄉村振興的背景下,農村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建構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統一。作為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產物,社會工作的賦權、文化敏感性、優勢視角等價值理念是建構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價值觀基礎,繼而再用這套知識體系解決鄉村問題、培養鄉村人才。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中國鄉村社會存在宗族鄉紳管理的歷史,當前村委會的自治是改革開放后才逐步推開的,歷史較短。農村社會工作在全球化發展脈絡下應融合鄉村的士紳文化。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生成既需吸收西方團體格局中的價值理念,又需認識到鄉土社會的復雜性,在各股力量交織運行的基礎上尋找自身的角色定位。
在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多元化的知識體系不僅推動著實務的開展,而且培養了一批具有全球化視野的社會工作人才。經過專業化訓練的一線農村社會工作者便是“全球化知識”與“本土化知識”融合的統一,與此同時,在實踐中他們動態地生產著農村社會工作知識。云南連心社區照顧服務中心重視本土社會工作人才的培養,認為每一位駐村社會工作者都是在祖國的大地上撒下的一顆顆“火種”,是鄉村振興的希望。在招聘駐村社會工作者時,連心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傾向于選用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因其在院校內受過專業知識的系統化訓練,具有相對開闊的國際化視野。同時,應聘者最好是所駐扎村的村民,懂當地的民族語言與傳統習俗,掌握在地化知識。這種駐地社會工作者的培養模式,是在如今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下,結合中國鄉村實際情況的一種嘗試。在院校接受過系統化理論知識培訓的本土人才,在推動實務工作時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與系統性,結合經驗提煉有效的概念與理論,可望成為農村社會工作本土知識生產的主力軍。
如今科技逐漸打破了各地的斷裂狀態,信息來源趨向多元化,全球化融通農村社會工作本土知識體系成為不爭的事實。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普適性的價值理念成為各地構建特色理論的基礎與起點,為在地化本土知識的生產提供了先導支持。全球化體系培養的農村社會工作人才則是融通西方文明與中國鄉土文化的關鍵,是建構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重要抓手。
四、基于本土化知識建構的農村社會工作未來展望
中國的鄉土社會帶有復雜性與獨特性底色,外來文明的進入必然要面臨本土化議題。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在農村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便呈現出西洋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為當代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積累了實踐經驗。以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為代表的鄉村建設學派,在鄉村踐行著個人理想,探尋救國之道。當代國內的仁人志士也在對鄉村發展進行探索,把西方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與中國的鄉情結合,在云南、廣州、江西等地開創了不同的發展路徑。
可以說,中國的農村社會工作對照西方既有的知識框架,在“照著講”的基礎上完成“接著講”,并通過本土建構的方式進一步提升到在“接著講”基礎上的“自己講”和“對著講”。①安秋玲:《社會工作知識本土建構:基于實踐場域的進路與策略》,《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6 期。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社會工作作為一股外來力量,在鄉村起到活化與聯結的作用,激發了農村社會的活力,并為村民提供了另類可選擇的發展模式。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也完成了基于本土情境的不斷建構。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農村社會工作在我國的發展仍處在起步階段,在未來的發展中應重點關注以下問題:
其一,推動農村社會工作本土化知識建構過程中農民主體性的發揮。通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本土化知識的建構是多方主體互動的結果,但在外力介入的過程中在地居民面臨著喪失“主體性”的風險。在外力主導型的農村社會工作進入鄉村后,“權力性存在”和“制度性安排”貫穿于鄉村建設的全過程,外來者起主導作用。大部分村民被隔絕在這場日漸熱鬧的盛宴之外,各方力量巧妙地實現了對原本屬于村民的鄉土資本的合法占有,并進行轉化與再生產,成為獲利者。②張偉強、桂拉旦:《制度安排與鄉村文化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甘肅社會科學》2016 年第1 期。在此過程中,農村社會工作發揮自身鏈接資源的功能,傾向于將鄉村理解為問題外化、被外部塑造的“他者”存在,形塑了傳統修復性的農村社會工作③吳越菲:《重思以鄉村性為基點的農村社會工作:概念嬗變與實踐轉型》,《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3 期。,從客觀上促成了“他性”文化的注入與轉化。④蔡鑫、朱若晗:《鏈接與賦權:現代性反思視角下鄉村文化資本治理與社會工作實踐》,《晉陽學刊》2021 年第2 期。
外力的介入加重了底層群體話語通道的缺失問題。在農村社會工作尚未進入前,農民掌握的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的耕種技術起關鍵作用,具有豐富經驗的當地人被稱為“能手”,享有很高的聲望。但在外力的逐步干預下,農村開始引進“現代科學耕種”方式。傳統的地方性知識逐漸喪失發揮作用的場域,農民也逐漸喪失了對于本地文化的自信心,盲目崇拜現代文明,產生“自我矮化”心理。但是追求短期內產量提升的現代化耕種方式卻未必是“科學”的,反而容易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嚴重后果。
農村社會工作推動知識本土化的過程應是地方傳統知識與現代文明相融合的過程,而不應是充滿“碾壓”與“拋棄”的斷裂過程。激發在地居民的內生動力,應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徑,充分重視當地的傳統文化與本土知識,以口述史等方式將其傳承,激發居民的認同感與文化自信,并將地方性知識中關于生產的經驗與現代化的生產方式相結合,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其二,推動農村社會工作本土化知識建構過程中社會工作專業性保障的供給。在當前階段,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帶有很大的模糊性①黃曉星、熊慧玲:《過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國社會服務困境——基于Z 市社會工作服務的研究》,《社會》2018 年第4期。,其功能與定位尚不明確。國家系列政策的出臺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工作在中國的跨越式發展,尤其是如今鄉鎮社工站的建設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社會工作專業性的保障始終是各方熱議的話題。當下在政府部門釋放空間有限與專業發展努力突圍雙重張力的作用下,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并沒有擺脫傳統社會服務模式的束縛。②高飛:《后扶貧時代的新貧困治理:社會工作的定位與角色——一個長程的比較視野》,《內蒙古社會科學》2020 年第6 期。
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我們要抓住社會工作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當下能否為社會工作提供專業性的保障無疑是其作為社會力量的代表參與社會治理與國家建設的關鍵。在建構本土知識的過程中,我們要將西方社會工作中“系統理論”“優勢視角”“社區為本的發展模式”等作為元知識與本土知識相結合,避免自身淪為對上唯命是從、對下狐假虎威的異化存在。
同時,社會工作者也應注意專業性的知識構建與社會實際的契合,尤其應具備一定的政治敏銳性。對于專業性的強調是為了提升實踐的有效性,而非彰顯與突出社會工作的專業權威性,產生切實有效的改變才是最終目的。對于一些價值理念的推廣和普及要充分考慮當地的歷史傳統與發展階段,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發展,盡量避免對在地村民生活帶來潛在傷害。在農村開展婦女的“性別意識”喚醒工作、推動“社會行動模式”的社區工作時,應切實考慮如何將社會工作專業的理念與當地實際相結合,其目的不是引起當地的性別對立或村民與權威的非理性對抗,而是以問題解決、社會進步為出發點,進而總結本土化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達到“理論引導—實務落實—知識生成—理論再提升”的良性循環。
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是西方文明與地方性知識的融合。換言之,中國農村社會工作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縮影。在這一過程中,在地居民主體性的“被剝奪”與社會工作發展過程中專業性的“被吸納”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要基于中國的本土情境推動本土特色的農村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構建,有效發揮精英群體的引導作用、充分發揮鄉土情境對在地化知識的建構以及全球化格局對不同知識體系的融通。面對諸多困難與挑戰時,我們不僅要以批判反思的態度審視,還要認識到本土知識的建構并不意味著對某種文明的摒棄,而是一個“包容性”的前進狀態,應對中西方文化兼收并蓄,使農村社會工作成為中國鄉村發展的重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