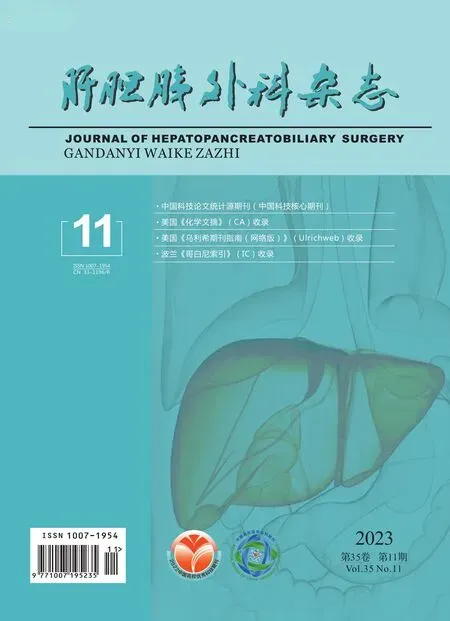循環腫瘤細胞在肝細胞癌中的臨床綜合應用進展
歐偉森,劉高敏,徐繼威
1.廣東醫科大學,廣東 湛江 524023;2.梅州市人民醫院 肝膽外一科,廣東 梅州 514031
2020年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發布的數據顯示,原發性肝癌是我國目前第4 位常見的惡性腫瘤以及第2位的腫瘤致死病因[1],對我國百姓的身心健康造成十分嚴重的威脅。原發性肝癌以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發生率最高,占75%~85%,因其侵襲性和轉移性很強,在疾病的初期就會侵犯到血管,從而導致遠處轉移。HCC目前主要依靠B超和AFP進行初步篩選,但二者缺乏足夠的敏感度和特異度:B超等影像學檢查的特異度>90%,敏感度為65%~80%;當AFP的閾值為400 μg/L時,特異度為99%,敏感度為32%[2]。待到確診HCC時,往往已發展至中晚期。因此迫切需要一種新型的腫瘤標志物來開啟診治HCC的新紀元。
作為液體活檢的代表,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最先由Ashwort在1869年定義,即從惡性腫瘤原發部位脫落,通過血管或淋巴系統進入到血液循環的細胞[3]。CTC能否助力HCC的診治,是當前探討的熱點問題[4]。
1 CTC對HCC早期診斷預測
AFP是當前早期診斷HCC的最常用指標,但缺乏足夠的敏感性和特異性。而CTC在疾病臨床表現前7~9 周即可被檢測到[5],因此其可能先于臨床癌癥診斷[6],這對于早期診斷不明確、AFP陰性或影像學不典型的高危患者有著獨特的優勢[7]。Qi等[8]在2例HBV患者中檢測到了低水平的CTC,并且在隨訪的5 個月內都出現了CT/MRI可檢測到的微小HCC腫瘤。因此CTC的檢測可能是極早期發現HCC的重要技術。目前最新的檢測方法主要有:(1)基于EpCAM和ASGPR的雙靶向功能化石墨烯薄膜,用于特異性識別HCC-CTC[9];(2)基于GPC3免疫磁性材料熒光系統(C6/MMSN-GPC3)的新型CTC捕獲平臺,捕獲效率比傳統EpCAM免疫磁珠提高83.3%~350.0%[10];(3)敏感度約85.7%的全自動集成微流控系統[11];(4)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8.2%和100.0%的CTC計數聯合GNB4/Riplet甲基化檢測[12];(5)利用抗ASGPR抗體和抗EpCAM抗體功能化的微流控協同芯片,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7.8%和100.0%[13];(6)新型Ep-LMS/Vi-LMS-GPC3-LMS CTC檢測系統,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8.1%和96.9%[14];(7)在檢測早期和AFP陰性HCC方面表現良好的ChimeraX-i120平臺[15];(8)ImagesteamX Mark Ⅱ流式細胞儀[16]。綜上所述,隨著檢測技術的不斷成熟,或許在不久的將來,CTC將有可能取代AFP的首選地位,更早期、更靈敏、更高效地用于HCC的早期篩查、診斷。
2 CTC對HCC腫瘤分期的參考
癌癥的分期直接影響到治療的選擇和預后預測。目前國際上主流的HCC分期系統是巴塞羅那臨床肝癌(BCLC)分期系統、TNM分期系統。而CTC則可以提供一種新型的參考指標。Yu等[17]發現,存活陽性CTC計數與TNM分期(P=0.002)和BCLC分期(P<0.001)顯著相關。有學者則發現HCC患者的CTC在BCLC A期和BCLC B/C期的陽性率分別為69.8%和87.5%[18]。更有研究進一步確認間充質CTC≥1 可作為判斷BCLC分期的臨界值[19]。早在2010年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AJCC)就已經在第7版《腫瘤分期指南》中將CTCs列入TNM分期系統;在第八版中,除保留cM0(i+)分期外,更進一步明確了CTC檢測的臨床價值。
3 CTC對HCC患者個體化治療的指導價值
HCC具有明顯的腫瘤異質性,這是影響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為其制訂相應個體化治療的依據之一[7]。CTC是循環中潛伏的癌細胞,能夠在治愈性切除后引起腫瘤復發,因此靶向消除CTC對于根治癌癥顯得十分重要。通過分析PD-L1+CTC與抗PD-1治療反應之間的關聯可知,接受PD-1檢查點抑制劑納武利尤單抗的5 例患者有治療反應[20]。有學者更是開發出了多點共擊納米裝置(GV-Lipo/SF/DT),可以特異性靶向治療細胞并在捕獲CTC后將其殺死,從而消除腫瘤的“根”和“籽”[21]。一項研究納入了47例接受三聯療法[PD-1 抑制劑聯合調強放療(IMRT)和抗血管生成治療]的HCC患者,發現基線時<2個PD-L1 CTC的HCC患者接受三聯療法的客觀緩解率(ORR)和總體生存率(OS)更好;并證實PD-L1 CTCs可以作為接受三聯療法的HCC患者的預測生物標志物[22]。FGL1是LAG-3的主要配體且通過二者結合來抑制腫瘤T細胞的功能,其可作為新發現的潛在免疫治療靶點[23]。這類治療靶點對于個體化治療決策顯得尤為重要,它可以幫助醫師選擇適當的藥物治療,以期改善反應結果。目前的研究已為HCC患者的靶向或免疫治療提供了理論甚至是現實基礎,但仍需要進一步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驗證。至于是否行肝切除術,Qi等[24]提出解剖性肝切除可能僅在低CTC計數和E/M-CTC陰性的患者中比非解剖性肝切除更有益,因此術前CTC分析可以更好地指導HCC患者切除方法的選擇。與單純肝切除術相比,接受PA-TACE治療的M-CTC陽性患者的無復發生存期(RFS)和OS均有顯著改善[25]。
4 CTC對HCC患者療效的評價
HCC的治療效果目前主要參考AFP及影像學檢測;對于采用系統抗腫瘤治療的HCC患者,大多采用RECIST 1.1進行療效評價[26]。Li等[27]的研究出現了HCC患者接受索拉非尼治療后CTC數量明顯減少的跡象,從而認為CTC數量變化是接受索拉非尼治療的HCC患者疾病無進展生存時間(PFS)的獨立預測因子。血清AFP、甲胎蛋白異質體3(AFP-L3)及CTC三者聯合可用于預測微波消融(MWA)后的療效[28]。MWA治療后CTC顯著下降從而證實MWA對HCC患者有殺滅腫瘤細胞的作用;而在接受C-TACE治療的患者中與MWA相比此作用沒有顯著差異[29]。但Wu等[30]卻發現TACE治療1、4周后CTC水平顯著下降。通過對123例HCC患者的血液樣本在肝切除前和肝切除后1個月進行檢測,Sun等[31]首次報道了HCC患者肝切除后不久觀察到CTC負荷顯著降低,這很可能歸因于原發腫瘤的手術切除;他們還認為,EpCAM+CTC可作為監測治療反應的實時參考指標,準確而早期的決策有利于根據個體腫瘤的特征定制出最有效的治療方案。HCC患者通過系統治療后進行CTC檢測,若其數量減少,說明治療方式有效;在整個過程中實時動態監測CTC的數量變化,可協助醫生了解治療效果,及時治療并調整方案。
5 CTC對HCC術前術后轉移的分析
CTC是原發瘤和轉移瘤之間的關鍵中間體,可以反映腫瘤侵襲性和轉移潛力,并且可以成為肝內轉移的預測標志物[11]。上皮-間充質轉化(EMT)在腫瘤侵襲和播散中具有關鍵作用,且EMT先于腫瘤形成[32],而轉錄因子Twist可能在HCC進展的早期階段促進了EMT的發生[33]。截至2018 年第一項繪制CTC擴散途徑并表征局部腫瘤患者CTC的綜合研究中,科研人員發現不同血管部位的CTC在上皮和間充質組成上表現出空間異質性,這將有助于揭示HCC轉移的新機制[34]。Li等[35]推測,門靜脈腫瘤血栓可能是CTCs全身擴散的結果,是微轉移形成的基礎;并且推測CTCs中的Twist和Vimentin表達可能是評估轉移的臨床早期預測因子。有研究甚至表明CTC計數與血管浸潤程度呈正相關,其預測HCC轉移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2.93%和52.38%[36]。而根治性手術后CTC計數≥3、負荷持續升高可能反映著肝外微轉移的存在[37]。HCC早期即可發生肝內外轉移,并且切除術后5年腫瘤復發轉移率高達40%~70%,這可能與手術前存在的微小播散灶或多中心發生有關[26]。通過CTC對HCC患者的分析,我們可評估患者術前有無發生腫瘤轉移,從而為其提供最優化的治療手段。另一方面,相較于AFP,CTC在患者術后的復發轉移方面更具有顯著的預測價值。如果將這兩者進行聯合監測,將有利于提高HCC患者肝切除術后復發轉移的預測效果[38]。
6 CTC對HCC患者預后的預測與評價
預后評估是患者經系統治療后的關鍵步驟之一,其重點在于尋找預測指標,CTC是HCC患者預后指標的佼佼者。Meta分析則充分證明了HCC患者中CTC陽性者的OS要低于陰性者[39]。Liu等[40]在2013 年開發出基于高核質比的新型CTC檢測方法,可用于高敏感性HCC患者的預后預測,特別是在短時間內評估患者是否會復發。通過隨訪數據分析,有學者認為其臨界值在CTC計數≥3[37]、≥5[38],此外還有各種CTC亞型,例如glypican-3陽性CTC[41]、Nanog CTCs[42]、CTC-WBC集群[43]等。并且,Twist+CTC[33]、M-CTC[44]或聯合Ki-67[45]的預后評估要優于單獨的CTC。CTC狀態及超聲組學評分[46]和術前CTC-NLR[47]則分別被視為HCC患者根治后早期復發(ER)和OS的預測因素。在肝移植方面,截至2021年誕生了第一項全面評估肝移植術后HCC患者圍手術期CTC檢測臨床意義的研究,結果表明CTC計數是預測HCC患者肝移植后復發的一個有用的生物標志物,移植后連續監測CTC計數可能提供比單獨使用傳統監測方法更早的治療干預機會[48]。同樣,有研究發現術前EpCAM+CTC檢測以及術前和術后第1天EpCAM+/CD90+CTC檢測可預測活體肝移植(LD-LT)后HCC患者的復發,并可指導其術后監測和免疫抑制[49]。
7 小結與展望
傳統的腫瘤確診“金標準”仍舊是依靠細胞組織病理活檢,但該方法存在著很多問題,如創傷性大、取材困難等缺點。相對而言,CTC具有無創、實時、方便、快捷、能夠持續監測疾病的進程,以及對療效檢測、患者預后和復發情況進行判斷和評估等優點,因此在未來對癌癥的診療中或許大有作為。但由于現階段檢測技術有待提升,暫時也沒有統一的檢測標準,我們還需要多中心、大樣本、足夠時長的隨訪,不斷積累足夠的循證醫學證據來支撐CTC在HCC臨床診療中的實際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