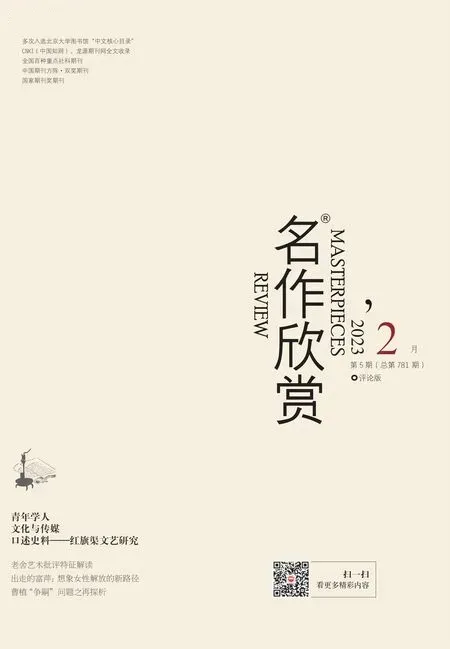“獸性”“神性”“人性”探析
——以《邊城》和《額爾古納河右岸》為例
⊙孟晗 夏雨 [伊犁師范大學,新疆 伊寧 835000]
“獸性”“神性”和“人性”,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形態的三個側面,當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激烈表達時,就沾上了“獸性”的色彩,而當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不懼于表達或對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淡然處之時,生命便有了“神性”的光輝。《邊城》以湘西茶峒為背景,描寫了一幅平和靜美又不失哀傷的人生圖景;《額爾古納河右岸》以鄂溫克族最后一位酋長夫人對于本民族百年來興衰歷程的自述揭開了籠罩在森林山川上的神秘面紗,兩者都在民俗風情上打開缺口,刻畫自然人生的喜怒哀樂和歲月變遷中深刻的生與死,并在此過程中展開對于“獸性”“神性”“人性”相交織的和諧健康的生命形態的憧憬和對現代文明的反思。
一、“獸性”的展露
從進化論角度來說,人和動物本就是同源,“獸性”即“動物性”,代表著一種不馴服的野性,一種雄強奔放的生命力,這種所謂的民族性中的“獸性”與正統文化理念不同,儒家的“仁愛禮義”、老子的道法自然、莊子的知觀達命……正統文化的價值毋庸置疑,但更多的還是朝向后來所說的“精英知識分子”立場。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獸性”逐漸被壓抑于“人性”之下,它根植于人性,卻又指向人性深處最真切的欲望,喪失了“獸性”的軀體是被抽干了汁液的枯木,人不能拋棄“獸性”,一個民族更不該如此。《邊城》和《額爾古納河右岸》正是在對兩處人民身上所流露出的“獸性”書寫上,展開對于現代文明的思考以及對于民族性的反思。
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一些人物明顯帶著一種原始的力之美,這種“原始的力”便來源于人的“獸性”,它與魯迅所批判的奴性對峙,奴性是阻滯,“獸性”是突破。
《邊城》的故事是在舒緩的曲調下呈現的,但在舒緩之下,我們依然可以窺見“獸性”的暢美。茶峒的人們真純、古樸且善良,但在人事困頓上也絕不逃避。順順對于天保、儺送兩兄弟的訓練,是甘苦與人相共,“且佩了短刀,遇不得已必須動手,便霍的把刀抽出,站到空闊處去,等候對面的一個,繼著就同這個人用肉搏來解決”①。決斗與廝殺是與文明相對立的現象,但在《邊城》中,這是合乎規矩的行為。沈從文在對《邊城》人事的刻畫上有意消解現代文明,在質樸善良的人身上增添原始的獸性之美,以此將自然人性和原始獸性置于一種和諧圓融的境地。在對翠翠的外貌刻畫上,也體現了沈從文對于原始獸性之美的憧憬。“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②沈從文直接將小獸的特征置于翠翠身上,翠翠是有著人的乖巧善良和獸的機靈活潑的結合體,作者再一次在人物身上凸顯了對于獸性之美的追求。除此之外,《邊城》中人與人的交往也是帶著“獸性”的,老船夫每次打酒后,遇見一個熟人便寒暄幾句,給那人嘗一口自己的酒,還沒到家,酒壺便有可能見了底,在翠翠的擔憂中,祖父也是可能喝醉了便在哪條路上倒頭就睡的,這些行為無不帶著原始的野性。茶峒人與人的交往,很多是突破了現代文明的規約與限制的,他們既有著人性中的質樸與善良,也有著獸性中的灑脫和不羈,沈從文在這些圓融健康的軀體上寄托了自己對于生命形態的思考。
此外,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有一個特性,當其他作家以鄉村為視點,用被摧殘的人性指向現代社會發展的批判時,沈從文反倒將受到苦難的人們以一種自得的,甚至美的狀態展現出來,更顯出一種蓬勃的、不馴服的獸性之美。
相較于《邊城》的含蓄,《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對于獸性的展露則更為外放,那群生活在右岸的人們就像森林中的獸物般煥發著生機。
在與仇敵的共同覆滅上,老達西將一種奔騰的“獸性”發揮到了極致。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曾徒手與狼搏斗而失去了一條腿,又為了復仇生生馴服了一只獵鷹,終于在一個夜晚同仇敵共同覆滅于廣袤的草原之上。在遲子建的筆下,老達西與他的獵鷹是共生的,人與獸共生,獸被賦予了人情,人亦被賦予了獸性,正是在這樣一種交融的狀態下,譜寫了一曲生命的頌歌。
在對于壓迫的反抗上,伊萬亦表現出了不馴服的獸性,他用他那一雙有力的大手攥壞鐵壺嚇退了販賣婦女的俄國商人,并抱得美人歸后,又對日本人的欺凌奮起反抗,用出逃繼而參加反抗戰爭的方式沖破了壓迫的阻滯。除此之外,遲子建對于女性角色獸性之美的展露也毫不吝嗇,相較于其他作品的性別意識,《額爾古納河右岸》將男女書寫置于一個平等的地位,他們皆如同野獸一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不同于男性角色的廝殺、搏斗,女性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同自然、人事、命運進行著孜孜不倦的斗爭。
依芙琳是個多面性的人物,她既有著人性最丑惡的一面,也具備獸性中不羈的一面。她從未屈服于一個不愛她的男人的求歡,即便是在失去獨子又懷孕之時,“伊芙琳駕著滑雪板,在山嶺雪谷間穿梭了一天,終結了坤得日思夜盼的那個小生命”③。在快意的報復面前,她完全喪失了人類的理智,以一種帶著野獸氣質的畸形的反抗主導自己的生命。對于常理而言,這種行為是不理智甚至是病態的,但正是這種不理智才超越了平淡。神奇的生、悲壯的死,獸性的出現是帶著毀滅的火種的,但唯有獸性才能激起大多數人如死水般的軀體,療愈千百年來因病態的壓抑所造成的屈從。
兩部作品對于獸性的呈現有所差異,但都肯定了人作為生物之一對于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與和諧完滿的生命形態的追求,沈從文用強悍、不羈的獸性擊垮虛弱、萎靡的性格,渴望從真純質樸的湘西世界挖掘出民族性中所缺失的部分,用自然的生命形態醫治都市中畸形的生命,使民族煥發新的生機。而遲子建從對鄂溫克族人原始生活的描繪到對人們集體搬遷的書寫,既有對原始奔放的民族生命力的追求,也有對人類文明發展、古老文明沒落的隱憂,兩部作品都隱含了作者對于人類文明與民族命運的焦慮及擔憂 。
二、“神性”的彰顯
神是純潔、神圣的象征,神性擺脫了原始的蒙昧狀態,帶著原始的蠻性中的自然純凈,又除去了其中野蠻粗糙的成分,它包含了人性至純至真的善與美,又去除了人性中矯作、偽飾的因子,它是一種與自然相融合的人性,神性與人性相通,但神性是最高的人性。
《邊城》中沈從文將神性之美體現在欲望的大膽表達上,在他的筆下,水手與娼妓們的交易是無關乎廉恥的,它是一種人性的本真表達,人可以不加修飾地展露自己的欲望,這是難能可貴的,欲望本身并不污穢,大膽的欲望表達反而是神圣的。沈從文對于神性之美的表達主要著眼于那個未經現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世界,在這片地域上,“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④。他還寫男女之愛中的人們對于一種發自內在的蓬勃生命力的欣悅,用詩性的筆墨描繪或暗示著男女之事,甚至有些言辭裸露,但絕不污穢,因為在沈從文的價值判斷中,性超越了道德的范疇,它是人性最真純的欲望表達,它與那些都市文化圖景中畸形了的人性不同,它寄托了沈從文的文化理想。
除此之外,神性還是自然圓滿的生命形態,是極致的愛和美。《邊城》中雖沒有對翠翠父母的愛情作過多筆墨,但寥寥數語便可以窺見,那軍士既沒有逃避責任,亦沒有拋棄愛情,首先服了毒,而那女孩待腹中小孩生下后,也到溪邊吃了許多冷水死去了。翠翠和天保、儺送三人的感情糾葛,“兄弟兩人在這方面是不至于動刀的,但也不作興有情人奉讓如大都市懦怯男子愛與仇對面時作出的可笑行為”⑤。儺送為了追尋愛情在碧溪岨對溪高崖上唱了一夜的情歌,翠翠在睡夢中摘了一把虎耳草。這一切不僅讓人嗅到蠻荒的氣息,更感受到愛情的莊嚴與神圣,一切皆遵循著自然的旨意,擁有著這般純潔到極致的美和愛的人,是具有神性之美的人。
《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神性則體現在人與自然的融合上,這是一種天然的靈性。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們,他們仿佛天然地靠近神明,他們將萬物置于一個平等的地位,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它們生于自然,亦死于自然,周遭的一切皆與自然相合。
在男女情事上,遲子建用“風聲”來形容人的欲望,冬日的風中有野獸的叫聲,夏日的風中有貓頭鷹的叫聲,希楞柱里也有風聲,“這種特別的風聲是母親達瑪拉和父親林克制造的”⑥。每一個新的生命都是在這樣的風聲中誕生的,直到多年后自己也制造出這樣的風聲,并在這樣的風聲中感受到了人世間最赤忱而熱烈的愛。
在那片廣闊的新堿廠上,“我的身下是溫熱的堿土,上面是我愛的男人,而我愛的男人上面,就是藍天”⑦。情欲與自然萬物交織,人與自然是一體共生的,它與現代文明中的情感不同,剝離了其中飽受壓抑的成分,與《邊城》相比,這里蠻荒的氣息更重,如果說《邊城》中的神性是一片平和的基調,那么《額爾古納河右岸》的神性則多了一份躁動的因子,但它們同樣都是一種圣潔化了的情欲,在純潔中溶有“神”,在自然中溶有“愛”,在天性中溶有“美”,無一不是神性的彰顯。
除此之外,《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悲壯的“死亡圖景”也帶有神性的色彩。不論人與獸,他們既在自然中出生,又在自然中寂滅,一切都順應著自然,一切又都有著神圣而莊嚴的色彩。他們食用獵物時,會為它們舉行風葬,孩子死去時會用一塊潔白的布裹起扔到向陽的山坡上。在右岸,生與死是貫通的,老達西死后瑪利亞奇跡般地孕育了小達西、“我”與拉吉達狩獵時放過了剛產下四只小水狗不久的大水狗,三年未孕的“我”便迎來了新的生命……生與死都與自然相契合,即便是擁有神力的妮浩,在面對挽救一個生命便失去一個親生骨肉的前提下,也坦然地遵循自然的旨意,順從天地自然間的平衡,在這群與自然共生的“精靈們”眼中,死亡不過是回到了天上,或與云作伴,或是化作馴鹿和鳥兒,生命只是展開了另一種形式的復歸,死帶著生的延續意味。鄂溫克族對待生存與死亡自有一套近乎哲學的認知,他們的生命是蓬勃有力的,他們所面對的死亡是人與自然的融合,整部作品中各式各樣慘烈的“死亡圖景”被豁達的溫情消解,留下動人心魄的悲壯和凄美,整部作品都有著耐人尋味的神性的色彩。
三、“人性”的呈現
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想在沙基或水面上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⑧
人性永遠是沈從文作品中的中心話題,在對人性的呈現上,他也通過一群社會地位較高的知識分子揭示本我被長期壓抑之下所造成的病態都市人格,比如《八駿圖》。但在《邊城》中,沈從文更多的是呈現人性的至純至凈至善至美,以期用純粹、靈動的生命力,對抗糜爛的都市文化,因此,整部作品便是由一個個純凈的靈魂所構成。魯迅的作品多在舊的一代身上展開批判,在新的一代身上寄托希望,而在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中,這極致的人性之美是有延續性的。沈從文更多的是對兩種文明相碰撞的過程中,一種文明的退化、另一種文明滋長的逐漸扭曲的反思,因此,在對人性的呈現上,他盡心地建造著他筆下純凈的湘西世界。
《邊城》中的人性之美首先體現在血濃于水的親情之上,老船夫與翠翠相依為命,翠翠與祖父都深切地為彼此牽掛擔憂著,翠翠觀看游船時會牽掛祖父,而祖父也時常為了翠翠能看到游船費盡心思。除了深厚的親情之外,一種人情之美在祖父與翠翠之間進行著延續,渡船便是延續的紐帶,這是一種精神的傳承,這位總是忠實地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自己一份力的祖父逝去了,而他質樸的精神內核永遠不滅,這份人情之美通過渡船延續到了下一代人翠翠身上,這是一種精神的傳承,亦是一種文化的延續。還有大方灑脫的順順,教育天保與儺送的方式正是讓他們甘苦與人相共,“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兩個孩子學得做人的勇氣與義氣……故父子三人在茶峒邊境上為人所提及時,人人對這個名姓無不加以一種尊敬。”⑨沈從文正是在兩代人身上傳達著對于美好的湘西文明傳承的訴求。
《邊城》的人性之美還體現在忠貞純潔的愛情之上,從逝去的翠翠的父母到如今翠翠與天保、儺送三人的情感糾葛,“愛”是《邊城》的底色,沈從文甚至對這些人的情感未著一“愛”字,卻將一片真摯深沉的情感盡現于筆端:年輕的姑娘義無反顧地為愛人殉情,兩兄弟各自為了對方的幸福忍受心酸,就連吊腳樓上的娼妓動了情時也心心念念地牽掛著岸上的那一個,每一份愛意皆動人心扉。
除此之外,鄉鄰之間的情誼也構成了《邊城》中人性美中較為突出的部分,《邊城》中并非沒有階級之分,但湘西世界中的不同階級是和諧共生的,船總順順慷慨而又能濟人之急,在天保死后,順順雖在內心對老船夫有所怨言,但老船夫去世之后,仍寬容地對翠翠施以援手。沈從文在人性可能會被扭曲的地方反而展現出了人性的本真和善良,這與那種為苦難所壓迫或是遭受了非人的摧殘后開始壓抑自身、甚至偽飾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是完全不同的,這也是沈從文作品最動人之處。還有楊馬兵,年輕時追求翠翠的母親未果,老船夫死后卻自覺承擔起照顧翠翠的義務。《邊城》中的人性之美既是線性延續的,又如一張巨大的精神之網將每一個人編織其中,形成了與欲望糾葛的都市文明相對峙的理想之地。
在都市圖景之下的社會文明中,親情、愛情、鄉情時常陷入與欲望糾葛的旋渦中,人的自然天性被壓迫,并與當下的文化道德產生矛盾。沈從文正是將筆墨著眼于湘西世界中健全完滿的人性,同時將這種健全完滿的人性與都市中人性的“死”和“萎縮”相對照,以期用諧和的人性療治都市文明的痼疾,尋找民族道德精神的源頭。
同樣是呈現人性,《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人性美帶著灑脫和超然,還有作者對于人性中的自然缺陷以及兩種文明碰撞所造成的人性悲劇發出的溫情批判。
妮浩明知救活一個人就會失去一個孩子,但當她面對被熊骨卡住的馬糞包、徘徊在生死邊緣的小男孩,她依然救活了他們,最后為了森林火災祈雨,在跳完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支舞蹈、神歌還未唱完時,便在滾滾濃煙與電閃雷鳴中倒向大地,這位“自然之子”將神力同軀體一起歸還給了自然,將愛和奉獻留在了人間。金得的一生都屈從于母親的意志,接受了難以接受的婚姻,最終在一棵枯樹上吊死。“金得很善良,他雖然想吊死,但他不想害了一棵生機勃勃的樹,所以才選擇了一棵枯樹。⑩是有多么純粹的人性,才能在面臨自己生命的終結時,依然顧及一棵樹木的生機。還有善良的達西拯救了新婚之后隨即陷入寡婦境地的杰芙琳娜、為了保護放映員和馬糞包而被黑熊吞噬的瓦羅加、為解坤得的困境被迫落荒出逃的伊萬……他們以平凡的軀體呈現出對每一個生命的終極關懷,大愛與無私是他們人性的底色,于荒野中寂滅,于自然中永生,他們的人性美是帶著灑脫與超然的,早已走出狹小的人類范疇,走向了廣闊的天地宇宙。
依芙琳是整部作品中相對復雜的人物,遲子建不吝于贊頌純粹的人性美,但也毫不規避人性的弱點。依芙琳是一個在不幸福的婚姻中飽受身心雙重壓抑乃至病態的女性,面對別人的幸福,她常常發出惡意的嘲諷甚至惡毒的詛咒,在兒子金得離世后,她將妮浩和瑪利亞的痛苦當作療愈心靈的良藥。但面對日本人的刁難,她卻堅定地說:“人就一個腦袋,別人不砍的話,它自己最后也得像熟透的果子爛在地上,早掉晚掉有什么?”?殘酷的生活封鎖了她內心深處本該有的善意,但鄂溫克人民頑強的精神品質依然在民族危機時閃現,遲子建借這個復雜的人物表達了對于民族品格的贊頌和思索以及對一個民族從興盛到衰退過程中所遭受的沖擊。依芙琳最終在給瑪克辛姆脖子上的爛瘡吹氣的過程中死去,在幫助他人中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完成了從惡向善的回歸,也拯救了因苦難所扭曲的人性。
與《邊城》不同的是,《額爾古納河右岸》還直白地展露了現代消費主義對于原始文明的沖擊以及兩種文明碰撞中人的精神困頓,“科學主義把人變成技術奴隸……消費主義把人變成消費動物,而自由卻像浮士德的靈魂一樣被出讓了”?。遲子建正是在深陷原始文明與現代文明旋渦中的新一代身上展現了精神的掙扎和人性的異化。伊蓮娜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城市,在城市的車水馬龍與森林的山巒溪流間往復,終于在看見了妮浩祈雨時感受到了一個民族百年的歷史激蕩,于是在用畫筆記錄下這一切之后在她熱愛的森林間終結了自己矛盾的一生,實現了靈魂的回歸。帕日格和沙合力則染上了酗酒鬧事的惡習,索瑪為了自己的欲望對馴鹿發出惡毒的詛咒……原始文明在消費主義的侵蝕下退化。遲子建對此種種展開了智性的反思,反思中更有溫情的批判。
四、結語
《邊城》和《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故事背景不同,人物命運亦不同,但他們都在對生與死的思索中譜寫了一曲又一曲生命的贊歌,在對“獸性”“神性”與“人性”的書寫中刻畫了和諧完滿的生命形態。健康圓融應是“獸性”“神性”與“人性”的統一,民族品格的塑造更需要三者的結合,丟失了“獸性”的民族會走向奴性的旋渦,丟失了“神性”的民族會對萬物失去敬畏之心,丟失了“人性”的民族則會陷入道德的墮落。在人類社會飛速發展的當下,現代文明催化了心靈的焦慮甚至精神的扭曲,在這種處境之下,人類文明的發展、民族品格的塑造、民族未來的走向是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應當承擔的重任。沈從文用《邊城》構筑與都市文明相對峙的湘西世界,遲子建用《額爾古納河右岸》在現代文明建造理想之城,兩位作家對人類文明的進程展開智性的思索,思索中也透露出對于民族品格塑造的疑惑、對于民族未來走向的擔憂以及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焦慮。
①②④⑤⑨ 沈從文:《邊城》,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頁,第27頁,第34頁,第84頁,第35頁。
③⑥⑦⑩? 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頁,第9頁,第104頁,第124頁,第105頁。
⑧ 沈從文:《沈從文選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頁。
? 楊春時:《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上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