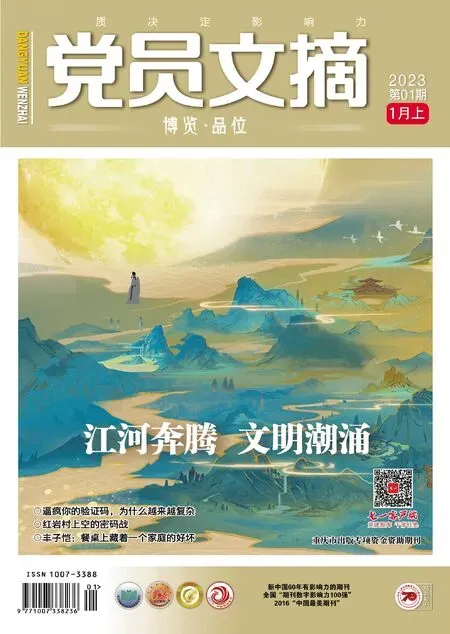我們的“空心病”,需要給心靈“補氧”
□焦晶嫻
跳槽到互聯網大廠后,李洋的微信未讀消息時常保持著99+,微信狀態總在“疲憊”“忙”“睡覺”“勿擾”中切換。24歲的李洋畢業2年,換了3份工作,她總覺得累,“感覺自己被全社會拋棄”。
一項健康報告顯示,2021年每個人平均存在4.8個健康困擾,其中情緒問題排在首位,18歲至34歲青年的焦慮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齡段。
崔慶龍是一名在微博上獲得了大量關注的心理咨詢師,他在一條微博里描述了對“精神亞健康”的觀察:“始終籠罩著一層驅散不了的惶惶不安,始終負荷著一些擺脫不了的沉重……雖然每天都能正常入眠,卻不能真正休息,好像總有一些倦怠常駐后臺。雖然每天都有閑暇,卻體驗不到安逸,精神上隨時在為什么待命。”
“我覺得情緒是個錯誤”
跳槽后,李洋用心學習“大廠生存法則”,發現隨時隨地復盤是同事們的必備技能。于是,即使在擁擠的地鐵上,她也不忘咀嚼工作中的失誤,質問自己“為什么不這樣做?”這種挫敗感會持續到第二天。
為了轉移注意力,李洋開始無休止地刷短視頻,刷完就生悶氣,“凈做些完全沒有營養的事”。當自我調節手段無法去除內心的惶惶不安,她開始懷疑:“有情緒,是不是我自己的問題?”為了找到答案,她體驗過冥想、催眠、心理咨詢,但仍然無法擺脫“虛無感”。
李洋經常找前同事王藝聊天,在她看來,王藝冷靜、堅強,但只有王藝自己知道,“哭不出來”已經快成為一種困擾。
“我覺得情緒是個錯誤”。王藝從小就習慣壓抑自己的情緒。父母工作忙碌,“無論我散發什么情緒,都無法引起他們的注意”。于是,她開始把精力放在學習上,優異的成績會讓父母多夸她兩句。工作后,王藝依然要求自己必須優異,但漸漸地,她發現自己常陷入一種“飄忽”的狀態。
2021年7月,王藝所在的公司裁掉了近一半員工,她雖然被留下了,但她上班時總無法集中精力,像一只受驚的兔子,時刻捕捉同事談話的碎片。
當時王藝以為這種“飄忽”的狀態會“被時間治愈”,但情緒在暗中慢慢累積,當熟悉的領導辭職、自己不得不融入新團隊時,她開始脫發、厭食。
為了“自救”,王藝買了不少心理學的書籍,在網上報了一個“情緒覺察”的課程。她發現自己在情緒發生后,會壓下內心的不適感,告訴自己不要太矯情。最終她發現,幾小時甚至幾天后,這種憤怒、悲傷、委屈仍未離開身體。
崔慶龍這樣解釋這種“損耗”的狀態:“生活中,人們在處理很多問題的時候,總是習慣于否認和忽視,總是假裝一件事已經過去了,并且用合理化的方式給那件事在意識層面做了一個完結的說明,但它其實還在運行。這種長期積聚會讓一個人越來越有壓力,越來越焦慮,也可能越來越虛弱。”
“嘿,你今天是怎么了”
在豆瓣App“自我覺察的瞬間”這一話題下,一位民警分享了一段經歷。有一次,一個年輕姑娘因為票務問題情緒失控,對工作人員全程黑著臉。這位民警隨意問了一句:“嘿,你今天是怎么了?”對方雖然沒說什么,但放下了戒備,后來還給工作人員道歉,吐露了近段時間有很多煩心事。
崔慶龍說:“一般大家只會表達‘我很喪’‘我很煩’這樣過度概括化的表層情緒,這種情緒會在心理上擰成結,變得難以被表達,也難以被理解。很多人也不習慣跟身邊的人分享更深度的體驗。”這時候就需要“自我覺察”來深入梳理情緒,對情緒的合理分辨是走出情緒的關鍵。
“我們確實需要接受一些吻合現實程度的痛苦,比如說損失了一些財物,或者好朋友的離開,這個痛苦需要我們去體驗和接受。但很多額外的情緒是來自于對自己潛在的評價,比如因為現實的損失,就覺得自己無能、沒有本事,對整個人生開始懷疑,這就背負了過多的情緒。”崔慶龍說。
和李洋一樣,很多人開始培養這種自我認知的能力。一項調查顯示,除了心理咨詢這樣針對心理問題、價格偏高的心理服務,年輕人越來越鐘愛“輕量”的心理內容產品。
“相比于父母一代,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精神脫貧’,不用再為基本的生存需要去忍耐工作的不如意,面前的選擇也更多。他們渴望實現更高的自我價值,但又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一位心理咨詢師這樣總結近十年的觀察。
“就像被提前劇透了,他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未來的目的地都被確定了,這種確定的東西不是自己想要的,但又無法改變這種局面。”崔慶龍說。
讓心靈暢快呼吸
在情緒覺察課程上,助教會發給王藝一個詞語。她聽到詞語后,就把腦海里的畫面寫出來,具體到物體顏色和人物動作,一步步具象化,同時描述感受。“這個過程里,我會發現自己潛意識里的情緒。”王藝說。
崔慶龍認為,每個人的精神負載能力有限,寫情緒日記能夠幫助我們找到承受范圍,“不是記錄流水賬,而是記錄內心世界的過程,盡可能準確地描述它,然后試著表達對自己這份情緒的理解”。
對于王藝來說,看心理學書籍、學習課程,都是在完善對“我”的認知,是一項很長期的工作。“我知道我已經有意識地發現熱愛的事了,那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
王藝回憶真正感到“安全”的時刻,是有一次一個人漫無目的地走進書店,隨手翻開一本書,從白天看到黑夜。合上最后一頁,走出門,夏夜的風吹在臉上,她看到路邊有小孩拉著母親的手,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臉上洋溢著笑。王藝忍不住也笑出了聲。
李洋試著改變復盤的目標,不再刻意關注“成長”“進步”,而是“讓自己和家人更快樂”。她會在周末關掉所有電子設備,點上香薰,讀書、畫畫、發呆,認真聽窗外的鳥叫,感受陽光灑進房間。
崔慶龍經常也會問自己,怎樣讓生活不單調?“其實生活中隱藏的可選項有很多。比如一個人每天上下班兩點一線,但后來有一天,他找到了一個書吧,或者參加了一個讀書會,參加了一次徒步旅行,去了一個自己從來沒去過的城市……人們需要體驗到本質上的自由性,意識到是什么在束縛著我,是什么讓我的生活變得單調,以及在現有的經濟能力下,我能為自己搭建起怎樣的一個生活?”他建議,可以從在生活里增加小的愉悅感和滿足感做起,“經常發生有趣的事,大多數心理問題會得到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