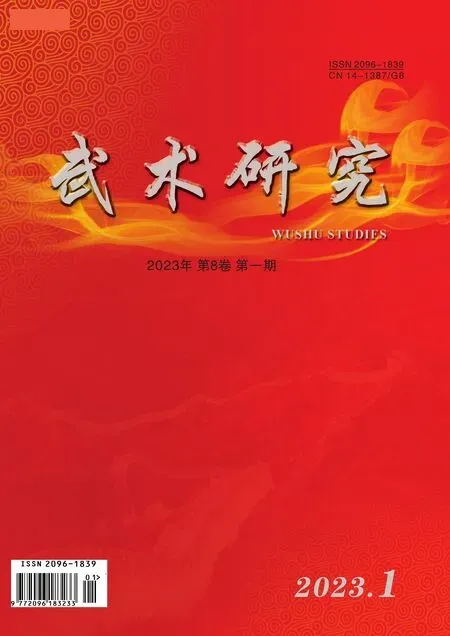貴州省錦屏縣新化舞獅的傳承與發展路徑研究
吳永歡 李 增 杜顯浪 熊姍姍
貴州師范大學體育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2021年8月12日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的認知與利用,并將其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資源。[1]舞獅是一項古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運動,是一項集合武術、舞蹈、音樂等多種藝術為一體的民間傳統體育項目。[2]據2006-2014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統計有1372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把舞龍舞獅分別分類收錄為民間舞蹈、傳統舞蹈、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3]通過查閱資料了解到錦屏縣新化鄉是貴州省著名的舞龍、舞獅之鄉。并且成為了當地的品牌特色,從當前的發展狀況來看,新化舞獅總體來說存在發展不足。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下,政府應加強對新化舞獅的宏觀管理,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推進工作,完竣非遺傳承體系系統,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正面臨機遇與挑戰,外來強勢文化沖擊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新化舞獅的生存發展亦如此。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讓新化舞獅的傳播與保護趨于淡化,技藝不能與時俱進而逐漸小眾化,導致現在傳承隊伍不穩定,人員青黃不接,資金不足,缺乏創新傳承,適應現代社會發展是新化舞獅面臨的主要問題,其傳承與發展在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道路上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1 相關的界定概念
1.1 舞獅
“龍獅運動凝聚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傳統體育項目,是華夏文明的傳承與發展,是中國特有的文化衍生出的民俗傳統體育文化,對于傳承和發展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具有重大意義”。[4]舞獅是中國流傳已久的民間藝術,舞獅有南獅北獅兩種,南獅也被稱為是醒獅。舞獅是獅文化傳承的一種形式,它是獅子的形態與舞蹈相結合的產物。人們認為舞獅是驅邪避災的吉祥瑞物,每逢重要節日都有舞獅表演助興。“舞獅運動是集武術、音樂、舞蹈、表演、競技于綜合一體的多元社會文化現象,舞獅是一項綜合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項目,更是一項民族風俗”。[5]
1.2 新化舞獅
新化舞獅起源于明清之際,發展高潮是在民國,且新化舞獅系北派舞獅系列,以表演威武雄壯的“武獅”為主,[6]是新化傳承久遠的民間文化活動,至今已傳承六百余年。2007年新化鄉被貴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了“舞獅文化藝術之鄉”的著稱,同年也被列為貴州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因其形象逼真,動作矯健活潑,擅于表演高難度動作。能強身健體又能娛情怡志而深受當地人民群眾喜愛,傳承至今,經久不衰。因其濃厚的漢文化色彩和獨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原屬于移植的民間文化,經過歷史的不斷演變,已經與當地人民的勞動生活和民俗民風融匯在一起,形成獨樹一幟的錦屏特色體育文化。
2 新化舞獅的概況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錦屏縣的新化舞獅是當地獨具特色的民俗傳統體育文化活動,政府對民傳體育的扶持力度在改革開放后逐漸增大,并且建立專門體育工作機構培養民族傳統體育人才來促進新化舞獅運動的展開。新化舞獅逐漸成為當地政府的品牌特色,舞龍舞獅活動一般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以一定的流程展現的,它不僅是一項傳統體育活動,更是一種有儀式感,可傳承文化的活動。通過實地調查和與傳承人交談得知,新化在早年活動的舞獅道具靠自己用麻袋和布料做成獅子的毛發,在長布條里塞谷子或是鋸木灰做成獅子的脊背,是新化傳承了數百年的民俗文化活動,因其形象性逼真、動作矯健活潑。獅頭圓又大且不失靈活,前額突起和黑亮有神的眼睛,凸起的鼻子,操縱自由的大嘴,威武靈動的雙耳是新化舞獅的典型造型。頭頂上的彩球是由彩綢扎成的憨態可掬的模樣,具有驚、險、奇、絕、美的藝術特征。2007年新化鄉被授予了“舞獅文化藝術之鄉”的稱號,同年也被貴州省列為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1 傳承形式
2.1.1 學校傳承
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是學校的教育任務之一。新化舞獅的隊伍不穩定,人員青黃不接這些現實問題讓其發展陷入困境,改善傳承方式是時代所需。2008年開始,新化舞獅主要傳承人劉毅將舞獅引進新化中小學,開設了以“新化舞獅非遺文化進校園”的特色課程、校園大課間的舞獅操、開展少年宮活動,通過非遺傳承人劉毅和邀請民間舞獅藝人每周二和周四來學校進行授課、學習、訓練舞獅技藝,讓學生在快樂中體驗傳統非遺文化精神、對舞獅文化有更直觀、深入地了解。因多數青壯年常年在外打工,學生處于學習階段,學習、模仿理解能力強,引入校園傳給中小學生比傳授給青年效果會好一些。新化小學還組建了兩支教師和學生舞獅隊,至今培養了數百名掌握新化舞獅技藝的學生。每年從學生中挑選合適的繼承人,以四十到五十人編為一個舞獅班,進行培訓,主要是從身高、體能、敏捷性幾個方面挑選,在訓練的過程中把教育元素加入到舞獅運動中,使學生在運動中感受到中華民族舞獅運動的內在精神,在練習過程中激發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增強文化自信、傳承民族文化的同時豐富學生的第二課堂。
2.1.2 自組的鄉村“文藝隊”
新化鄉成立了鄉村文藝隊主要用于于各種演出形式,有舞獅、舞龍、大戲表演。雖然“文藝隊”有一定的規模發展,相比于其他專業的藝術團隊,該團隊的業余屬性限制了其進一步的專業化發展。據調查,以前在大年三十的時候才有舞獅游街拜年,在春節拜屋活動中,有數支兩到三人的小獅隊在大年初一時到新化鄉居民屋前舞獅拜年送吉祥。后來政府重視舞獅文化,為豐富當地農村群眾文化生活,就在村委會有了特定地點,文藝隊一般在農閑或晚上排練,這極大豐富了鄉村文化生活,但近年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后就沒有過大型舞獅表演活動。
2.1.3 個體傳承
個體傳承也是師徒或者家族傳承,大多是進行拜師學藝,師父口傳身授式的帶徒弟。新化舞獅傳承人閔文澤說早些年會有人特地上門學藝,但隨著新文化的沖擊和新時代的發展,愿意學習新化舞獅的人越來越少。當下新化舞獅的傳承模式主要是非遺傳承人劉毅在學校教授學生的師徒形式,但這種師徒傳承是流動的,因為被選中的學習人員在完成初中學業過后繼續升學或步入社會,不再繼續學習舞獅。
2.2 “非遺”傳承人的概況
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的傳遞者和載體者,在非遺傳承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7]非遺傳承人有兩個內涵:一種方式是師徒或家族傳承,具有的技能可以延續和發展某項非遺項目,一種是需要通過專家評審后,成為法定的非遺傳承人。
“活態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大的保障,新化舞獅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傳承人通過特定活動和訓練來掌握非遺的知識和精湛技藝。[8]傳承人:劉毅,苗族,1971年生,錦屏縣新化鄉新化所村人,新化舞獅文化主要傳承人。受當地文化的影響從小對舞獅有著深厚的興趣,16歲便開始參與并組織新化舞獅表演活動,不斷改進創新舞獅動作,如搶寶、互推、理毛、吐對聯、獅子直立打滾等,使新化舞獅更具觀賞性。2008年以來,在新化所小學初中作為舞獅文化進校園課程的老師,培養了許多批舞獅青少年學生。2015年被命名為新化舞獅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傳承人2:閔文澤,1963年生,錦屏縣新化鄉新化所村人。從小熱愛舞獅并掌握了傳統舞獅技藝,他積極參加各項表演和賽事,在長期的實踐中,他還對獅子旋角、搶炮、登高樓、吐對聯、拜案等動作進行了鞏固和更新,使舞獅得以繼承發展和推陳出新。2015年被評為新化舞獅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傳承人3:劉秋生,漢族,1962年生,錦屏縣新化鄉新化所村人。1982年開始學習舞獅表演技藝,他在任新化所村民委員會主任時積極開展舞獅技藝培訓和展示展演活動,他在當地著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使得舞獅文化在社會上得到發展傳播。劉秋生在2011年被國家認定為新化舞獅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除此之外,他還在縣級非遺項目新化水龍的傳承發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2015年時成為新化水龍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傳承人4:閔樹民,苗族,1954年生,錦屏縣新化鄉新華所村人。12歲開始學習舞獅,逐步掌握技藝與要領。在當選新化所村黨支部書記時積極組織開展舞獅文化的培訓,舉辦省、州、縣的展演活動,為弘揚舞獅文化和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做出很大貢獻,在2013年成為新化舞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3 體育非遺新化舞獅面臨的傳承困境
3.1 群眾非遺自覺保護意識和宣傳力度欠缺
以往當地民眾雖常年能看到新化舞獅活動,但缺乏對非遺新化舞獅文化的自覺保護意識。這是因為新化舞獅文化傳承的宣傳和普及力度不夠,傳承意識和民俗文化意識普及化程度低。非遺傳承不只是對物質形態與技藝進行保護,群體的文化認同感更是傳承的活力源泉。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新化舞獅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人們接觸的現代化信息較多,視野打開的同時存在崇洋媚外的心理,對傳統的文化不夠重視。新化所村當地民眾認為舞獅只是一種娛樂活動,并沒有非遺文化保護的自覺意識,且舞獅活動展示的平臺日益減少,更使得新化舞獅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因此,提高當地群眾的文化認同感和文化自覺保護意識是新化舞獅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
3.2 非遺的“活態”傳承人才青黃不接
非遺的“活態”傳承需要依附于承載著非遺制作技藝與地方文化的群體來完成。[9]從傳承人才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生活方式和外來文化的沖擊,新化舞獅文化的傳承人員,年齡結構偏大,年輕人很少愿意去傳承,沒有穩定的新成員加入,固定傳承人就只有劉毅、閔文澤、閔樹民、劉秋生四位,據訪談得知,新化舞獅沒有固定的學習者,主要以在學校訓練的學生為主,缺乏專業的訓練基礎,政府也沒有專門的生活補貼,許多村民為了生計外出謀生。學校舞獅課程雖在實行,但多數家長也只抱著讓孩子了解傳統文化、娛樂和鍛煉身體為主,并未讓其發展成為傳承人的意愿,再加上升學的流動,這種模式也很難留住和培養傳承人。
3.3 政府缺乏對非遺保護的系統管理,資金不足
政府是傳承地方傳統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動者,文化保護和傳承需要依靠當地政府的引導和決策,政府的有效介入是地方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因素。新化舞獅沒有制定明確的系統管理法規和規章制度,這使得新化舞獅處于缺少法規保護的危險地位。新化舞獅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后,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新化舞獅在進行文化宣傳活動時,政府會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助用于增添設備和制作服裝道具,雖有一些經費用于文化宣傳,但其他活動均由村民自費。新化舞獅的宣傳、傳承人才的培養、市場操作運營等均需要大量的資金維持,對資金的需求較大,但它不像其它非遺項目一樣每年都有一定的資金投入,資金的短缺致使新化舞獅的傳承發展缺乏資金和政策的推動。
3.4 原生態教學和表演內容匱乏、專業化程度低
目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新化舞獅在學校并未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只是作為一項特色課程、大課間操和課余少年宮活動,而且,在校內從事該工作的只有舞獅傳承人劉毅和一些臨時培訓的老師來給學生指導,并沒有固定的專業化教師,課程訓練中缺乏專業性和針對性的指導,學校活動場地太小,課外活動時間少,過于分散的訓練讓舞獅學習成效不高,兼備非遺專業素養和體育技能的師資非常匱乏,教學形式過于原生態和老套,使得學生對舞獅積極性不高。新化鄉成立的鄉村“文藝隊”,是當地村民自發組建的團隊,目的只是在農閑和節慶的時候作為娛樂活動,并沒有進行專業訓練,內容也是老一輩口傳身授遺傳下來的,動作較為單一老套。
3.5 新化舞獅逐漸商業化且文化單一
以前當地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沒有受到外來文化過多的干擾,非遺體育新化舞獅得到了較好的傳承發展,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和國家脫貧攻堅的完成,當地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質量和經濟的發展逐漸提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外來文化的沖擊,思想觀念的轉變,逐漸影響著新化舞獅的文化傳承向商業化方向發展,且新化舞獅的產業文化過于單調,沒有形成一定的品牌影響力,經濟影響力不高,影響可持續發展,所以,加強新化舞獅與當地經濟、旅游業以及少數民族的風情結合尤為重要。
4 體育非遺新化舞獅的傳承發展路徑
4.1 加強宣傳,提升政府和群眾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覺保護意識
為保證新化舞獅文化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廣度和深度,新化鄉委會宣傳部應利用多種媒介渠道加大對新化舞獅文化的宣傳力度,保障新化舞獅的宣傳、推廣的深度和遠度。著重普及當地民眾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保護意識,尤其面對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更要保持更高的民俗文化認同感,樹立牢固的文化自信意識,堅定對本民族文化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
4.2 建好“非遺”人才隊伍,人人皆可“傳承人”
非遺的傳承創新是凝聚當地民眾的民俗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傳承人是文化發展的重要載體,新化舞獅文化歷史悠久,傳承人受到保護,非遺也就得到了保護。斷代現象,青黃不接是非遺傳承人正在面臨的困境。政府應完善傳承人保障機制和傳承人管理機制,積極開展教育傳承工作。可以在每年舉行舞獅活動教師培訓班,社會人士和學校教師均可參加,并進行評級體系。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同時,也要有確保對非遺傳承人的財產保障措施,讓他們依法享受獲得報酬的權利,有效解決傳承人生活保障問題,逐步探索并建立一種以模范優秀傳承人為核心,大眾傳承人為中心的非遺傳承體系。
4.3 提高政府宏觀把控和經濟支持力度
新化舞獅文化的傳承發展需要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去管理和落實。要想提高非遺新化舞獅資源的影響力和輻射力,無論是加大宣傳,還是資金投入,都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利用現代媒體的宣傳功能,讓舞獅文化拉近與公眾間的距離。非物質文化多是以手工技藝為表現手段,宣傳上也應該是流動、直觀的,而不是呆板的文字信息介紹。政府更要宏觀把控,加大對學校的資金投入,來建立舞獅班活動基地;組織人力物力,積極培養舞獅班專業指導人員,提高培訓效率;對新化舞獅開展文化研究、技藝研究、精神研究小組,展開民間遺產保護工作;給予傳承人基本的生活補貼,保障基本生活。
4.4 原生態傳承與數字平臺創新同行
根據時代變化和現代人喜好對新化舞獅動作進行創新改良,新化當地可以打造“小獅人”特色舞獅隊,提高群眾對新化舞獅的興趣,創編符合當地特色的動作吸引觀眾眼球,改變大家對舞獅固化的動作觀念。在訓練和表演的過程中向學員和觀眾傳達舞獅文化精神和內在含義。新化舞獅保留原生態傳統文化的同時積極迎合大眾審美,建立非遺數字化保護平臺,利用圖片、音頻、視頻的手段,用不同形式組成舞獅“活的記憶”。平臺創建查閱和圖片視頻展示,還可以增加互動環節拉近與公眾之間距離。數字化平臺的創建可以讓舞獅文化不被遺忘在時間長廊里,通過該平臺多功能讓非遺新化舞獅得到更好的傳播和傳承。原封不動地繼承傳統文化不是目的,只有立足創新,才能使新化舞獅得到更深遠的發展。
4.5 轉化新化舞獅的產業方向化
轉化新化舞獅項目的產業化有利于優化非遺傳承的方式,將非遺傳承的教育由繼承向教育、旅游和就業教育方向的轉化,一方面提升非遺的經濟價值,增加就業機會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可以促進新化舞獅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新化鄉應該抓住鄉村振興的政策,在舉辦的新化舞獅文化藝術節吸引來大批游客,宣傳新化舞獅文化,發展鄉村旅游產業,可以與當地優良的環境和民族風情結合打造開展舞獅活動特色村,建立有民族體育文化的特色產業,既能推廣和傳承當地舞獅文化,又能提高本地人收入,帶動經濟增長,促進綜合旅游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