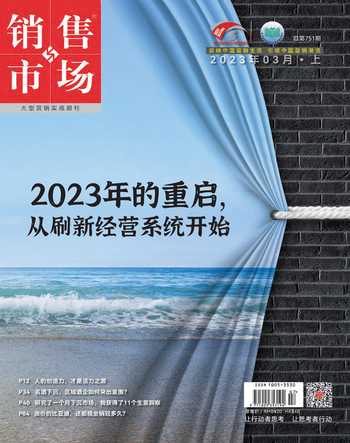刷新經營系統的兩個抓手
我們談刷新經營系統,要有具體的抓手。有了抓手,才能真正把刷新之后形成的經營理念,轉化為現實的行動。從我的個人體會和大企業的一些體驗來看,有如下兩個具體活動可以作為抓手。
大家之前也對價值觀有一些理解,但今天講的這個體系和以前大家接觸的可能不太一樣。“科學管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哈林頓·埃默森說過:“清晰明確的理念體系是組織協同的基礎。組織的生命力來自從頂級開始到下一級能協調一致,共同推動組織的發展。如果組織中的人采用相異的理念,就會將組織作用于不同的方向,其結果一定會產生消極的負面影響。”
一個企業的組織,其力量建立在所有人遵循同一套價值原則的基礎上,如果這些人遵循同一套價值原則,大家看到的機會就具有一致性,去打仗的時候就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一個組織協同的基礎、存續力量的基礎。如果不具備一致性,企業家的想法和基層的想法不一樣,組織就會離散,力量就無法存續。從小到大的所有企業都需要這套理念系統,即便沒有系統的表達,但是經過長時間的磨合,形成了核心團隊,核心團隊成員之間的理念系統是具備一致性的。
越是有一致性的企業,越能表現出強有力的組織能力;越缺乏一致性,組織能力就越弱,人的心智資源容易被分散。
1.組織的三大問題和三大機制
當環境發生變化,需要再重新調整經營理念的時候,管理者可能無法完成同步調整,這時候組織就有可能發生離散。那么如何在環境變化的時候,根據環境讓管理者同步刷新這套理念體系?
華為在1996年就面臨這個情況,當時它的規模急劇擴張,原來這些人的評價、定工資、分配任務以及公司的大決策都是老板來定;而當人多起來,決策就開始離散,這個時候組織建設無非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組織的動力從哪里來?早期動力來自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發現機會,把人組織起來,帶著這幫人往機會上靠,去改變這些人的習慣、工作方式,把他們統一到機會上來。但是當體量開始變大時,組織動力僅僅依靠企業家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所以,如何根據市場機會的力量把這些人組織起來,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如何突破個人局限?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謂組織就是讓不同的人按照分工的方式形成互補,把所有人的長處加在一起。個人是有局限的,能力有局限,時間有局限。即便企業家再厲害,但很多事情沒在一線,沒有體驗,臨場信息不夠,這時候必須突破個人局限。怎樣讓不同的人都做出貢獻,超越企業家的個人能力邊界,這是組織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如何做到大而不散、大而不僵、大而不亂,使組織仍然保持一個整體?即便體量再大,業務中也有內生的一致性,管理者的決策也有一致性。
建設組織本質上就是回答這三個問題,而解決這三大問題則需要三大機制。
第一個機制,利益機制。解決分錢、分譽、地位的問題,把錢分好了,從利益出發,只要圍繞著機會、圍繞著績效、圍繞著合作建立組織,就能把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統一起來,這樣就解決了利益機制的問題。
第二個機制,分權機制。把決策權力分配給那些專業的人、了解實際情況的人,即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去決策,這叫分權。我們研究治理結構,研究組織結構,研究職位體系的設計,其實本質上都是理順權責機制,從而更好地去分權。

第三個機制,評價控制。這些人有了動力、有了權力,但是在組織里,每個人都會夸大自己的貢獻,都會有濫用權力的傾向,要讓他們為我所用,就需要評價機制。通過機制去評價其績效、能力、行為,看權力是否濫用、責任是否履行、貢獻是否到位。
這三大機制正好對應組織的三大問題:動力從哪里來?如何突破個人局限?如何做到大而不散、大而不僵、大而不亂?但是,僅僅設計這三大機制,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機制在運行中很難實現絕對公平。比如華為鐵三角,三個人搞定一個訂單,一個搞定客戶關系、一個搞定解決方案、一個搞定交付,這三個人誰的貢獻大、誰的貢獻小?其實離開誰都不行。
2.機制背后的難題:統一價值前提
機制能否發揮作用,表面上是基于客觀事實的選擇,即事實前提,包括贏不贏利、可不可靠、技術上通不通、投資上過不過得去、人的能力行不行等,而本質上機制發揮作用、產生力量的前提是,組織中的人認為它是合理的,這就是價值觀的問題,也是隱藏在機制背后的難題——價值前提。
機制能不能被大家接受,取決于背后這些人是不是認可,是不是有相同的價值觀、相同的價值排序。比如開發一個產品,到底是等成熟后才上市,還是先做到八成熟到市場上占坑,這就是價值判斷。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決策。
有一個做醫療器械的企業,早期產品質量很差,經常出現低水平的質量問題。我和老板說:“你是做醫療生意的,怎么能做不合格的產品呢?”老板說:“苗老師,你不知道,國外的進口產品做一臺手術需要7萬—8萬元,用我的產品做一臺手術只需要2萬元,8萬元的產品大多數老人是換不起的,很多人寧愿忍受痛苦也不換。但我們把成本降下來,很多老人都能換,縣級醫院就能做這個手術。雖然我的產品質量差點,合格率只有95%,但是也讓95%的人獲得了幸福。”我說:“那為什么不能把質量做好了再推向市場呢?”他說:“如果質量做好了,可能3年產品也推不出來,雖然只是合格率提升5%,可是難度太大了。我把現在這個質量水準的產品推向市場,于社會、于企業都是好事。”
類似于這個決策,背后就是價值觀在驅動,而不僅僅是量化決策。諸如此類的決策在企業里有很多,如果不統一管理人員的價值原則,大家不是在一個價值原則上去做事,老板就無法授權,一授權就亂。很多老板授權下去以后,因為價值觀不統一,很快就會對下面人做事的結果不滿意;這時候再把權收回來,下面人就覺得老板出爾反爾。組織經過反復折騰以后,就失去了信用。
所以,統一價值前提是一個企業生存的基礎。很多企業之所以能發展起來,是因為在背后無意識地建立了統一價值前提。當環境發生變化時,這背后的一系列價值原則都需要刷新,如果這種刷新不處于管理狀態,組織就會陷入混亂。
西方在20世紀用二三十年研究科學管理理論得出結論,第一條就是清晰明確的理念體系是齊心協力的基礎。所以一個企業的價值觀一定要清晰,否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就會混亂。
3.刷新組織系統,企業家需要回答的六個問題
在環境變化時,管理者需要審視企業過去的做法是否已經過時,刷新組織系統需要企業家和管理者至少回答以下六個問題,從而調整經營基礎。
第一,如何重新定義機會和增長?
一些企業過去一直在增長,但目前事實上大部分企業都處于低增長狀態,那么經營目標應該如何調整?
一種是從增長到成長。原來的機會是宏觀的機會,現在的增長方式要向抓住結構性機會轉變。當結構性機會發生改變時,我們觀察環境、對市場的認知以及競爭規則也要有相應變化。中國的企業家原來做生意有個邏輯,即看哪里人多就做什么,類似農民種地的思維,人家種啥我種啥。這種邏輯在當時也成立,因為人多的地方市場大,在宏觀上有規模優勢,所以總能找到求生之道。但現在宏觀機會沒有了,如果還是依靠哪里人多往哪里走的邏輯,存活的概率就很低。這時候就需要重新思考業務機會,思考如何調整和變化。
對很多行業來說,現在機會少了,那還要去追求增長嗎?這時候如果還去定增長的目標,可能會不斷打擊團隊的信心。當然也不排除有的企業有結構性機會,那就可以去重新定義增長,原來是外延式增長,現在可以定義為內涵式增長。所謂外延式增長,類似豐臣秀吉式的增長,即擴展地盤、擴大規模;所謂內涵式增長,就是改變內部產業的質量,也可以提高贏利水平,提高核心價值和附加值。也就是說,從增長的概念轉變為成長的概念,去改善業務質量,拉近客戶關系。雖然增長可能沒那么快,但是可以連續發展。
還有一種增長方式,如果企業不幸連成長都無法維持,還可以選擇堅持生長。所謂生長,就是無論再糟糕的環境,你都能活下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當這個行業開始復蘇時,你還能崛起。就像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底下的小樹一直在積蓄能量,有一天當一棵老樹倒下了,周邊的小樹有哪棵能夠盡快吸收陽光、占據空間,它就能成長起來,這就叫生長力。
第二,圍繞機會和增長方式的改變,企業是否具有匹配的核心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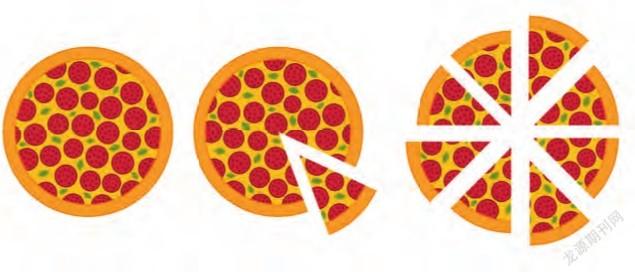
機會和增長方式改變了,需要的核心能力和過去不一樣,比如原來需要的是復制能力、快速響應能力,現在要響應結構性機會,就要做品類創新,這種創新的核心競爭力從何而來?
第三,核心能力是否已經建立在組織上?
只有建立在組織上的能力才是可以管理、可以上升的。怎么把戰略上的核心能力建立在組織上,從哪幾個方面去建?
第四,組織系統是否具有柔韌性和敏捷性?
所謂柔韌性,就是當機會不斷變化和間斷時,組織能夠具有適應性。就像稻盛和夫講的“阿米巴”(變形蟲),組織也需要具備柔韌性。那么柔韌性從何而來?過去一些企業強調流程、強調硬性的規則,現在一些企業開始強調小的作戰團隊、強調劃小核算單元。其實劃小核算單元并不是本質,本質是每個核算單元里要有柔韌性,從固定化的組織變成團隊,而團隊之間具備嚙合關系,就有了柔韌性。那么企業怎么去改造自身的柔韌性?
第五,核心干部隊伍是否過硬和具有學習力?
當企業面臨的環境發生變化、增長邏輯要調整的時候,沒有現成的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走,這時候拼的就是核心干部隊伍對公司的歸屬感,他們是否愿意根據公司環境的變化去調整自己,獲得新的能力,這就表現為學習力。
每個企業其實都是一直在創業,去年做5000萬元,今年做8000萬元,明年做1億元,企業里從老板到員工都沒有經歷過新的規模形態,所以對大家來講企業一直在創業,要不斷解決一些過去意識不到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核心干部隊伍如果學習力弱、僵化,或者對企業的歸屬感不強,就只是打一份工,那企業應對環境變化的能力就弱。
第六,企業成敗的要素是否處于管理狀態?
這些要素一開始可能不成熟,達不到要求,那怎么通過管理讓它從不具備條件到具備條件,從不成熟到成熟,從沒有能力到獲得能力,一步一步變強,我們稱之為管理狀態。
以上就是企業在環境變化時刷新組織系統要解決的六個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重構企業內部的組織系統和管理系統。
第二個要開展的活動,是熵減活動。“熵減”這個詞來自物理熱力學領域,這兩年已經被引入管理學界。物理學中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又稱“熵增定律”,表明了在自然過程中,一個孤立系統的總混亂度(即熵)會不斷增加。熵積攢多了,系統就變得越來越沒有活力,最后就會死亡。組織內部同樣有一種熵,熵不斷減少,組織才會有活力。
1.推特、小米、阿里巴巴的熵減實踐
近幾個月全球范圍內,一些知名企業都在進行熵減活動,最典型的是馬斯克在推特的實踐。馬斯克是一個極負盛名的天才,他搞特斯拉、搞火箭發射,2022年10月又花440億美元收購了推特。推特很有人氣、很旺盛,內部人才濟濟,業務很成熟,用戶規模和活躍度都很高,但就是不賺錢,因為沒有贏利模式。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先搞了三輪裁員。據說第一輪裁員特別夸張,7000人先裁掉一半;第二輪開始評估能力,凡是沒有業務能力的,比如不能寫代碼的,全部裁掉;第三輪再精準裁員。隨后,他開始重新設定業務規則,探索用戶付費的贏利模式。我認為這就是典型的熵減,把內部不適應這個企業增長和贏利的東西全都清理掉。對馬斯克而言,企業能夠活下去、能夠活得好,是第一位的。
再看小米的高層大調整。2022年12月,小米也在做大調整,一是把總裁換了,二是讓“老干部”退休,三是提拔年輕的副總裁。小米每次在業務困頓的時候都做人事調整。其實小米那些“老干部”也不老,剛剛50來歲,都是當打之年,那為什么要把他們換掉,讓更年輕的人上?
因為小米在做戰略轉型,從過去的低端戰略轉向高端戰略。小米的產品之前是滿足收入低、有活力的年輕人群的需求,主打性價比;現在行業開始穩定,要增加利潤必須走高端戰略。但是從低端人群轉向高端人群,需求的性質、排序都會改變。而管理者已經被過去的邏輯高度馴化了,在往上轉型的時候,這些人在新的場景下想改變自身邏輯是很難的,每個人都很難從底層把自己的邏輯全部清理掉。所以小米搞人力結構調整。
阿里巴巴也是如此,阿里云戰略也開始做大量的高層調整。阿里巴巴本身是立足于做基礎設施的,但是阿里云和釘釘現在遇到了挑戰,不像原來支付寶、淘寶這種基礎設施性質的業務,現在這兩個業務遇到了企業微信、遇到了華為、遇到了字節跳動的挑戰,業務邏輯能不能走下去還不一定,所以阿里巴巴也在重構人力結構。
2.熵減:減掉慣性之中與環境變化不一致之處
企業面臨的環境發生變化時,要去清理組織中的熵,所謂熵就是慣性與變化不一致之處。組織是有慣性的,人都會沿著自己熟悉的路線去做事,組織里的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按照固定的文化運行;組織結構一旦形成,每個人固守自身的位置,結構就很難調整,很容易板結,這些都是企業中存在的慣性。但是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慣性就會和環境產生不一致,轉彎轉不動,必須把這種不一致減掉,這就是熵減。而且這種不一致可能會存在于業務中。如果業務一直習慣于按照一種模式去運行,當環境發生變化時,業務結構就需要調整,要改變過去那些與新業務形態不適應的東西。
有一家服裝企業,主要做高端品牌,在行業內很有影響力,規模也很大,年銷售額有七八十億元。在服裝行業的互聯網線上模式沖擊下,這個企業面臨一個難題。老板認為高端業務一定要有豐富的線下體驗,認為線上的都是低端的,會導致品牌低端化,這種觀念造成該企業業務線上轉型困難。但是實體店受到的沖擊越來越大,業務結構不調整,肯定走不下去。
為什么西方的品牌企業持續越久,它的品牌力越強,能跨越不同消費趨勢的變化,而中國的品牌企業過幾年就換一茬?實際上業務背后最重要的是要與顧客的聯系節點同步,去做相應改變,而不是以一成不變的思維來經營。線上也可以經營高端品牌,而這個企業的問題就在于過于依賴過去的慣性。這是業務中的熵。
組織中人的重構、企業用人也需要熵減。當企業用慣了幾個熟悉的人之后,雖然他們與老板的價值觀一致,但是在過去的成功邏輯越來越強的時候,這些人反而表現出好像在兢兢業業但事情卻干不好,很“忠誠”地阻礙了企業的變革。
這就需要進行人的重構,這也是熵減。再比如文化的重構、價值觀的重構,企業刷新內部的理念體系,即組織結構的重構、機制的重構等,每一種重構之中都有一些熵減的活動。我不稱其為變革,因為變革很容易傷筋動骨,而企業把每個領域里的熵減掉,是可以常態化開展的活動。
今年媒體都在講相信和勇氣,我一直認為企業家在熵減活動里最需要勇氣,因為我們都不愿意擺脫過去的慣性。我們更應該去判斷自身的業務結構、組織結構、人才結構中存在哪些熵,勇敢地采取一些措施,將其耗散掉,如此才能夠刷新自己。
在一個不確定的時期,長期來看,我們要堅定信念,對做企業,對我們的人生,要有一個信念級的東西支撐我們。堅信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保持這種信念。中期來看,我們要保持信心,只要按照做企業的規律去做,總會走出一條路來。短期來看,我們要保持達觀,對于看不懂的事情,也秉持接納的心態。
在這個變化的時代,快不是重要的,觀察才是。我們需要在一個不斷觀察的過程中,根據環境的變化去做相應調整。(苗兆光,華夏基石高級合伙人、副總裁,華夏基石大師塾訓戰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