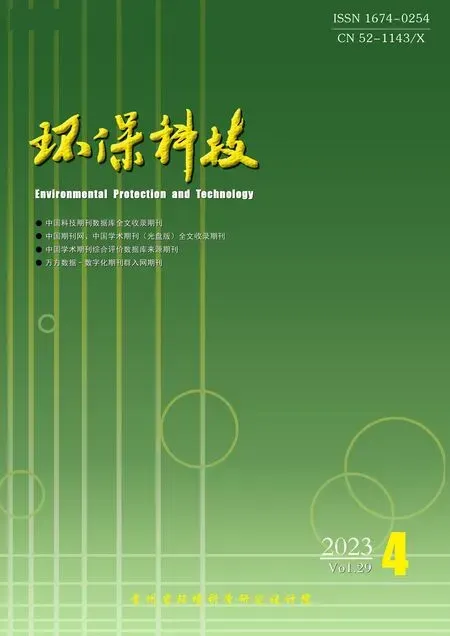水生動物群落調控在富營養化水體治理中的研究進展
司馬小峰
(安徽省城建設計研究總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230051)
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我國水體的富營養化日趨嚴重, 2020年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中營養和富營養的湖泊(水庫)所占比例分別為61.8%和28.1%[1],水體富營養化不僅影響水體景觀、阻塞供水系統,而且污染水質,甚至危及人類健康,已成為威脅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
經過近年來的持續研究,國內外學者逐漸總結出富營養化水體治理的方針為“外源截流、內源清除、活水循環、生態修復”,污染源控制后進行生態修復是實現水體“長治久清”的關鍵[2-3]。生態修復工程主要是通過構建水生植被、投放水生動物改變水體內氮磷的化學循環,使水體內多余的氮磷隨水生動植物的收捕而被移除[4]。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等均為水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種生物的生物量由捕食和競爭等關系進行控制,進而影響氮磷等營養物質的遷移轉化,水生植物在富營養化水體生態修復的相關研究較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5-7]。科學家們對水生動物群落調控也開展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8-10],歸納起來,當前被廣泛使用的水生動物調控包括魚類、底棲動物、浮游動物和聯合調控等方法。盡管治理方法多種多樣,但對這些方法的應用范圍和存在問題等缺少系統對比討論。因此,本文對這些治理方法進行綜述,旨在通過介紹不同調控方法的理論、適用范圍以及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合理化建議,為富營養化水體生態修復工作提供科學參考。
1 魚類調控
魚類群落調控主要通過改變不同營養級間攝食關系從而達到控制水體生態平衡的目的。1961年,Hrbacek等[11]發現魚類群落結構的變化能顯著影響水體水質和營養水平,從而提出水體浮游動物數量取決于水體中營養物質和魚類。1975年,Shapiro等[12]提出了生物操縱理論,認為增加肉食性魚類數量或減少濾食性魚類數量可以調節浮游動物的種群結構和數量;促進植食性大型浮游動物的生長,從而減少浮游藻類數量,提升水體透明度,并改善水質,此即經典生物操縱理論[13]。在36個丹麥湖泊十余年的應用中證明了其效果,通過反復清除雜食性魚類,增加了水體內水生植物生物量與浮游動物的攝食壓力,水體的氮磷濃度及葉綠素含量均下降了50%~70%,并使水體保持在清水穩態[14]。江蘇傀儡湖與廣東惠州西湖生態修復過程中,也通過投放食魚性魚類、捕撈浮游食性和草食性魚類實現了魚類群落結構調整,隨后水體葉綠素a濃度顯著降低,透明度明顯提升[15-16]。由于經典生物操縱前一般需通過捕撈來控制浮游食性魚類的數量,所以在與外界交換頻繁的水體中實施難度較大,另外,高濃度藻類和體型大的藻類會抑制浮游動物的捕食,所以在營養鹽上行效應占主導的水體難以發揮作用[9]。
部分學者[17]在實際應用研究中提出了非經典生物操縱理論,即通過放養濾食性魚類直接濾食浮游植物從而控制水華發生。謝平等[18]通過原位圍隔實驗發現濾食性魚類鰱、鳙能有效控制微囊藻水華。濾食性魚類主要通過它們特殊的濾食器官對藻類進行控制,這些濾食器官由腮耙、腮耙網、腭皺和腮耙管組成,藻類尺寸小于腮孔時隨水流漏掉,尺寸大于腮孔時則被截住送到消化道,鰱、鳙能濾食10微米至數毫米的浮游植物,從而控制藍藻水華,這在千島湖沿岸池塘和洱海紅山灣的應用中均得到了驗證[19-20]。
利用濾食性魚類控制富營養化水體藍藻爆發有其局限性,可以用于控制藍藻等大型藻類的種群數量,但不能用于控制整個水體中浮游植物生物量[21]。由于大部分藍藻細胞的衣鞘較厚,導致鰱鳙對其消化率很低,只有25%~30%,未消化的藍藻細胞會隨魚類糞便再次進入水體,并且長周期下會導致水體內浮游植物逐漸向難消化的種群演化,影響水生態系統整體結構與功能[22]。利用濾食性魚類控藻效果影響因素較多,包括水體類型、浮游植物群落結構、放養模式與放養密度等,鰱魚和鳙魚濾食的浮游植物主要為藍藻和綠藻,鳙魚食藍藻多,鰱魚食綠藻多,利用鰱、鳙控制藍藻等大型藻類群體時,其密度達到閾值效果較好,放養密度為50~80 g/m3,鰱鳙搭配比例為3:1或者4:1時控藻效果較好,并且在水華爆發前投放的效果比水華爆發后效果更好[21],這主要是由于水華爆發前藍藻細胞較為幼嫩,容易被鰱鳙魚消化利用,從而限制藍藻的增殖,當水華爆發后,藍藻細胞壁已經老化,大量無法消化完全的活藻會通過魚糞再次進入水體。
單一魚類群落進行調控存在較多不足,研究人員開始考慮多種魚類進行協同調控,Peng等人[23]在福建龍湖進行了多種魚類調控研究,他們發現經典生物操縱、非經典生物操縱與雜食性魚類復合操控的效果較其他單一操控手段效果更好,優化了藻類群落結構,且藻類生物量得到有效控制。Chen等[24]在四川東平湖的研究以及蔡杏偉等人[16]在江蘇傀儡湖的研究也表明濾食性魚類與食魚性魚類等的復合調控手段能取得良好的生態效益。
2 底棲動物調控
底棲動物是水體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水體生態系統功能與健康的重要生物指標。大量研究發現,底棲動物具有多種生態功能,包括促進水底的有機碎屑分解,調節沉積物-水界面物質與能量交換,同時也是食物鏈的重要環節[25-26]。濾食性貝類隸屬于軟體動物門,種類多且分布廣,多以浮游生物為食,是富營養化水體治理中應用較多的底棲動物種類[27-28]。
濾食性貝類的濾水能力很強,文獻報道翡翠貽貝濾水率可達2 L/g·h[29],牡蠣的濾水速率可達4.8 L/g·h[30],大量的研究發現濾食性貝類如三角帆蚌[31]、背角無齒蚌[32]、褶紋冠蚌、湖螺、[33]河蜆[34]等能通過這種對浮游植物、懸浮顆粒的濾食作用而降低水體葉綠素a和懸浮物,使水體透明度提高,有效控制水華爆發。濾食性貝類對于藻類的濾食作用具有選擇性,這種選擇性主要與顆粒物的大小相關,比如三角帆蚌更容易濾食粒徑在10~40 μm范圍的浮游植物,而圓背角無齒蚌更易選擇2~30 μm粒徑的浮游植物[35]。
然而該方法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濾食性貝類不能完全消化藻類細胞,沒有消化的藻細胞會被糞便包裹排出而重新進入水體,沉入水底的糞便也會加重沉積物中營養負荷[36],此外,底棲動物的生物擾動作用會破壞沉積物原有的表層結構,從而導致底泥中氧氣滲透深度、含水率及總微生物活性均有所增加,促進了沉積物內營養鹽的釋放[37]。
3 浮游動物調控
浮游動物是水生態系統中重要類群,在水中營浮游生活,也是經典生物操縱理論中的關鍵環節,國內外大量研究學者利用浮游動物進行控制水體富營養化的研究。張麗彬等人[38]在于橋水庫的試驗發現,在營養鹽ρ(TN)為3 mg/L、ρ(TP)為0.02 mg/L左右時,輪蟲、枝角類和橈足類等浮游動物可以通過攝食作用顯著控制藻類過量生長。
熊春暉等人[39]在上海滴水湖的研究發現大型溞和隆線溞實驗組浮游植物密度較空白組分別降低了70.3%和80%,葉綠素a濃度較空白組分別降低了80.4%和75.2%,葉綠素a和氨氮、可溶性磷顯著相關,主要是大型溞和隆線溞對沉水植物表面附著藻類具有一定牧食作用,從而提高沉水植物的光照吸收,促進自身生長并降低水體營養鹽濃度。韓士群等人[40]研究了長肢秀體溞對幾種藻類的牧食作用,結果表明長肢秀體溞可以用于控制水體藻類,其對不同藻類選擇性有較大差異,對小球藻和斜生柵藻的攝食速度分別是銅綠微囊藻的89.8倍和92.7倍,并且其攝食速度受藻類生物量影響較大,隨著藻類生物量增加而增加,但超過攝食飽和值后反而會下降,其對斜生柵藻和銅綠微囊藻的攝食飽和值分別為17.33 mg/L和4.42 mg/L。大型溞已經被用于相關水體治理工程實踐中,一方面利用其對藻類的直接攝食作用,另一方面利用其分泌物的絮凝作用降低水體懸浮物,提高水體的透明度[41-42]。張喜勤等[43]直接將大型溞和方形網紋溞投放到長春南湖進行試驗,4個月內總氮降低了54.55%,總磷降低了44.46%,CODCr降低了53.34%,SS降低39.58%,透明度提高了139.3%,對富營養化治理有較好效果。
4 聯合調控
早期利用水生動物修復水體生態系統主要是對系統內某一營養級進行調控,沒有考慮調控整個生物鏈的作用。近年來研究開始將水生動植物與鰱鳙等進行混養,利用食物鏈組合來改善水質。陳永鋒[44]進行了不同生物鏈組合的水體治理試驗,發現“鰱鳙魚+美人蕉+底棲+生物填料”實驗組效果最好,葉綠素a降低了85.59%,總磷和總氮降低均達到85%以上,氨氮和CODMn降低分別達到78%和66%,顯著高于其他生物鏈更短的實驗組,表明生物鏈越完整,控制水體藻類數量與營養鹽濃度的效果就越好。
劉耘彤等人[45]研究了“浮游動物-沉水植物-魚類”的立體復合生態修復對水體浮游植物群落結構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立體復合修復后有效控制了藍藻,水體內浮游植物生物多樣性增加,明顯改善了水質。熊文等人[46]構建了沉水植物群落后利用投放的鰱、鳙對水體上層浮游植物進行控制,利用投放的底棲動物對下層藻類進行控制,中后期又利用烏鱧、錦鯉等其他食性的魚類豐富了食物鏈,明顯改善了水體水質,透明度由0.2~0.4 m提高到了1.0~1.5 m,溶解氧濃度由1.82~2.35 mg/L提高至5.21~6.28 mg/L,CODMn、TN和TP去除率分別達到73%,50%和83%。
5 總結與展望
水生動物群落調控在水體生態修復工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單一的水生動物調控措施都有其局限性。由于水體形態、水質、生物條件的復雜性,且水生動物之間的種群和種間關系也十分復雜,在具體的水體修復中不可能只采取一種調控手段就取得好的修復效果,應針對水體自身特性與各種調控措施的局限性進行聯合調控,構建食物鏈或食物網,結合水生植物修復與微生物技術,以達到預期治理效果。在后續的工作中需要進一步研究水生動物、水生植物以及微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構建完善而穩定的水生態系統,降低系統維護管理成本,保持水體長效清潔,這對水體富營養化治理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