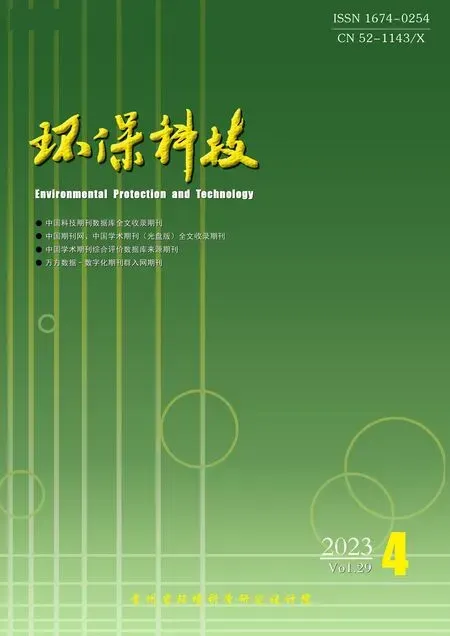濕地土壤重金屬的研究及進展
趙 津
(煙臺市萊陽環(huán)境監(jiān)控中心,山東 煙臺 265200)
濕地是位于陸生生態(tài)系統(tǒng)與水生生態(tài)系統(tǒng)之間的過渡地帶,具有獨特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調節(jié)功能,是全球三大生態(tài)系統(tǒng)之一,在維持生物的多樣性、降解污染物質、抗旱、防洪以及調節(jié)氣候等方面具有其他生態(tài)系統(tǒng)不可替代的作用[1]。濕地一般位于地勢比較低洼的地區(qū),容易接收來自河流等污染物質的輸入,因此,隨著環(huán)境問題的日益增加及突出,保護濕地以及保持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性的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社會的熱點。在許多情況下,濕地擔任了重金屬儲存庫的重要角色[2]。但是當重金屬的含量超過濕地所能容納的環(huán)境的容量時,濕地就會逐漸的變成重金屬的提供者,從而危害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穩(wěn)定性。濕地的研究已經(jīng)逐漸成為許多國內外研究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濕地的定義,國際《濕地公約》這樣給出,“不問其為天然的或人工的、長久的或暫時性的沼澤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帶、靜止的或流動的、淡水、半咸水、咸水體,包括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水域。還可包括與濕地毗鄰的河岸和海岸地區(qū),以及不位于濕地內的島嶼或低潮時水深超過6m的海洋水體”[3]。
重金屬由于其在環(huán)境中的難降解性、毒性、生物富集性等地球化學特征,被認為是嚴重的污染物質,具有潛在的生態(tài)危害性[4-7]。重金屬的存在、遷移和轉換,可能會對土壤、水體、沉積物等產(chǎn)生嚴重的重金屬污染,并且會對人類、動物、植物和其它生物產(chǎn)生持久性的潛在風險性[8-9],重金屬在土壤中的積累可能會給周圍環(huán)境帶來比較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
1 不同類型濕地重金屬的研究
濕地根據(jù)成因分為天然濕地和人工濕地兩大類,天然濕地分為濱海濕地、河流濕地、湖泊濕地和沼澤濕地4類[10]。
1.1 濱海濕地
濱海濕地是位于海洋與陸地之間的過渡地帶,研究濱海濕地的變化,可以為近海岸的濕地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及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保護提供依據(jù)[11]。劉志杰等[12]對黃河三角洲濱海濕地表層沉積物進行了分析,發(fā)現(xiàn)黃河三角洲濕地的主要的潛在生態(tài)風險因子是重金屬Cd,這一結果與姚新穎[13]對黃河三角洲濕地土壤重金屬的研究分析得出的結果是一致的。馬香菊等[14]對天津臨港濱海濕地公園重金屬進行了監(jiān)測,發(fā)現(xiàn)Cr、Cu、Zn和Cd不同程度超過我國土壤環(huán)境背景值。
1.2 河流濕地
河流濕地包括跟河流連接的淺湖,河流的岸邊帶,以及河邊、河叉、河口的沼澤區(qū),具有凈化水體,降解污染物,調蓄洪水,調節(jié)河川徑流及維持生物多樣性等功能特點[15-16]。敖亮等[17]對三門峽庫區(qū)河流濕地沉積物重金屬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重金屬累積發(fā)生在渭河入黃口下游處,重金屬Cu、Cd、Pb的污染及累積最為明顯。張軍等[18]對會仙濕地典型河流重金屬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Hg的強生態(tài)風險率高達95.8%。
1.3 湖泊濕地
湖泊濕地是屬于流域內的水陸交錯地帶,具有凈化水體、保持生物的多樣性、維持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性等作用,湖泊濕地又是相對脆弱的地帶,是流域可持續(xù)發(fā)展、以及流域生態(tài)學研究應密切關注的地帶[19]。Zhang等[20]對衡水湖濕地水、沉積物和蘆葦中進行重金屬研究發(fā)現(xiàn),沉積物中重金屬的含量最高。朱嵬等[21]對寧夏黃河流域湖泊濕地底泥重金屬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以現(xiàn)代工業(yè)化前,正常顆粒底泥中重金屬含量的最高背景值作為參比值,重金屬的單因子生態(tài)危害程度順序為:Cd >As >Hg >Pb >Cu >Cr >Zn,重金屬的富集系數(shù)順序為:Cr >Pb >Zn >Cu >As >Cd >Hg,鶴泉湖底泥中重金屬的潛在生態(tài)危害性相對最高,其他湖泊底泥中重金屬的潛在生態(tài)危害性比較輕。
1.4 沼澤濕地
沼澤濕地是典型的濕地類型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態(tài)調節(jié)功能,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2]。葉華香等[23]對扎龍濕地表層沉積物重金屬的含量進行研究,以松嫩平原土壤背景值作為參比值,發(fā)現(xiàn)重金屬Hg、As、Cu、Pb、Zn、Cd、Cr的平均含量都超標,并且含量分布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各重金屬相互之間呈現(xiàn)著極顯著正相關性,除了Hg、Pb之外,這表明這些重金屬元素之間可能具有著同源性。
濕地重金屬含量及分布特征與濕地的類型、環(huán)境、含量背景值、污染物質輸入輸出量、地理位置等有關,不同類型的濕地重金屬污染因子不同、潛在環(huán)境風險性不同。因此,濕地重金屬研究為濕地保護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jù)及理論價值。
2 濕地重金屬形態(tài)研究
重金屬污染的嚴重性不僅僅取決于重金屬的總量,也取決于在土壤中重金屬存在的化學形態(tài),土壤本身的物理化學性質也會影響重金屬的化學形態(tài)[24]。重金屬化學形態(tài)的研究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類作用及自然作用等對重金屬的生物毒性,以及來源的貢獻。土壤重金屬是以不同化學形態(tài)存在于土壤顆粒物中的,確定重金屬存在的化學形態(tài),對于揭示重金屬的來源、遷移、轉化、以及對環(huán)境的污染程度等具很重要的意義。土壤的化學物理性質等比較復雜,重金屬的化學形態(tài)不同,產(chǎn)生的環(huán)境效應不同[25-26]。因此,對濕地土壤重金屬進行化學形態(tài)的研究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重金屬形態(tài)目前還沒有統(tǒng)一的分類和定義。目前經(jīng)常性采用的重金屬形態(tài)提取的方法有Tessier法、BCR法等方法,Tessier法常被用作土壤及沉積物重金屬形態(tài)的提取。Tessier等[27]將重金屬的形態(tài)劃分為:可交換態(tài)、碳酸鹽結合態(tài)、鐵錳氧化物結合態(tài)、有機態(tài)及殘渣態(tài)五種化學形態(tài)。可交換態(tài),指吸附在腐殖質上、粘土上等的重金屬形態(tài),對環(huán)境比較敏感,容易遷移、轉化,反映人類對環(huán)境的影響,以及對生物的毒性作用;碳酸鹽結合態(tài),指與重金屬結合形成的共沉淀態(tài),受pH值影響最大,pH值越大,越容易形成碳酸鹽結合態(tài);鐵錳氧化物結合態(tài),指活性的鐵錳氧化物共沉淀或吸附陰離子而形成的,水體氧化還原電位較高時,有利于鐵錳氧化物結合態(tài)的形成;有機態(tài),指土壤中各種有機物質等,與重金屬結合而形成的;殘渣態(tài),指一般存在于原生礦物、次生礦物、硅酸鹽等土壤晶格中,比較穩(wěn)定,不易釋放,能長期穩(wěn)定在沉積物中[25-29]。Tessier法是近20年來環(huán)境科學、地球化學、土壤學等領域較多采用的重金屬形態(tài)劃分的方法[30-32]。李如忠等[33]利用Tessier五步提取法對銅陵市惠溪河沉積物重金屬Cd、Cr、Cu、Zn、Ni、Pb、As進行形態(tài)分析,發(fā)現(xiàn)主要以有機態(tài)形式存在于沉積物中的是重金屬Cu,主要以殘渣態(tài)及鐵錳氧化物結合態(tài)存在于沉積物中的是重金屬Zn、Pb,主要以殘渣態(tài)存在于沉積物中的是重金屬Cr、As,這一結果與李如忠等同年一月份利用Tessier法分析研究的結果相一致[34]。臧飛等[35]利用Tessier五步提取法對東大溝、西大溝沉積物中重金屬Cd、Pb、Cu、Ni、Zn、Cr進行形態(tài)分析,發(fā)現(xiàn)東大溝沉積物中主要以鐵錳氧化物結合態(tài)存在的是重金屬Pb,主要以殘渣態(tài)存在的是重金屬Zn、Ni、Cr,主要以有機態(tài)存在的是重金屬Cu、Cd,,西大溝沉積物中Pb主要以鐵錳氧化物結合態(tài)存在,其余重金屬均主要以殘渣態(tài)存在。
BCR法將重金屬的化學形態(tài)分為弱酸溶解態(tài)、可還原態(tài)、可氧化態(tài)、殘渣態(tài)四種形態(tài)[35]。BCR法與Tessier法不同的是,BCR法將Tessier法中的可交換態(tài)及碳酸鹽結合態(tài)合并為一項,稱為弱酸溶解態(tài),BCR法雖然其它幾種形態(tài)的分類與BCR法相同,但提取所用的試劑、溫度、時間等不同[36]。秦延文等[37]利用BCR提取法對太湖表層沉積物重金屬Cd、Pb、Cu、Zn進行形態(tài)分析,發(fā)現(xiàn)四種重金屬以可提取態(tài)(弱酸溶解態(tài)、可還原態(tài)、可氧化態(tài)并稱為可提取態(tài))為主,且可提取態(tài)具有較高的二次釋放潛力性,這一結果與陳春霄等[38]采用BCR提取法對太湖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分析,發(fā)現(xiàn)重金屬Cu、Zn、Pb的可提取態(tài)具有較高的二次釋放潛力的結果相一致。李必才等[39]利用BCR四步提取法對白洋淀底泥重金屬形態(tài)及垂向分布進行分析。
3 濕地重金屬污染評價研究
濕地重金屬來源不同,以及存在的形態(tài)不同,并且形態(tài)的不同導致其生態(tài)效應不同,因此,重金屬的來源、存在形態(tài)、生態(tài)效應等可以由重金屬的風險評價來反映出來。
目前,國內外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的評價方法比較多,如有:地累積指數(shù)法,潛在生態(tài)危害指數(shù)法,單因子指數(shù)法,內梅羅綜合指數(shù)法,生物效應濃度法,富集系數(shù)法,污染負荷指數(shù)法,生物效應數(shù)據(jù)庫法,綜合響應因子法,健康風險評價方法,基于GIS的地統(tǒng)計學評價法等,但目前還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以及成熟的方法[40-42]。重金屬的各種評價方法有其各自的使用特點以及局限性。在進行土壤中重金屬的污染評價時,應該選擇合理有效的一種或幾種評價方法進行評價。盧君勇等[43]運用地累積指數(shù)法及潛在生態(tài)危害指數(shù)法對四川省馬邊老河壩磷礦重金屬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Cd元素危害最大。Arunkumar等[44]利用污染系數(shù)、地累積指數(shù)及污染負荷指數(shù)對印度南部的特里凡得瑯地區(qū)(Thiruvananthapuram)濱海濕地進行研究分析發(fā)現(xiàn)Poonthura濕地和Akkulam-Veli濕地潛在危害熱點地區(qū)。郭偉等[45]利用單因子指數(shù)法及內梅羅綜合指數(shù)法對內蒙古包頭礦尾土壤中的不同重金屬及不同地區(qū)的重金屬進行污染評價,發(fā)現(xiàn)土壤環(huán)境的健康與穩(wěn)定正在遭受著土壤重金屬的威脅。Li等[46]利用單因子污染指數(shù)法(SFCI)、金屬污染指數(shù)法(MCI)、生物-沉積物富集因子法(BSAF)來評價黃河三角洲濱海濕地沉積物及底棲生物中九種重金屬的潛在生態(tài)危害性及生物富集性,發(fā)現(xiàn)重金屬As超標率達50%以上,且九種重金屬的單因子污染指數(shù)秋季比春季要大,金屬污染指數(shù)沒有固定的模式,但生物-沉積物富集因子法表明重金屬Cd從沉積物到底棲生物中產(chǎn)生生物富集。
4 濕地重金屬污染防治對策及生態(tài)修復技術應用
強化源頭的控制,提高濕地重金屬污染防治水平。控制河、湖、江等水質中重金屬的通量,分類別、分區(qū)域對河、湖、江等的水質進行污染防治及監(jiān)管,可采取將直排江河湖等的企業(yè)廢水進行循環(huán)再用,減少排放量,或者提高廢水重金屬治理工藝,如沉淀法、離子交換法、吸附法、電解法等,降低江、河、湖等的重金屬污染,從而減少濕地重金屬的污染;加大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巡查力度,降低濕地重金屬通量。分地區(qū)、分類別對不同江河湖等進行沿岸徒步巡查,將排查到的排水口進行登記記錄,建立排水口臺賬,嚴格排水標準,從而降低濕地重金屬的含量;重視濕地本身的保護,提高濕地的觀賞價值。可充分利用現(xiàn)在的高科技,加強對濕地的在線監(jiān)測力度,可加強濕地的生態(tài)修復技術應用,如植物在濕地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起到吸附重金屬的作用,隨著植物的定期收割,將重金屬從濕地中去除。
5 展望
濕地重金屬研究雖然已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但關于不同類型濕地重金屬污染特點的比較及重金屬形態(tài)的研究比較少,濕地重金屬的污染評價沒有統(tǒng)一的評價方法與評價標準。因此,應重點對不同類型濕地重金屬污染的比較、濕地重金屬形態(tài)、濕地重金屬的污染評價等進行深入研究。在研究上,應注重新技術的應用與開發(fā)。這將更加有利于濕地的保護。
濕地污染不但會使水質惡化,同時還嚴重危害著濕地的生物多樣性。由于濕地保護存在如濕地保護管理體系不完善、監(jiān)測體系不完善、公眾對濕地的保護意識不高等問題,因此濕地的保護及修復尤為重要。應完善濕地的管理保護體系,建立聯(lián)防聯(lián)動機制、部門間建立信息聯(lián)動,以進一步強化對濕地的保護;同時,應加大電視、網(wǎng)絡、報紙等的宣傳力度,提高群眾保護濕地的意識。以為人類創(chuàng)造良好的濕地生態(tài)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