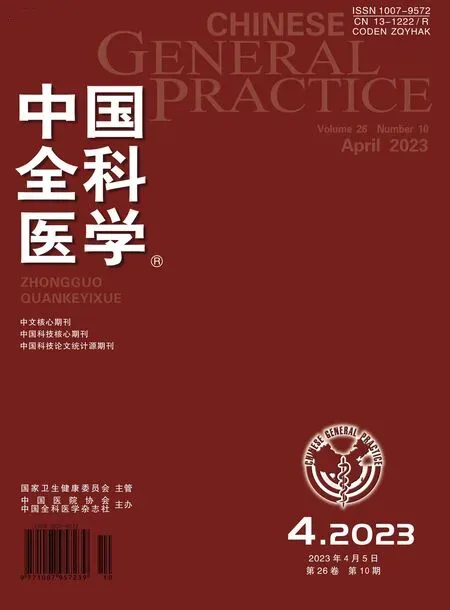親密伴侶暴力的臨床后果及識別與處理技巧
趙梓翔,肖婧,豐艷,姜岳
家庭暴力指在家庭關系中發生的一切暴力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簡稱《反家庭暴力法》)將其定義為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1]。親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屬家庭暴力的一種,WHO將其定義為親密伴侶的行為導致身體、性或心理傷害,包括身體侵犯、強迫性行為、心理虐待和控制行為。虐待關系通常以言語虐待和情感虐待開始,部分可進展至軀體虐待和性虐待。IPV可發生在任何性取向的親密關系中,但多為男性對女性施暴[2]。IPV在世界范圍內是一個棘手問題,但在中國則更有難處。首先,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IPV屬家庭糾紛而非犯罪,這種文化上的容忍進一步加劇了IPV的危害;其次,中國既沒有專業IPV救助機構可供醫生轉診,也沒有醫療指南指導醫生診療,這就導致臨床醫生即便識別出IPV也無法幫助患者擺脫困境。最重要的,盡管《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要求醫生有義務識別和處理IPV并向公安機關報案,但實際上由于缺乏明確的報警標準和獎懲機制,醫生通常不愿意主動報警并進一步幫助患者。本文通過PubMed檢索“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相關文獻,嘗試總結其臨床后果及識別與處理技巧,并討論如何將證據更好地應用于中國。
1 流行病學
IPV是較為常見的家庭暴力,廣泛存在于各種社會經濟、宗教和文化群體中。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對161個國家和地區2000—2018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全球約30%的女性遭受過親密伴侶的身體侵犯和/或性暴力;終生IPV發生率在西太平洋區域約為20%,歐洲約為22%,美洲約為25%,非洲約為33%[3]。2014年,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約35%的女性一生中曾遭受過IPV,約10%曾被親密伴侶強奸[4]。2013年,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中國的抽樣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39%的女性曾遭受過IPV,約10%曾被親密伴侶強奸[5]。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約有1/4的婦女曾遭受過不同形式的IPV,其中明確表示曾遭受過配偶毆打的女性為5.5%[1]。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發生以來,經濟壓力增大、社交模式轉變更是加大了婦女遭受IPV的風險[6]。
2 臨床后果
盡管大多數患者不以IPV為主訴就診,但IPV在全科門診中卻不罕見。在美國全科門診患者中,約38%的女性曾遭受過IPV[7]。如何在各種非特異癥狀和體征中快速識別IPV是臨床醫生的工作重點和難點。盡管醫生在考慮IPV時會想到創傷,但患者其實更有可能因IPV的各種后遺癥而就診[8]。
2.1 慢性疼痛 頭疼、頸痛、背痛、腹痛等多種慢性疼痛都與IPV相關[9]。在加拿大,35%的IPV患者會出現嚴重的慢性失能性疼痛,且疼痛部位平均超過3處[10]。因為慢性疼痛,IPV患者更易出現與年齡不匹配的活動受限[11]。
2.2 消化系統疾病 很多胃腸道疾病都和心理社會因素相關,包括但不限于消化道潰瘍、腸易激綜合征、胃食管反流病、慢性便秘、慢性腹瀉等,持續壓力可能是IPV患者消化系統疾病增多的原因[12]。IPV患者會更頻繁就診于消化科,更頻繁做影像學或侵入性檢查,甚至更有可能行腹部手術治療[13]。
2.3 性傳播疾病 性傳播疾病和IPV有明顯的相關性。據舊金山的性病門診統計,11%的患者在過去1年曾遭受過IPV,24%的患者曾至少遭受過一次IPV;IPV患者的性傳播疾病發病率會增加1倍,其原因可能與IPV患者更易被脅迫發生非保護性行為相關[9]。針對美國13 928例女性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IPV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危險因素〔OR(95%CI)=3.44(1.28,9.22)〕[14]。但是,此類觀察性研究不能證實性傳播疾病與IPV之間的因果關系。
2.4 酒精和藥物濫用 各種成癮性物質和IPV相關[15]。在美國,IPV患者被診斷為藥物濫用的概率增加5倍[16]。酒精和藥物濫用是IPV的明確危險因素[17]。考慮到二者間的相關性,若患者被診斷為IPV,醫生應常規篩查酒精和藥物濫用,反之亦然。
2.5 創傷后應激障礙 IPV患者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發病率可高達85%[18]。嚴重而頻繁的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甚至心理虐待,都會加重創傷后應激障礙等癥狀;闖入性癥狀、心境和認知的負面改變、回避和喚醒狀態、職業和社交能力下降等癥狀即便在IPV結束后多年后仍會發生;創傷后應激障礙還常與抑郁、藥物濫用等情況相伴發生[19]。
2.6 抑郁與自殺 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的侵害都使IPV患者長期暴露于高壓之下,使得患者更易出現心情低落、興趣喪失、失眠、食欲改變及注意力難以集中等癥狀。遭受過IPV的婦女,其自殺傾向增加了7倍[20]。在出現慢性疼痛癥狀的遭受過IPV的婦女中,有過自殺傾向的比例高達31%[21]。與酒精和藥物濫用相似,對于IPV患者也應當進行抑郁篩查。考慮到IPV的自殺傾向,筆者建議常規使用患者健康問卷抑郁量表(PHQ-9)[22]而非兩條目患者健康問卷抑郁量表(PHQ-2)[23]作為初始篩查工具。
2.7 創傷 急診就診IPV患者中,頭面部和頸部創傷最常見,胸腹部創傷次之,四肢創傷反而相對少見[24]。與意外事件相比,IPV所致創傷多為多發傷。對于非車禍所致多發傷,醫生應提高對IPV的警惕性。另外,考慮到IPV患者長期、反復遭受毆打,故查體時應重點評估多發創傷是否處于不同愈合階段[25]。
疾病綜述一般會用似然比來評估癥狀和體征對該疾病的重要程度。但是以上提及的癥狀對于IPV來講既不特異也不靈敏,陽性似然比幾乎必然小于1,對于臨床工作沒有指導意義。與癥狀本身相比,從病史中發現的各種蹊蹺之處更有幫助。例如,IPV患者更易出現各種不相關的癥狀和體征,甚至癥征不符,很難用一元論解釋;IPV患者常會延遲就診,又或者頻繁取消就診;IPV患者常癥狀反復,對癥治療效果欠佳,部分IPV患者就診時,其家屬會全程伴隨并替患者回答各種問題。
3 識別
中國尚無相關指南指導醫生進行IPV篩查。2018年,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推薦對育齡期婦女進行IPV篩查,因為IPV的主要危害發生在孕期和產后,該推薦為B級證據[26]。不過對于非育齡期婦女,該組織認為沒有充足證據證明應常規篩查IPV。需要指出的是,國家指南是否推薦篩查某疾病,既會考慮發病率、疾病危害、干預收益等特點,也會權衡醫保特別是商業保險利益、醫療資源可及性等社會經濟因素。故指南不推薦篩查不等于不需要篩查,臨床工作中還是應個體化評估患者情況后再做抉擇。考慮到IPV的危害,建議放寬篩查指征,特別是當患者出現上文提及臨床表現時。
3.1 篩查準備 當懷疑IPV并準備開始篩查前,醫生需要確保診室內只有患者本人。多數患者只有在隱私和安全受到保護的前提下,才會提供完整病史。如患者家屬不愿意離開診室,則很考驗醫生的溝通技巧。首先,建議在問診前“設置日程”,告知患者和家屬單獨問診屬于常規流程的一部分,以降低患者家屬的警惕性;其次,可以在查體時要求患者家屬離開診室,并趁機詢問病史細節;最后,如若患者家屬仍不愿離開診室,可考慮以“復查生命體征”等借口帶患者到另一診室問診。
3.2 問診技巧 問診應從常規詢問社交史開始,如“在家庭生活如何?和家里人關系怎么樣?”進而根據患者回答選擇是否需要進一步詢問細節,如“在家里有沒有覺得不安全的時候?你的伴侶會控制或限制你做任何事情嗎?你的伴侶有沒有傷害過你或威脅要傷害你?”如果患者說出了任何IPV細節,醫生則應進一步評估患者的安全情況,如“你會擔心自己和/或孩子的安全嗎?你的伴侶最近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的變化么,比如最近失業、酗酒或吸毒?你最近遭受傷害的頻率或程度是否增加了?”
3.3 篩查量表 盡管沒有任何量表被驗證可以有效地篩查IPV,但篩查量表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首先,對于經驗尚淺的年輕醫生,篩查量表可以引領問診,避免漏掉重要的“報警”癥狀;其次,篩查量表可以標準化診療流程,利于隨訪對比及后續科研。最重要的是,高靈敏度的篩查量表能夠提高IPV的診斷率。常見的IPV篩查量表包括:(1)社會適應功能評估量表(Social-Adaptive Functioning Evaluation,SAFE)[27]。該量表包括4個問題,即“你在和伴侶相處過程中感覺安全嗎?你是否曾被伴侶威脅或傷害?你的家庭和朋友是否知道你曾被傷害?如果發生緊急事件,你有安全的去處嗎?”其最早被用于評估家庭暴力,但并非針對IPV所開發。(2)成人依戀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AAS)[28]。該量表通過5個問題來評估孕婦是否遭受過IPV,即“你是否遭受過伴侶的身體虐待?在過去的一年里,你是否被人打過、扇過、踢過或遭受過其他身體傷害?自從你懷孕以來,你是否被人打過、扇過、踢過或遭受過其他身體傷害?在過去的一年里,有沒有人強迫你發生性行為?你是否害怕你的伴侶?”任意一個問題回答為“是”,即為陽性。(3)HITS(Hurt,Insult,Threaten,and Scream)量表[29]。該量表包括5個問題,即“在過去1年內,你的伴侶多頻繁會對你進行軀體暴力?侮辱或言語攻擊?威脅要傷害你?吼叫辱罵你?強迫你進行性行為?”每個問題根據不同頻率來打分,0~4分分別代表“從不”“偶爾”“有時”“經常”“頻繁”,總分數>10分即為陽性。(4)PVS(Partner Violence Scale)量表[30]。該量表常被應用于急診以快速評估疑似的IPV。具體問題為“在過去的一年中,你是否被人打過、踢過或以其他方式傷害過?你和現在的伴侶一起生活感到安全嗎?是否有任何之前的伴侶讓你現在感到不安全?”(5)HARK(Humiliation,Afraid,Rape,and Kick)量表[31]。該量表包括4個問題,即“在過去的一年中,你被伴侶或前伴侶以任何方式羞辱或情感虐待過嗎?你害怕伴侶或前伴侶嗎?你被伴侶或前伴侶強奸過嗎?你被伴侶或前伴侶毆打過嗎?”任意一個問題回答為“是”,即為陽性。(6)STaT(Slapped,Threatened,and Throw)量表[32]。該量表通過問卷篩查IPV,從43個候選問題中選取了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下面積最大的3個問題來評估IPV。“你是否被伴侶推搡過或扇過耳光?你是否被伴侶威脅過要傷害你?你的伴侶是否會打砸破壞物品?”當評分為≥1、≥2和3時,STaT對IPV檢測的靈敏度分別為96%、89%、64%,特異度分別為75%、100%、100%。(7)女性虐待篩查工具(Woman Abuse Screening Tool,WAST)[33]。該量表共8個問題,即“你和伴侶關系緊張嗎?面對爭吵,你和伴侶是否很難解決問題?你和伴侶的爭吵是否讓你感到很沮喪?爭吵時你的伴侶會踢、打、推搡你嗎?你被伴侶的言行嚇到過嗎?你被伴侶身體虐待過嗎?你被伴侶情感虐待過嗎?你被伴侶性虐待過嗎?”WAST沒有固定的陽性閾值。
根據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2012年的系統回顧,HITS、STaT、HARK和WAST量表具有相對較好的特異度和靈敏度。常見的篩查問卷中HITS靈敏度為30%~100%,特異度為86%~99%;WAST靈敏度為47%,特異度為96%;PVS靈敏度為35%~71%,特異度為80%~94%;AAS靈敏度為93%~94%,特異度為55%~99%[34]。
筆者不推薦任何一個篩查量表,原因如下:(1)所有常見的篩查量表都是基于小樣本研究研制,無論內部真實性還是外部真實性都有待進一步證實[35];(2)所有篩查量表的高靈敏度和特異度都是在低質量研究中驗證的,并未通過高質量研究對比,即不同量表的數據好壞很可能或至少不能排除是方法學不同所致[35];(3)篩查量表均基于西方人群開發,沒有在中國人群中驗證過其篩查效能,盡管筆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嘗試意譯,也很難保證其通俗易懂;(4)當沒有官方認可的統一量表時,推薦某一量表可能并不利于醫生之間交流;(5)使用任何量表都可能“留痕”,被家屬發現都可能進一步危害患者安全;(6)尚無任何研究評估任一量表的假陽性率。
相比直接使用某一量表,理解量表背后邏輯,并將其融入問診之中或許是當下更好的選擇。綜合各種量表,其核心問題主要為:有無身體和/或心理虐待及有無安全威脅,前者對應了如何識別IPV,而后者是IPV最需要處理的問題。
4 處理
4.1 回應患者 醫生面對陽性的篩查結果,首先應該直接回應患者,目的在于展示同情和支持,向患者保證為其保密,并同時將其健康后果和IPV相聯系。例如“謝謝你告訴我這些,直面問題是戰勝IPV最好的開始;每個人都值得擁有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我會替你保密并幫助你解決這些問題;IPV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也很可能是導致你目前多種癥狀的原因。”
4.2 評估安全 評估安全的目的有兩個:首先是判斷患者今天回家是否安全。例如“你覺得今天回家安全嗎?如果不安全的話,你能到朋友或其他家人那里暫住嗎?”其次是幫助患者制定安全計劃以應對隨后可能到來的安全威脅。例如“你能提前規劃好一個逃生路線嗎?如果你在家中被侵害,哪個房間相對安全(一般衛生間或臥室為單向出口不易逃跑,客廳則相對容易逃跑,廚房有刀而相對更危險)?你能準備一個備用手機和一些錢嗎?你的重要證件在哪里,能提前偷出來或者復印一份嗎?能將這些重要物品放到房間外面的一個安全地方嗎?如果發生暴力,你能如何保護你的孩子?你有信任的朋友或家人可以幫你報警嗎?你有什么暗號可以告知你的朋友或家人你正遭受死亡威脅?”
4.3 轉診 盡管尚無明確的IPV轉診機制,但部分科室還是能從某些方面幫助患者。對于專科醫生,建議將患者轉診至全科。全科服務以人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以社區為范圍,能更便捷地做到“長期負責式照顧”。對于遭受IPV的所有患者,只要本人同意,都應轉診至心理科和/或精神科。根據《反家庭暴力法》[1],對于IPV患者,醫生有義務將患者情況匯報給居委會、街道辦事處、婦聯等。相關機構對既往IPV應做好問題調查和糾紛排解,對可能發生的IPV應做好備案和預防,對正在發生的IPV應及時制止并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
4.4 病歷記錄 為避免家屬復印病歷,一定要囑咐患者不要簽署家屬授權書,避免家屬看到病歷后進一步傷害患者。翔實的病歷記錄能夠在法律上保護醫患雙方。如發生創傷,醫生應記錄受傷機制、詳細描述傷情,必要時使用“身體地圖”來標志所有受傷部位。如果患者同意,也可以將傷情部位拍照后上傳至病歷系統。對于抑郁、自殺、創傷后應激障礙、物質濫用相關篩查表格,應復印后隨病歷留存。病歷中應記錄已和患者討論了安全計劃,以避免糾紛。
5 全科醫學在IPV診療中的作用
5.1 識別方面 IPV發病隱蔽,所涉及的癥狀往往既不特異,也不局限于單一系統。除急性創傷外很難在首診時被識別。全科醫生應該利用全科醫學的持續性和綜合性優勢,從病史查體及就診模式的蹊蹺之處尋找可能的IPV線索。考慮到IPV的高發病率及嚴重危害,全科醫生應降低篩查IPV的閾值。
5.2 預防方面 IPV與很多疾病互為因果。全科醫學強調對于疾病的預防,在幫助患者管理酗酒、藥物濫用、焦慮與抑郁等疾病時,其實也是在做IPV的一級預防,反之亦然。另外,全科醫生可以向家庭的每個成員提供醫療照顧,如能提前發現IPV的危險因素,也能防微杜漸,將其控制在萌芽階段。
5.3 處理方面 全科醫生簽約患者后會長期同患者打交道,這種類似醫療管家的特點會增加患者的信任,是幫助IPV患者的最佳角色。IPV往往需要長時間的管理,以幫助患者遠離威脅,逐漸走出心理陰影。而全科醫學強調對患者“長期負責式照顧”,更利于引領IPV患者戰勝暴力。全科醫生還應做到醫療聯系員的角色,充分利用可及的醫療資源,包括心理科、精神科、理療科等資源,并在必要時協調利用社區內外其他資源共同幫助患者。
5.4 法律方面 全科醫生應注意保護患者隱私,做到“一對一”就診。病歷既要記錄翔實,更要謹慎保管,在保障患者利益的同時,避免激化矛盾。在面對正在發生的IPV及患者有可能生命受到威脅時,應鼓勵患者報警,尋求法律援助。
綜上,IPV發病率高、危害大,在臨床中不易被識別,且在中國尚無規范處理方法。全科醫生應當了解IPV常見臨床表現,善用篩查量表并適當降低篩查閾值以更好地識別IPV。對已知的IPV,全科醫生應評估患者安全,及時轉診,并幫助患者尋求法律援助。我國應盡快制定官方診療指南,以明確醫務工作者在IPV中的職責,從而更好地預防和制止IPV。
作者貢獻:趙梓翔、肖婧負責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撰寫論文;豐艷負責文章的修訂,并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進行批判性審閱;姜岳負責文章質量的控制及審校,并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