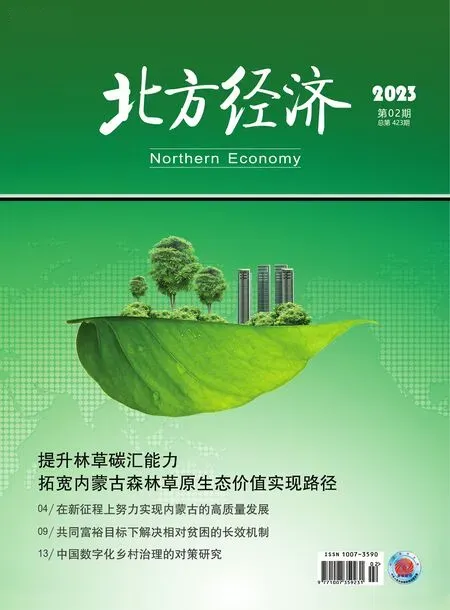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的對策研究
張 捷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方面,數字化鄉村治理具有標志性意義。在中辦、國辦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中,將數字鄉村作為數字中國建設的重大內容,對創新鄉村治理方式、提高鄉村善治水平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構建鄉村數字治理新體系。在新時代新征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出現了較多新情況新問題,值得我們深入反思。破解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既需要結合國內數字化鄉村治理的一般模式,也需要圍繞治理思路、價值取向、具體機理等主要內容,開展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的思路分析,并提出針對性的對策。
一、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科學內涵、新要求
2022年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中,總書記指出:“要用好現代信息技術,創新鄉村治理方式,提高鄉村善治水平。”總書記的一席話既道出了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科學內涵,也為中國的治理對策提出了具體的新要求。
從組織架構看,以保障和改善農村民生為優先方向,圍繞讓廣大農民得到更好的組織引領、社會服務、民主參與,加快構建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
從微觀法治看,深入推進平安鄉村建設,嚴厲打擊把持基層政權、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侵吞集體資產等違法犯罪活動,依法制止利用宗教、邪教干預農村公共事務。
二、當前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的反思
(一)數字化鄉村治理的一般性困境仍待攻破
一方面是鄉村政府財力能否承受所需資金,另一方面是服務對象和基層工作人員的思維、身心是否存在“脫節”隱憂。在廣袤的南方鄉村,具備率先開展數字化鄉村治理的試點基礎,而在西北等偏僻鄉村,則需要選擇“開源節流”的方式方法,減少鄉村政府的巨額財政負擔。由于西北偏僻鄉村的“青年才俊”外流嚴重(根據人口七普數據,西北偏僻鄉村15-59歲人口比重低于南方鄉村至少4個百分點),剩下的較多文化層次偏低群體無法掌控智能手機等信息技術。從治理成果共享看,數字化鄉村治理交互平臺使用門檻較高,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在短時間內,基本應用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二)數字化鄉村治理“技術神話論”仍待澄清
從數字化鄉村治理實踐看,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在“三農”中的廣泛應用,驅動鄉村治理產生系統性變革,促進公共服務效能較快提升。以其為代表的技術手段,也使得傳統型鄉村治理與社會生態結構的不協調越來越明顯。因此,數字化鄉村治理需要胸懷“國之大者”,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引領,充分體現人文精神、生態文明,要求黨員干部解放思想,探索新路子。
(三)數字化鄉村治理內卷傾向有待糾偏
近年來,各級政府積極推進“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并把較多行政工作下放至社區。據悉,社區干部反映較多的是,事事留痕、追求“完美”的治理細節帶來新的負擔。目前,透視民政、公安、勞動保障、社會事業等業務部門的數據來源采編,仍然沒有完全實現信息共享,多頭管理的狀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個中緣由,是因為缺乏開放、共享的數字化新思維,在運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時,仍然局限于本轄區、本部門的團體利益,導致數據庫建設質量下降。因此,需要緩解消除轄區、部門之間的數據“拖延癥”,自下而上建設統一的鄉村治理大平臺。
(四)數字化鄉村治理的安全風險有待預警
在鄉村治理實踐中,中國的數字技術發展得到催化,然而國內相關法律法規制度的制訂相對滯后。比如說,部分互聯網龍頭公司在鄉村擁有業務基站,具有較強的話語權,數據保管應用對公共安全具有隱患,其中農民個人信息泄露被騙現象屢禁不止,人身、財產安全面臨許多困擾。因此,在外部,應該牢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將鄉村治理的數據安全、信息保護擺在重要位置。在內部,需要構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督機制,完善鄉村治理數據庫的技術預警措施。區別化設置權限,確保數據存儲、使用、維護的安全性。
三、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的思路分析
(一)國內數字化鄉村治理的一般模式
總體而言,國內數字化鄉村治理一般模式主要是:利用數字信息技術,重構鄉村治理的基礎設施與技術規則,提高鄉村行政機構辦事效能,帶動鄉村的數字經濟發展,推動“三農”全面數字化。其中比較成功的一般模式有:“福建模式”“浙江模式”“湖北模式”“貴州模式”等。
習近平同志2000年任福建省長時,率先提出“ 數字福建”;2003年,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時,提出“數字浙江”,二者邏輯一脈相承。目前,浙江省依托鄉村治理數字在線,完成了省、市、縣、鄉、村五級機構的體系搭建,探索形成了較多數字特色鄉村,其中,“鎮海模式”“村情通”等是典型代表。
湖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依托數字智慧政府建設,深度賦能數字化鄉村治理工程。目前,湖北恩施的“騰訊公益·五社聯動·家園助力站”公益項目以“黨建引領、五社聯動、共建共治”為目標,將鄉村基層治理由“村里事”變成“自己事”,由“上級安排”轉為“激勵引導”,由“要我參與”變成“我要參與”。
貴州模式主要是依托大數據中心,創造性地運用大數據新思維,以大數據產業發展帶動數字經濟發展。作為貴陽市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示范縣(開陽縣),將縣內農村垃圾收集點、垃圾收運車共同接入“貴州數字鄉村”數字化監測平臺,實時監控農村生活垃圾收運、環衛設施運行情況。
(二)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體系
1.治理框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總要求下,具體內容是,在生態上保育美麗鄉村環境,在生產上促進美麗鄉村經濟,在生活上引領美麗鄉村生活,在風貌上塑造美麗鄉村特色。
2.價值取向。一是統籌謀劃、有序推進,把握鄉村治理與數字經濟、信息技術發展融合新趨勢,探索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新模式。二是數據驅動、資源共享,搭建諸多新基建平臺,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三是創新引領、應用導向,加強應用集成試點示范,提升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四是多方參與、合力共建,完善鄉村數字化協同治理機制,形成多元參與的科學共治格局。
四、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的對策建議
(一)從實踐上理解數字化鄉村治理的新內涵
在數字經濟快速擴圍的今天,鄉村治理面臨的外部環境復雜性持續增加,我們需要通過技術賦能,提升治理的風險識別能力、資源整合等能力。圍繞以服務“三農”為中心,以村民需求為指南,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研究出臺“以村民為中心”和“善治”的數字化鄉村治理細則。借鑒“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的相關模式經驗,依托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的物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改進,優化鄉村政府條線部門的職能業務,推進多元化命運共同體治理,讓鄉民少跑路、數據多跑路,助力數字治理實現數字化鄉村治理現代化。
由于數字化鄉村治理的技術前沿存在不確定性,數字安全存在較大風險,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數字紅利與數字貧困并存。因此,亟待順應數字化鄉村發展、數字化技術應用的迭代升級趨勢,推動鄉村治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融合數字化管理、新經濟、新基建等內容,合力推動新一輪鄉村治理由數字化管理向全周期數字化治理變革。特別要運用好區塊鏈技術,推動實現數據的交互分享,構建公共服務網絡,提高公共服務的供需匹配度,并平衡多方利益,讓其為鄉村治理提供新形態和新模式。
(二)加快數字化綜合創新平臺等新基建建設應用
充分加大頂層設計和高位協調促進力度,推進縱向統籌多層次平臺建設,橫向打通各業務部門的數字壁壘。錨定數字化綜合創新平臺等新基建建設需求,推進數字化可視大平臺、數字專網和數字智能物聯網配套建設。以數字化綜合創新平臺等新基建建設為契機,重點建設連接鄉村與鄉民的前端、集成數據的中端,以及掌管算存的后端,驅動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其中,應當大力推進中端和底座的數字化鄉村建設,推動構建跨部門、跨地域、跨層級、跨業務、跨系統的數據融合、職能融合和監管融合。
鎖定數字化鄉村與城市共同體的成長性場景應用需求,在鄉鎮板塊,內蒙古引入各類企業、村民參與數字化鄉村多元共治,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綜合協同效應。跟蹤數字化鄉村治理的最新動態,提供高效的數字化綜合創新平臺等新基建一站式應用服務。借鑒浙江的一般模式相關經驗,區別化完善中國數字化鄉村治理平臺的場景應用職能和機制。以新基建促進數字鄉村治理職能轉變,以數字服務提升鄉村治理場景效能,有效推動職能部門、條線之間的場景應用結果共享、風險共擔。
(三)推進新方位、系統化的鄉村政府職能流程優化
利用數字技術推動鄉村政府職能流程優化。借鑒國內數字化鄉村治理一般模式的相關經驗,做實中國鄉村“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的治理基礎,通過鄉村政府內部職能流程的創新優化,推動政府和社會多維協作。釋放中國建設“數實融合”的政策紅利,整合鄉村政府行政審批等多頭緒、反復性流程,改善行政響應的低效率流程,取消相應的無效流程。完善鄉村政府“三定方案”,梳理整合鄉村政府部門的核心業務,避免越位、缺位和錯位。
推動契合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鄉村產業經濟體系重構。推動鄉村產業經濟體系重構,需要融入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大局,實施數字鄉村富民戰略,引培壯大鄉村數字經濟發展規模,以數據鏈帶動提升鄉村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建立村民生產與消費平臺的銜接互動機制,促進貧困村民與數字鄉村有機融合。發揮“互聯網+”“物聯網+”特色產業扶貧的杠桿作用,持續拓寬村民增收渠道,科學有效地保障改善村民生產生活。
(四)因地制宜開展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績效考核
健全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績效評價體系。將社會公民、團體、單位等主體,納入到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績效評價主體中。通過邀請省內甚至國內知名績效管理專家團隊,避免傳統績效考核的“行政化”色彩。統籌考慮多個維度,對納入績效考核的指標,開展充分的必要性科學研究。通過問卷調查、現場采訪、意見箱等方式方法,了解村民對數字化鄉村治理服務的意見建議。創建完善數據管理系統、績效過程數據庫,研發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績效分析軟件。
強化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績效考核結果運用。由績效考核委員會圍繞數字化鄉村治理有關部門業績,形成績效考核綜合報告,明確今后努力方向。歸納整理考核中反映出來的數字化鄉村治理突出問題,納入相關部門下一年度工作目標,督促責任部門落實整改周期、細化整改措施、確保整改實效。圍繞數字化鄉村治理的節能減排、社會穩定、安全生產等工作內容,對于發生嚴重失職瀆職的領導干部,嚴格開展誡勉談話、嚴肅懲戒、社會公示,必要時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