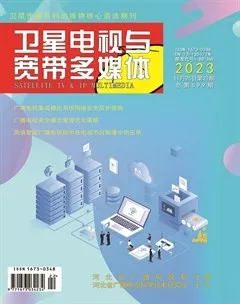短視頻新聞評論語態轉變的原因及方向分析
肖明松
【摘要】新聞評論節目的播出平臺從最早的廣播電視到今日的移動互聯網平臺,歷經了從播評論、說評論到聊評論的轉變,其體現了評論主體的身份定位從權威代言的媒體形象到個人形象;從評論節目到評論視頻;評論節目的表現方式從單向傳播到多方互動的轉變。而據此,專業媒體內容的生產者也應轉變傳播姿態,以評論主體為中心,打造適合媒體評論的形象,并堅持內容為王的基本原則,在短視頻平臺下生產高質量的新聞評論內容。本文從我國早期的廣播電視新聞評論節目開始分析,探討評論節目語態所經歷的變化及其原因并對未來新聞評論節目應做出的發展和改變提出構想和建議。
【關鍵詞】短視頻;新聞評論;傳統媒體;新聞傳播
中圖分類號:G241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 ?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3.22.050
所謂語態,即“傳播者表達的態度、形式和內容以及其背后所體現出的傳播者對受眾的姿態”[1]。所以評論節目的內容選取、主播形象、表達狀態都屬于語態的研究內容。本文通過分析短視頻新聞評論節目語態的轉變,探討其原因,并推斷其未來語態的轉變方向。
1. 新聞評論語態的嬗變
“傳統新聞評論節目”是一個與“短視頻新聞評論”相對應的概念,在這里特指在廣播電視平臺中播放的新聞評論節目。評論節目的主要內容是由評論主體口中說出的新聞評論,評論表達主體的語態決定了整個節目的語態樣式。所謂“評論主體”有時由出鏡的播音員或主持人直接承擔,有時由節目特邀的評論員承擔。
1.1 權威教化:“播”評論
播評論,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1950年4月10日開播的《新聞與報紙摘要》為代表的新聞節目中的評論板塊,主要是播音員與主持人在節目中將評論文章轉化為有聲語言播出,“電臺自己寫作的評論很少見,但轉發播送報紙的言論是大量的……評論播音認真地說,并不是指地道的廣播評論,而是指的報刊評論[2]。”雖然有著播音員有聲語言技巧的加持,但是文字稿件創作時并不考慮到廣播的播出,所以廣播評論的風格就不可能是口語化、個性化的表達。旗幟鮮明、情感充沛的語言風格,教育人、鼓舞人的節目目的成為了評論節目的主要語態。整個節目“是國家級媒體的新聞發聲,是權威的、端莊的、傳統的”[3],評論節目代表著權威、正確,與受眾拉開了距離,形成了一種教育與被教育的關系。
1.2 親民引導:“說”評論
“說”評論階段,以1993年《東方時空》開播為標志。《東方時空》雖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新聞評論節目,但是其所提倡的“平等交流”理念對后續評論節目起到了重要影響。廣播電視節目語態逐漸打造一種平等與受眾交流的形象。主持人口語化表達的比重加強,聊天式主持風格凸顯,不再嚴格傳遞代表權威形象的評論觀點,而是以個人的身份出現,“找到平民化的視角和切入點,拉近和目標受眾之間的距離,避免說教式地傳播意見性信息[4]。”主持人雖然依舊是權威的形象代表,但已經不再明顯“教育”受眾,而是委婉“引導”受眾,以平等的身份傳遞權威的觀點。新聞評論節目的語態逐漸發展,誕生了“對話”評論節目與“談話”評論節目。如《時事開講》,主持人不再以評論人員的身份出現,而是以節目節奏的把控人形象出現,引導評論人員說出觀點的節目形態。
2008年央視新聞頻道播出的《新聞1+1》則從“對話”變化為了“談話”形態,即兩位主持人,或一名主持人與一名評論員共同承擔著把控節目進程與傳遞評論內容的功能,二人一起“討論”新聞事件。這種節目形態使得評論節目從“一錘定音”發展至“思辨探討”,讓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悖的評論觀點在公共平臺上同時播出,而觀眾究竟應該“接受”或認可哪一種觀點?這個選擇權下放給了節目觀眾,也給了觀眾一種“平等交流”之感。
1.3 平等討論:“聊”評論
自2017年后,短視頻平臺迅速發展,以抖音、快手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平臺普及率激增,而短視頻平臺的新聞評論呈現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短視頻平臺的新聞評論不以“節目”為基本單位,而是以單獨成立的短視頻作為最終呈現形式,只要該視頻內容以新聞評論為主,或者其短視頻的制作者、上傳者稱自己為“節目”,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屬于我們對于“短視頻新聞評論”的討論范圍。
短視頻平臺下,新聞評論的表達狀態轉變為平等討論,評論人員不再是權威的代表:短視頻新聞評論人員的儀表多樣,不一定是俊男靚女;口音南腔北調,不一定需要受過專業的語言訓練。與傳統媒體時代下,“凡是報上寫的,凡是電臺、電視臺播的,就是官方的意見,就具有絕對的權威性”[5]不同,短視頻平臺中信息本身不代表任何權威,只是給評論者一個展示的空間,而不存在對于評論者自身身份的任何形式的“認可”,新聞評論節目從權威聲音的表達工具變成了一個平等表達的平臺。
2. 短視頻新聞評論語態轉變的原因
2.1 評論主體身份定位:媒體形象到個人形象
廣播電視平臺與以“去中心化”為特征的社交媒體平臺相比,其地位和功能都有著根本的差異。廣播電視平臺在地位上屬于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中的重要一環,“從根本上說,我國的廣播電視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社會主義宣傳文化事業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6]。廣播電視媒體的根本屬性一直以來都是新聞屬性,而我國的新聞工作者從身份上便與其他行業從業者有著屬性的區別,新聞行業具有著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橋梁作用,媒體平臺具有著黨和國家的“喉舌”的特殊身份,其本身就帶有著“權威”色彩。
播音員與主持人代表著媒體平臺的形象與身份,而媒體平臺又代表著權威聲音,其身份地位注定不能與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受眾群體真正“平等”。
短視頻平臺自身有“去中心化”的性質,短視頻平臺中沒有傳統意義上占據絕對主動地位的傳播者和被動地位的接收者。“Web2.0時代環境下社交媒體這種新興的信息資源創造和共享模式即為用戶生成內容[7],”這種生產模式使得“用戶也可創造內容”變成了“創造內容者都是用戶”。這種祛魅性使媒體機構的權威屬性被消解。同時,短視頻新聞評論的主體并不全是專業的媒體機構或媒體從業人員,無論何種身份,只要對于新聞事件想要發聲與表達,都可以在短視頻平臺制作新聞評論視頻,完全以自己的個人形象發聲。專業媒體和普通受眾的定位變成了“大用戶”和“小用戶”的關系,從根本性質上達到了平等。二者間的區別不再是能否發聲,而只是發聲影響力大小的區別。甚至有些專業媒體在短視頻平臺的影響力還不如某些普通用戶的大。傳統媒體的短視頻平臺賬號與其他非專業媒體的賬號以及所有普通用戶身份的平等化,也為短視頻新聞評論的語態平民化轉變提供了可能性。
2.2 評論節目平臺特性:評論節目到評論視頻
廣播電視節目,指的是“廣播電視機構播出內容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播出形式和構成單元”,“有固定的播出時間和時長、內容主體和形式風格統一、定期播出的節目單元[8]。”傳統媒體的新聞評論節目受固定時長限制,有最基本的節目制作標準和主題限制,播出需要具備相關部門所發布的播出資格。一檔新聞節目從立項到播出需要經過復雜的準備過程。
而與傳統媒體平臺的“節目”概念不同,短視頻平臺新聞評論以賬號或賬號矩陣為單位,短視頻的“節目”沒有固定的時長要求、節目類型,沒有統一的節目播出資質和制作標準。從媒介生產角度來看,短視頻平臺的新聞評論視頻制作沒有任何固定要求,其制作門檻低使得任何人只要具備媒介接觸能力,也就具備了媒介信息生產能力;從媒介內容制作來看,基本不存在任何評論內容知識、質量的要求;從媒介接收來看,沒有任何的時間、空間要求,有一臺手機隨時隨地就可以觀看評論視頻。
目前,在短視頻平臺上除了對于新聞發布、采訪有一定要求之外,對于表達評論人觀點的評論視頻沒有發布限制。短視頻平臺的賬號不需要明確的節目定位,今天以時政新聞為主題,明天可以以娛樂新聞為主題,只要能夠拉近與受眾的情感距離,獲得受眾關注,就可以根據一些熱點內容進行內容制作。短視頻平臺的節目內容沒有時長限制和固定單元,只有數十秒鐘的一段視頻內容也可以作為內容的承載主體。
傳統媒體節目制作成本高,流程復雜,體量大,要求制作者來服務節目;短視頻平臺視頻制作成本低,流程簡單,體量小,整檔節目(或稱視頻)可以完全圍繞評論主體來服務。由于節目不受題材、時長等的限制,評論主體的語言風格靈活多變,不受拘束,時而活潑時而嚴肅,時而長篇大論時而簡明扼要。評論主體的個性與個人形象在短視頻中充分展現,不是主持人為節目服務,而是評論視頻成為了主持人意見表達的平臺,短視頻平臺的新聞評論也由此呈現出個性化、平民化的語態。
2.3 評論節目表現方式:單向傳播到多方互動
傳統媒體時代,新聞評論節目屬于單向傳播,新聞評論節目在傳播活動中占據優勢地位,觀眾的反饋渠道主要通過現場連線、事后反饋、選擇頻道來達成,其反饋有一定門檻,且滯后性較強:評論節目的時長決定了現場連線在節目的占比較低,即便是《馬后炮》等以連線觀眾或播出觀眾留言為特色的電視節目,其給予觀眾的表達時間也不及節目的五分之一;事后反饋指在節目播出之后,通過寫信、電話、留言等方式向媒體機構表達意見,這種反饋方式并非公開傳播,也無法及時反饋意見、表達觀點;觀眾表達自己觀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切換頻道來觀看自己喜歡的節目,也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短視頻平臺下,其“社交”屬性凸顯,評論內容生產主體的身份是“用戶”,而普通的觀眾其身份本質也是“用戶”,二者在短視頻平臺所提供的“評論區”“論壇”等場域下,進行平等、及時的交流。在短視頻平臺直播時,也有在互聯網接收終端(通常為移動通信設備)的屏幕中占比不小的公共屏幕,如果受眾的負面反饋過多,也會直接影響到短視頻平臺直播的效果。這種觀眾輿論在節目表現中占據重要地位,受眾的轉發、點贊、舉報、拉黑等行為都會影響新聞評論節目,受眾選擇權上升,地位更加重要。
新聞評論也脫離開高臺教化、我播你看的高姿態,轉向更加平等的姿態。一些原有的專業媒體的數字媒體賬號也開始轉變語態來獲得用戶喜愛。比如央視《新聞聯播》的主播團隊,在短視頻平臺打造的新聞評論《主播說聯播》,“主持人轉變播報方式,建立人格化形象;轉變播報語態,采用幽默化解讀;轉變播報語氣,剛柔并濟表態度[9]。”
3. 新媒體語境下評論節目的轉變策略
3.1 以評論主體為中心:打造優質評論主持人
短視頻平臺的新聞評論節目呈現出以評論主體為核心的發展趨勢,從主持人為節目服務轉化為節目為主持人服務。在傳統媒體時代,主持人的形象也是節目的“門面”,評論節目注重主持人和評論員的表達是一以貫之的。在短視頻平臺,想要做好新聞評論,就必須更加重視主持人或評論員的個人塑造。傳統媒體時代,新聞節目主持人的選擇具備嚴格的標準,主要以播音主持工作或新聞工作的從業人員來擔當,其語言表達規范,相關知識豐富,但這些優點卻在短視頻平臺成為了與受眾產生隔閡的原因。縱觀我國廣播電視發展史,主持人的語態歷經多次變化,其主要原則便是“實踐為師”,什么表達狀態適合節目播出的實際需求,播音員主持人就需要轉變自身表達語態來適應實踐需求。評論主持人應該在保持傳統時代為人所重視的語音標準、專業態度、權威身份以及語言表達能力等等特征的同時,運用數字媒體平臺運營技巧,打造個人親民形象,拉近與受眾間的情感距離,培養出短視頻時代的新聞嗅覺和新聞敏感度,并用專業的有聲語言工作者的能力制作出上接天線,下接地氣的新聞評論節目。簡而言之,在短視頻時代,專業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員更應轉變自身表達語態,以新聞工作的專業素養輔以平民化的表達語態,以適應短視頻新聞評論節目的需求。
3.2 以優質內容為守則:打造優質內容矩陣
與傳統媒體平臺事業性體制相比,短視頻平臺全民創作的性質決定了大部分的媒介內容都是免費的,只有部分的內容生產者能夠盈利。而制作優質內容需要成本,時間、人工等的消耗在短視頻內容生產初期未必能夠獲得相應的回報,缺乏固定的收入渠道也會使得有生產優質內容能力的創作者入不敷出,終止創作。同時,短視頻內容生產門檻的降低使得大量低質量短視頻井噴式出現,并通過賬號矩陣,借助平臺推送算法機制分發并盈利,形成一種“劣幣驅逐良幣”之勢。
同時,我們也應意識到去中心化的特質雖然使得傳播者與受眾的絕對界限消弭,但是平臺上不進行內容生產,專門的“看客”仍然占比最高,專業意見領袖和專業媒介內容生產主體仍然是短視頻平臺中的主要媒介生產者:絕對意義的傳播者與受眾關系已經不再,但相對的受眾與傳播者的區別依然存在,“受眾的媒介的使用需求可以歸結為五大類:認知需求、情感需求、個人整合需求信息、社會整合需求、疏解壓力需求[10]。”在短視頻平臺下,受眾使用媒介依然是為滿足其特定需求,而優質的媒介內容依舊具備強勁的競爭力,“內容為王”的傳統觀念永不過時。如何優化視頻流量分發與盈利機制,令優質內容生產者得到應有的回報,這無疑是媒介平臺亟需解決的難題。不論分發機制如何改變,優質的內容總是會提供受眾所需的價值,同時優質內容的生產也是專業媒體的核心價值所在。專業媒體應當利用自身優勢,多平臺、多賬號布局,在多個社交平臺上發布內容,充分利用圖文平臺、長視頻、短視頻平臺以及其他社交平臺的媒介特點持續輸出有特色、高質量的媒介內容,綜合打造自身媒體的IP形象,以求在數字媒體時代扎穩腳步,實現媒體價值。
4. 結束語
媒體是社會的守望者,這是媒體行業公認的常識,也決定了媒體的內容生產與分發形態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在記錄社會變化的同時影響著社會的變化。短視頻平臺的火爆體現出了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其對社會的深刻影響,媒體工作者更應該在這種環境下把握機遇,處理好專業內容和平民表達的語態平衡,轉換傳播語態,在新的媒介內容分發平臺中創作有溫度、有態度、有熱度的新聞評論節目,發揮好媒體應具備的社會守望、輿論監督、信息提供功能。
參考文獻:
[1]彭蘭.網絡傳播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265-266.
[2]陳剛.談談評論播音的基本要求和語言表達特點[J].現代傳播.1980(01):39-43.
[3]劉博偉.淺析如何判斷新聞節目的播音主持語態[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9(08):158-159.
[4]李敏,譚天.電視新聞評論的形態創新和語態創新[J].視聽界,2011(04):66-70.
[5]劉學義.話語權轉移[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46-47.
[6]田惠愛.深化對廣播電視政治屬性和經濟屬性的認識[J].前進,2001(10):32-35.
[7]丹尼斯麥奎爾.受眾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42-54.
[8]陸曄.當代廣播電視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271-279.
[9]于小菲.新媒體背景下時政新聞播音在風格上的創新——以央視新媒體欄目《主播說聯播》為例[J].西部廣播電視,2019(20):172-173.
[10]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68-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