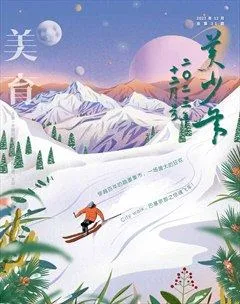大唐最美勞動畫卷——《搗練圖》
行橋鑫
1.搗練活動通常由婦女在秋季天氣轉涼時進行,“搗練”便逐漸被賦予了秋思閨怨的象征意義。
2.畫中仕女多梳鬢云高聳的圓形發髻,這種發型在隋唐時期的貴族婦女中十分常見。
3.《搗練圖》中正在生火的仕女手執團扇,扇面繪有蘆汀野鴨圖,你發現了嗎?
4.炭火盆邊插著一雙火筷子,可用來翻動炭塊,讓炭火燒得更旺。
5.正在織繡的女子身著白衣,衣袖上的白色有些泛黃,頗具古舊的韻味。
6.唐代女性喜用花鈿裝飾眉間,畫中的仕女便在眉心貼有藍、綠兩色,呈三瓣狀的花鈿。
7.《搗練圖》右上角有一行小字“天水摹張萱搗練圖”。這些字是金朝皇帝完顏璟寫的,其中“天水”指的就是宋徽宗。
夜深了,月亮掛上樹梢,孩子們已經進入甜蜜的夢鄉。此時,家家戶戶的主婦們再次忙碌起來。借著月光,她們將布料放在砧板上,用木杵不停地敲打,每敲打一下,對遠在邊關征戰的丈夫的思念就更深一分。唐代詩人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描述了這種孤寂的“搗衣”場景:“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我們在感嘆古代女性勤勞的同時,不禁產生了深深的好奇:何為“搗衣”?為何要在夜晚搗衣?想要解開這些謎團,我們可以從一幅畫談起。
何為“搗衣”?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有一幅描繪我國唐代仕女搗衣場景的珍貴畫作——《搗練圖》。此畫原作早已遺失,作者是唐代仕女畫大師張萱。這幅摹本出自北宋末年極具藝術天賦的宋徽宗趙佶,其重要程度自然不言而喻。
《搗練圖》中共繪制了12個唐代宮廷仕女形象,她們分為三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搗衣工序。按照欣賞古畫的順序,將畫卷從右向左徐徐展開,畫面展示的依次是搗練、織繡、熨燙的場景。
搗練組由四位仕女構成。她們圍著一座枯黃色的長方體石砧,上面放著用細繩捆綁起來的白色布料——生練。所謂“練”是一種生絲織品,因為質地堅硬且顏色不夠潔白,所以在縫制衣物之前,必須先用沸水煮泡,再將布料置于石砧之上用木杵反復敲打,才能使布料變得平滑、柔軟。
搗練是個力氣活。四位仕女被分為兩組,輪流搗衣。她們圍繞著石砧兩兩相對,每人手中都持有一個中間細、兩頭粗的木杵。站在中間的兩位仕女此時微弓著背,正舉著木杵欲向下搗去;另外兩位仕女則是持杵靜立。更為生動的是,左側穿紅衣藍裙的仕女把木杵靠在胸前,一只手正在給另一只手挽袖,顯然在為下次搗練做準備,這一細節讓整個畫面變得生動起來。
織繡與熨燙,姿態的對比之美
畫卷中間描繪的是織繡的場景。兩位仕女以中間的線軸為中心,一個坐于左側的凳子上,面向觀者;一個坐于右側的地毯之上,背對觀者。面向觀者的仕女一只腳踩在凳子上,手捏繡花針,認真地縫補著置于腿上的白練;背對觀者的仕女正從線軸上拉扯絲線,定要把纏在手上的絲線梳理清楚。看到這里,大家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剛剛搗好的布料就能直接拿來縫制了嗎?事實上,搗練的正確步驟應該是先搗練、熨燙,最后才是縫制,但在《搗練圖》中,這種順序被打亂了。關于如此安排場景的理由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畫家很可能參考了北魏時期壁畫的構圖方式——組合畫式,將最具感染力的內容放在畫面中央。所以在觀看這幅畫作時,大家不妨采取從卷軸兩邊向中間觀看的方式,或許會獲得不一樣的視覺體驗。
畫卷左側描繪的是熨燙環節。熨燙之前先要生炭火。身穿藍衣、蹲坐在地上的年輕仕女,正在為熨燙組準備炭火。她手執團扇,為炭火添風助燃。炭火燒得太旺,她不得不轉過臉去,以手掩面遮擋熱氣。在她左側站立的四位仕女也呈兩兩相對之勢。兩邊的兩位仕女身體微微后仰,將長長的布料展開,而不繃緊。中間的兩位仕女,一人手握盛有炭火的熨斗緩緩移動,將布料燙平,另一個年輕的仕女則配合著她的動作將白練料理平整。白練下面還有一個可愛俏皮的粉衣小女孩,與辛苦勞動的仕女形成鮮明的對比,為畫面增添了一抹輕松活潑的色彩。
服飾與發梳,唐人的風韻之美
《搗練圖》除了向我們展示了古代仕女搗練的過程,仕女們的服飾紋樣與發型裝束也同樣值得我們細細欣賞。唐代仕女的服飾主要有裙、衫、襦等,她們將短衫的下襟掩在束胸長裙之內,外搭半透明的披肩,使整個人物呈現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服飾上的圖案紋樣,可謂豐富多彩,各具特色。
在搗練組中,最右側身穿綠色長裙的仕女,其披肩上的紋樣是以淺藍色構成的六邊形,內部以紅色、綠色填充,整體形狀類似龜背,因此被稱作“龜背瑞花”;在織繡組中,坐于翡翠色毯子上正在理線的仕女,身著大紅色披肩,靛青色枝蔓纏繞其上,枝蔓內填以粉色蓮花,這種紋樣線條柔美,色彩濃麗,被稱為“卷草蓮花”;在熨燙組中,左側身穿藍色長裙的仕女,短襦以粉色為底,上織邊線以兩片葉子構成的菱格,內部填充呈放射狀對稱的瑞花,紋樣由此得名“菱格瑞花”,體現一種吉祥、莊嚴的格調;蹲在一旁生火的仕女,其所穿服飾的紋樣同樣頗具特色,綠色長裙上以暈色圓環為骨架,中間填充如意瑞花,其形似雪花,這種紋樣稱為“團窠瑞花”。圖中服飾紋樣搭配多變,充分體現了唐代服飾端莊、明艷的特點。
與紋樣相配的還有仕女們的發型裝束。《搗練圖》中的仕女們束發時多用梳子裝飾其上,每把梳子的形狀都略有不同,有的裝飾于發鬢前,與額間的花鈿相互搭配,有的裝飾于發髻之后,這也是唐代仕女較為流行的一種裝扮。
月下搗衣聲,古人的智慧
“搗練”這一活動最早出現在詩文之中,后來逐漸成為繪畫的題材。如漢代班婕妤在《搗素賦》中云:“于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飚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又如魏晉時期曹毗在《夜聽搗衣》中云:“纖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砧。”又如南朝詩人謝惠連在《搗衣》詩中云:“檐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至唐代有王建的《搗衣曲》:“月明中庭搗衣石,掩帷下堂來搗帛。”甚至大詩人李白也在《子夜吳歌》中寫道:“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在這些詩句中,搗衣活動總是在夜晚進行,搗衣的婦人們也常常與月亮相伴,帶有幾絲凄清之感。
原來,經過搗練后的布料很容易變得松散,所以搗練需要在特定的環境下進行。據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記載:“凡布縷緊則堅,緩則脆……石不發燒,則縷緊不松泛。”所以搗練一般不在溫度過高的時候進行,需等到夜晚溫度降低或者在溫度較低的季節,才能開展搗練活動,只有這樣,搗練出來的織物才能更加緊實、耐用。
在古人的世界里,搗練不僅是一種勞作活動,它還被寫進了詩文之中,繪入了畫卷之上,寄托了無數人的浪漫遐想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