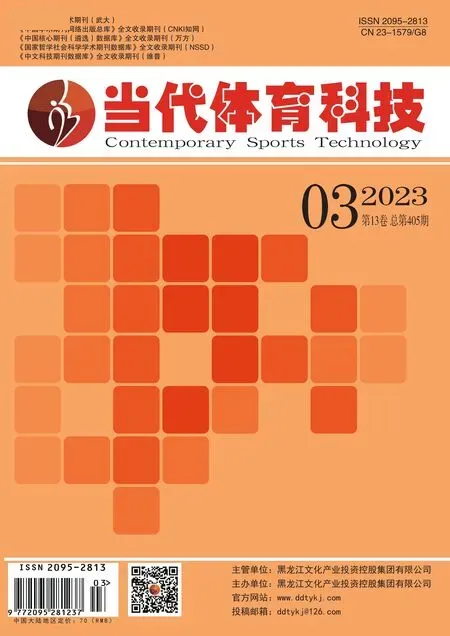競技速度攀巖運動疲勞時序性研究
肖隨龍 李宏偉 張蕾
(1.江西應用技術職業學院;2.贛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江西贛州 341000)
攀巖運動需要調動全身絕大部分肌肉,在受力點極小的情況下克服自身重力向上移動,而運動疲勞是影響速度攀巖成績的重要因素[1]。生物反饋技術以其實時監控、無創、遙測的優勢,在運動醫學的疲勞程度監測工作中得到廣泛應用[2]。因實驗需要運動員在實驗過程中達到疲勞指標,攀爬速度攀巖15m 標準賽道一次不一定能達到指標要求,反復攀爬過程中落地到再次攀爬,運動員生理機能處于恢復休息狀態,因此,該研究采用高強度間歇(HIIT)運動方式,組間休息時間為每次攀爬到最高點至第二次攀爬起始點之間。使用生物反饋技術監測競技速度攀巖中運動員的心率變異性(HRV)、表面肌電(sEMG)兩項指標,根據指標變化特征確定運動員不同部位疲勞發生的時序性,進而針對薄弱環節進行專門訓練,為攀巖科學化訓練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1 對象與方法
1.1 實驗對象
實驗隨機選取江西省攀巖隊運動員12 名,其中國家健將、國家一級運動員共6 名,作為實驗組;無運動員等級且有2.5年以上攀巖運動經歷的運動員6名,作為對照組。受試者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受試者無任何運動禁忌且無家族運動病史,在實驗前48h 內無熬夜、過度飲酒或者劇烈運動等情況,飲食生活正常。此外,均在實驗前進行了預實驗,熟知實驗流程。

表1 實驗對象基本情況
1.2 實驗儀器
生物電收集,選擇奧地利的SCHUHFRTED 生物反饋儀;即刻最大心率的采集與監測,選擇芬蘭的SUUNTO遠程心率遙測團隊系統。
1.3 實驗方法
受試者穿戴心率帶以及其他信息采集裝置,采用高強度間歇攀巖的運動方式,反復攀爬15m 國際標準賽道,直至達到疲勞指標。疲勞的判斷通過實時監控最大心率的85%確定。實驗需在受試者右側尺骨莖突及側腕曲肌群部位放置sEMG電極片,左側乳頭下方與喉結部位放置HRV電極片。
1.4 運動中疲勞狀態的確定
疲勞狀態的確定:在對運動員的反應時、閃光融合頻率、即刻最大心率以及RPE 等指標進行測定且滿足既定數值后,確定該運動員進入到疲勞狀態。疲勞確定的綜合指標見表2所示。

表2 疲勞確定的綜合指標
1.5 數據處理
實驗數據使用Excel軟件收集整理,使用SPSS 23.0對所收集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單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等統計學分析。P<0.05,表示數據具有顯著性差異;P<0.01,表示數據差異非常顯著。
2 結果
2.1 受試者安靜、疲勞階段HRV指標變化特征
對高水平攀巖運動員與普通運動員在安靜、疲勞兩個階段的心率變異性指標,R-R 間期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SDNN)、相鄰NN 間期之差的均方根值(root mean square of successive differences,RMSSD)、NN間期的平均值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deference between adjacent NN intervals,SDSD)、竇性心律不齊(absolute sinus arrhythmia、SAa)、相鄰NN 之差大于50毫秒的個數占整個竇性心搏個數的百分比(percent of nn50 in the total number of rr intervals,PNN50)、LF、HF、LF/HF、HRV指數展開分析,所得結果信息如表3所示。經分析明確,高水平攀巖運動員與普通運動員二者在安靜、疲勞兩個階段HRV 指標無顯著性差異,但疲勞狀態與安靜狀態相比,高水平攀巖運動員LF/HF 指標出現明顯上升,且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其他指標呈下降趨勢(P<0.05)。疲勞狀態時高水平攀巖運動員與普通運動員相比LF/HF 指標明顯下降(P<0.05),其他指標有下降趨勢,但差異不具顯著性。

表3 攀巖安靜、疲勞的HRV數值分析
2.2 受試者安靜、疲勞階段sEMG指標變化特征
對受試者安靜、疲勞2 個階段的表面肌電指標進行分析,結果見表4、表5、表6。

表4 攀巖高水平組安靜、疲勞的sEMG數據值(μV)

表5 攀巖普通組安靜、疲勞的sEMG數據值(μV)

表6 攀巖高水平組與普通組疲勞時的sEMG數據值(μV)
高水平攀巖運動員與普通運動員安靜時,sEMG各項指標IEMG、RMS、MPF、MF 沒有差異;但由安靜進入疲勞狀態,兩組均呈顯著性差異(P<0.05);在疲勞時,高水平攀巖運動員與普通運動員各項指標均有差異(P<0.05)。
2.3 受試者安靜、疲勞階段生物反饋復合指標時序特征
受試者由安靜進入疲勞時,不同指標出現變化的時序特征如圖1 所示。由圖1 可知,HRV 首先發生變化,其次是肌電,最后是皮電發生變化。由此可推測,受試者在攀巖運動中發生疲勞的順序是由心臟到外周肌肉。

圖1 生物反饋復合指標時序特征圖
3 討論
3.1 HRV在運動疲勞中的特征性變化
高強度間歇訓練(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是指運動時最小運動強度不低于80%VO2Max[3],進行多次持續時間為幾秒至幾分鐘的運動方式,讓機體在不完全恢復的機能狀態下反復訓練,因其運動強度較大的特點,最早由競技體育使用和推廣。HRV(heart rat variability),心率變異性是指逐次心跳周期差異的變化情況。當前,HRV存在著眾多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頻域分析法、時域分析法與非線性(混沌)分析法3 種類型[4]。在實際運動訓練環節,HRV 憑借著自身無創傷性傷害影響、科學高效、操作便捷等優勢,得以大范圍推廣與應用,為生物反饋監測工作的順利展開帶來全新的研究視角,迎來發展的新時期[5]。
高水平攀巖運動員HRV 會隨著攀巖運動疲勞狀態的變化而呈現線特征性變化。高水平攀巖運動員HRV 分析指標內,SDNN 體現出自主神經系統達到的張力水平,RMSSD 體現出迷走神經達到的張力水平,TP體現出自主神經能力,HF與VLF對應反映出迷走神經與交感神經具有的控制能力,LF則表現出交感神經改變的具體趨勢[6-10]。而LF/HF 則表現出高水平攀巖運動員的交感神經以及副交感神經的相互作用情況。
該研究表明,高水平攀巖運動員的HRV 指標、SDNN、TP、VLF 都表現出持續下降的變化趨勢,伴隨HRV 指標pNN50 的不斷降低,則高水平運動員達到的競技水平出現顯著的上升變化趨勢(P<0.05),HRV 相關指標能夠將高水平運動員當前的體能狀況完整地展現出來,便于教練、運動員及時進行運動狀態的調整。
該實驗表明,高水平攀巖運動員在攀巖遞增負荷運動中,隨著運動負荷的遞增,SD1 呈下降趨勢,利用HRV指標對高水平運動員的運動強度適應情況進行評定,選擇心律變異性對高水平運動員的自主神經進行評定具有合理性。該研究HRV首先發生變化,其次是肌電,最后是皮電發生變化。由此可推測,在攀巖運動中發生疲勞的順序是由心臟到外周肌肉。
3.2 sEMG在運動疲勞中的特征性變化
經研究工作顯示,當平均肌電值(AEMG)與確定性線段百分比(%DET)呈現出顯著升高狀態,并且Lempel-Ziv 復雜度C(n)與平均功率譜(MPF)呈現出顯著降低狀態時,表明運動員現階段處在疲勞狀態[11]。伴隨運動員疲勞程度的持續增加,AEMG與%DET沒有明顯改變,而MPF 與C(n)卻表現出顯著遞減的變化趨勢[12]。有研究針對低氧環境以及不同運動狀態等情況下的運動性疲勞肌電圖具有的特征情況展開分析,闡釋了疲勞狀態下運動員肌電圖變化特征及肌電信號特征改變的作用機制。
經實驗分析,明確在遞增強度的運動過程中,運動員出現運動性疲勞時,C(n)、MPF與%DET變化率對于運動強度表現出顯著的依賴性特點;在肌肉疲勞的過程中,sEMG 信號有關的MPF 與C(n)表現出單調遞減的整體變化趨勢,而%DET 則表現出單調遞增的整體變化趨勢。針對運動性疲勞進行的評定工作中,%DET 變化率是相對理想的分析指標,具有一定的推廣與應用價值[13]。有研究針對太極拳運動期間肌電信號的具體變化情況進行分析,明確維持仆步、野馬分鬃以及摟膝拗步動作時,運動員支撐腳股外側肌的MF、MFC、ZCR 以及AEMG 都低于股內側肌。研究指出,MPF 與MF 是在對攀巖運動員的腕曲肌與腕伸肌功能水平進行評定期間具有顯著的有效性[14]。
當前,國內有關sEMG 方面的研究趨向成熟狀態,涵蓋不同肌肉收縮狀態下具有的肌電特征最大隨意收縮產生的肌肉疲勞等眾多方面的研究內容,并且研究期間用到的評定指標極為多樣化。梳理國內現有研究工作明確,在運動員疲勞狀態的監控工作中,用到相對較多并且操作實現更加便捷的指標就是中位頻率(MF)、平均肌電值(AEMG)以及平均功率頻率(MPF)[15-18]。
該研究表明,當攀巖運動員疲勞程度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其速度與步頻將會下降,軀干扭曲的幅度增加,存在多余動作現象,且后仰持續增多,具有疲勞動作表現;伴隨疲勞程度持續增加,運動員的腿部肌肉平均功率頻率將會有所降低,且積分肌電持續增長。
該研究顯示,伴隨運動強度的持續增大,高水平攀巖運動員的MPF、MF、AEMG等指標顯著下降的時間大幅度提前,能夠通過對這些指標顯著下降時間進行監測的方式,對運動員疲勞狀態進行評定。
4 結語
攀巖運動員在攀巖運動直至疲勞的過程中,HRV、sEMG均出現特征性變化;該實驗各指標發生變化的順序為心功能指標HRV、sEMG。由此推測,攀巖運動員在攀巖運動中不同部位進入疲勞的順序為先心臟,后外周肌肉;在競技攀巖運動中,運動員從安靜狀態進入疲勞狀態的順序為心臟到外周肌肉。在攀巖運動員日常訓練中,可針對性訓練心肺功能、有氧運動能力,以提高運動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