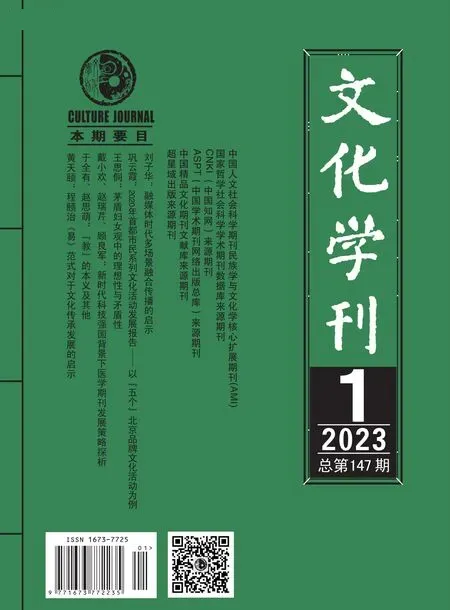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教”的本義及其他
于全有 趙思萌
涉足中華為教之道,不能不涉及對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凝聚著民族教育智慧的“教”的本真內涵的追問與思考。
盡管在中國古代的甲骨文中很早就有了“教”與“育”這兩個字詞,并自《孟子》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1]句中就已出現了“教”與“育”這兩個字詞連用而來的“教育”之表述形式(1)依據清代焦循《孟子正義》(焦循《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05頁)、當代的《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頁)等文獻闡釋,此《孟子》句中連用的“教育”之表述形式,不過是“教”與“育”兩個詞及意義的連用,大致相當于“教而育”表述形式之含義,并非完全等同于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教育”一詞的內涵。在《孟子》這本書中,這種“教育”連用的情況為僅見。,但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古漢語表達以單音節詞為主背景下的許多教育家們在涉及“教育”含義的表述時,往往習慣上依然是將“教”跟“育”分開使用、以“教”與“學”來表達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教育”的有關內涵[2]。特別是以“教”來表達“教育”之意,或者說是用“教”來指稱“教育”的狀況,頗為常見。因而,發掘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凝聚著民族教育智慧的中華為教之道,以汲取先賢留下的有益的精神內涵為我們的民族教育發展服務,顯然就不能不叩問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的本真內涵到底是什么。
一、關于“教”的本義問題
一說到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的意義,不少相關研究者往往會想到“教育”“教導、指點”“告訴”“政教、教化”“效仿”等含義義(此含義下的“教”,音jiào)以及“把知識或技能傳授給人”等含義(此含義下的“教”,音jiāo)[2]87-88。其實,這不過是“教”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相對比較常見的意義,并不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的本義。
按著慣常的一般理解,“教”的意思好像本就是“教育”(此義中“教”,音jiào)、“傳授”(此義中的“教”,音jiāo)等。盡管“教”的眾多義項里,也確有“教育”“傳授”等常見義項,在說到“教”的本義時,有時大概地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卻須要明確的是,這并不是原本狀態意義上的“教”的本義,它們不過是由“教”的原本狀態意義上的本義而衍生出來的“教”的一些常見的意義。
二、由“教”的本義所引發的若干為教之道的思考
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的本義的澄明與厘清,對于我們教育的正本清源、健康發展,無疑具有十分積極的啟迪意義
(一)“教”本身是一種揚善抑惡、有賞有罰的教育、教化行為
“教”的本義意味著: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不僅僅只是一種傳授知識的行為,它同時也是一種上施下效的教育、教化的行為;“教”不僅僅是一種揚善的教育、教化行為,它同時也是一種抑惡的教育、教化行為;“教”不僅僅是為達至揚善的教育目的而可以采用褒揚、賞識的方式去進行的一種教育、教化行為,它同時也是為達至抑惡的教育目的而需要適當采用必要的訓誡、批評的方式去進行的一種教育、教化行為。并且,在古人的意識里,對上述意味中的后者的關注與重視,起碼不弱于前者。這種理解,不僅從“教”字的會意構形及其本義上可以得到體現與印證,而且也跟古代先賢所提倡的人心應當向善抑惡、“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7]等教育、教化思想是一脈相聯的。
古往今來,無論是孟子的人性善之說也好,還是荀子的人性惡之說也好,抑或是人性有善有惡之說、人性無善惡之說也好,盡管人們對人性善惡的理解與主張并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無論持哪種看法的人,都主張人心應當向善抑惡。而社會人心向善抑惡的實現途徑,無外乎是教育、教化與修行。而要有效地達至這種向善抑惡的教育、教化之目的,教育必然要有自己的原則與方式,有一套相應的能夠使受教育者遠惡向善、以達到相應的教育目的的教誨方式、方法與措施。這本是為教之道的應有之義。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前賢已有的對由“教”的本義而衍生出來的“教”的其他意義的闡釋中,得到某些相應的、回向性的印證。《廣雅·釋詁三》曰:“教,效也。”《唐韻·效韻》曰:“教,法也。”后者同時又曰:“教,教訓也。”唐玄應《一切經音義》亦曰:“教,誨也。”[8]前賢的這些對“教”的“效法”“教誨”“教訓”之衍生義的闡釋,等于同時也從不同層面回向性地映現了“教”所內蘊著的這種教育、教化行為內涵的基本輪廓。而教育若要達至使受教育者遠惡向善的教育目的,為教者在具體的致知教育實踐中,必然需要對受教育者施行揚善抑惡、糾正其錯誤與不足的教育。西漢戴圣在《禮記·學記》中曾說道:“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這段話大意是說:人在學習時,有的人是錯在貪多,有的人是錯在所學太少,有的人是錯在把學習看得太容易,有的人是錯在學習時遇到困難就止步不前。這四種過失,是心理不同造成的。為教者需要了解學習者的心理,然后才能挽救其過失。教育就是要激勵學習者好的地方而挽救其過失[7]239-240。清代魏源在《古微堂內集卷二·默觚下》中說:“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長,不知人長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長,則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長,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也。”[9]清人魏源在這當中所說的“教人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也”,與西漢時期戴圣所說的“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明顯地可以讓人感到他們對相關為教之道的理解與認識是一脈貫通的。而揚善或揚長之教,可以以賞,以便激勵、弘揚;抑惡或糾錯之教,則需要用罰或批評,以便戒除、糾正。正所謂“賞以勸善,罰以抑惡”是也。這二者之間本是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一種關系。這樣才合乎為教之道、賞罰分明之道。倘若偏廢二者之間的關系而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崇賞諱罰,這固然可能會使善的行為相對變得更為美好,但同時也會使惡的行為相對變得更為惡劣。這顯然是不合乎相應的為教之道的。《禮記·學記》有言:“能博喻然后能為師。”意思是說:能夠相應地采用多種方法對受教育者進行教育,這才能做老師[7]240。前賢之言,值得后人玩味、深思。
(二)“教”是一種有原則、有底線的教育、教化行為
“教”的本義也意味著: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是一種有原則、有底線的教育、教化行為。而這種教育、教化行為,不僅在施教者那里是一種有原則、有底線的教育、教化行為,同時對受教者而言也是一種讓受教育者養成對世事要有敬畏之心、為人行事要有原則、有底線的教育、教化行為。
盡管我們在教育方法上常說“教無定法”,但這卻并不能因此而推衍出教育無原則或教育無定則、教育沒底線或教育沒定線這樣的邏輯來。對于施教者而言,教育是一種有原則、有底線的教育、教化行為意味著,施教者必須要遵循并堅守一定的、合乎基本的為教之道的原則與底線,去開展相應的教書育人工作。這應該是施教者能夠勝任教席、以免于誤人子弟、以免于“己之昏昏,何以使人昭昭”之虞的一種基本的素質與素養。同時,對于受教者而言,教育是一種有原則、有底線的教育、教化行為,這也意味著教育應當將這種有原則、有底線的行為教給受教育者,讓受教育者效法并養成一種對世事要有敬畏之心(包括與之相關聯的感恩之心等),養成為人行事要遵循并堅守一定的原則與底線的氣質與素養。這也是“教”之本義中的“上所施下所效也”的應有之義。而此應有之義的達至,除了為教者本身的言傳身教外,必要的訓誡批評教誨方式、方法與措施即是為教者借以達至一定的教育目的的一種憑借與手段(當然,這里我們并不是不講原則、條件與方法地,不分青紅皂白、不合教育規律地在推崇訓誡批評的教誨方式)。畢竟,在“上所施下所效”的這種教育、教化行為實施的過程中,沒有規矩,難成方圓;畢竟,一定的目的與目標的實現,合乎相應規律的必要的憑借與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此乃自然之理。
(三)“教”必須以合乎并尊重教育的基本規律為前提
“教”的本義還意味著: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自有自身的規律與軌道,教育中的一葉障目、無知無畏、舍本逐末等違反本身基本規律的行為,既是對為教之道應有規律的一種漠視與誤讀,也是一種到頭來必將會因此而受到教育本身基本規律懲罰的行為。任何教育行為,必須以合乎并尊重教育的基本規律為前提。
近些年來,隨著賞識教育的濫觴與流行及某些社會現象的影響,不分青紅皂白地、生吞活剝地簡單機械套搬賞識教育的狀況時有發生,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基本的教育規律的現象也并不鮮見。我們的一些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已部分地遠離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凝聚著的民族文化智慧的為教之道的應有之義,不僅教育中應有的、必要的批評教育之道不同程度地受到莫名的擠兌與排斥,以至于我們的一些教育已在某種程度上失掉了批評教育的勇氣與氛圍,造成某些必要的批評教育之道的缺失與錯位,而且不加分析與區別地對賞識教育的一味迎合,已使我們的一些教育部分地呈現出有滑向浮化、庸俗化的泥淖之虞。時下,不少學生與學生家長都以學生能夠在所在的集體中當個什么“長”及獲得過什么獎“賞”作為是否受到有關方面“賞識”的重要標志之一。這又致使不僅各級各類層次學校中的各路帶“長”的名頭的行情也隨之一再看漲,頗受追逐,而且各種名目、各種角度的“獎”項滿天飛,并部分地呈現出由僅對學生行為的思路而擴展至包括對教職工行為的思路上發展,以至于一度曾傳出某小學為了迎合這種“賞識”的需要,竟然在班里“創造”出“第×窗臺長”之類的這種帶“長”的“賞識”名目來,以滿足某種畸形的心理與追求。由是可見,目前我們的部分民族教育中的這種“賞識”的庸俗化及對教育的本然規律把握的缺失已經到了多么捉襟見肘、智商捉急的窘境。這還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為教理念與為教追求的應有之意嗎?
為教有原則,方式有尺度。任何不適切地盲目打破或超越規律應有的限度與尺度的行為,往往會適得其反。正所謂“物無美惡,過則不美”是也。為教之道,必本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