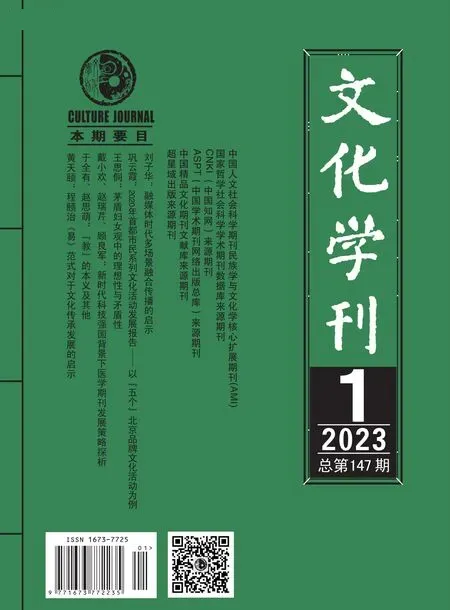明代小說中的市井人物研究
王 卓
在明代人民經濟發展水平穩定,生活富足,且有著豐富多彩的市井生活,文學作品當中也出現了大量關于市井生活、市井人物的刻畫描述,比如:《三言二拍》《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等等,就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文人的筆墨開始關注到豐富多彩的市井生活,這是時代發展造就的民生風貌,更是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與其說是文人的創作目光投射到了市井生活和民生發展之上,不如說是明代繁盛的經濟發展促成了市井文化的興盛,而市井文化的興盛發展對當時社會的文化、藝術、思想等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是現實促成了文學藝術的眼光開闊、內容豐富,也是現實帶給了明代文學藝術發展空前的生命力與創造力[1]。當時社會的發展當中潛藏著一股對底層人民生活關注的動力,逐漸地讓底層勞苦人民的生活成為文學創作的源動力之一,在權貴與威勢盛行的封建社會,這無疑是向著平等自由邁進的一大步,更將百姓的生活與日常經營、喜怒哀樂融入了創作之中,形成了有血有肉的世俗文學基調。在富足的商業發展景況下,體現出對革新的追求,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對未來發展的希望,更體現出對權貴勢力的鄙夷和批判,為平靜的文學藝術發展激起了層層漣漪。當時的市井文化發展,不僅影響了文學藝術創作,甚至對人們的思想、審美、意識潮流的發展趨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充滿活力的,是內涵豐富的。
一、明代小說的市井人物與市井文化
準確來說,明代市井文化的鼎盛時期應當是在明代晚期,而“市井人物”在文學作品當中的出現從這個時期的市井文化發展就可見一斑。封建社會的文人,大多專注于科舉考試,這種制度始于隋朝,設立之初并不完備,隨著不斷的發展,到了唐代逐步趨于完善,更成為了眾多文人學子眼中進廟堂、登高位、光宗耀祖、施展抱負的唯一出路,且不談制度吸引下的競爭何其激烈,就是權貴擺弄下的陰暗與洶涌就讓眾多學子文人寒心。但當時社會文人并沒有更多的謀生手段,社會經濟的發展政策也并不開明,想要有所成就,就只有參與科舉,這也是為什么有許多學子在多次考試之后萌生歸隱的念頭。到了明代,文人雖然仍然參加科考,但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穩定,民生富足,商賈云集,似乎生活的出路有許多,并不只有科考一途,許多家庭在對子女的教養方面也不再只是崇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有了更多的選擇。我國著名的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雖然講述的內容以明代初期為主,但已經能夠看到許多的市井文化內容,其中包括酒肆、肉鋪、茶寮等的描寫,都已經是市井文化的常見場景。包括作品當中的人物“武大”,也是每日以售賣炊餅為生,而王婆也是經營類似短住的驛站,西門慶為當地的富戶,都是典型的市井人物代表。由此可見,市井人物扎根于市井文化,他們的生活大多以市井文化為主要環境,他們當中的大多數生活并不富裕,仍然是底層人民,依賴經商、務農、手工業等為生,謀生的行業較多,涉及市井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們是市井文化的創造者,也是真實生活在市井文化當中的受益者,最能夠體會到市井文化的煙火氣。也有少部分是富足之人,這些富足之人的生活要么依賴于祖上的蔭庇,要么就是商賈之家,也以商業為主要謀生手段,比普通的百姓要生活得優渥一些,成為了市井財富的主要盤踞者。在眾多的市井生活片段當中,他們更像是與統治階級為伍的一群人,有時財富會成為他們的武器,貪婪和欲望會成為他們的典型嘴臉,當然有時候也會有富有者為善,比如:《水滸傳》中的盧俊義,就是出身巨富,也正是因此,他才有了千金散盡救梁山好漢于水火的能力,更有了在江湖上的赫赫威名。
二、明代小說中市井人物的界定
明代小說中的市井人物,有的時候會有許多人對這里的“市井”有誤判,容易與一般的平民產生混淆,實際上市井人物必須要符合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孟子·萬章 》當中曾提及“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通過這一點能夠得知,所謂的市井人物,首先當居于市井之中,而所謂的“市井”本就有著明確的位置信息,市井位于“都邑”之內,而“都邑”則是現代人理解的城市,與農村有著明確的差別。也就是說市井人物必須要居住在城市之中,而并非一般的農戶。而農戶有時候也會把自己種植的農作物臨時帶到城市進行售賣,他們往往都是臨時走街串巷,并沒有固定的攤位,雖然也是進行了商業活動,但是卻并不符合市井人物的根本條件,最多算是進行了短暫的市井活動。當然,這里的城市也包括周邊的一些小城鎮,都與鄉村有著本質的差異。第二,對于市井生活而言,市井人物生活于其中,他們的行為促成了市井文化的發展,同樣他們也是市井文化的一部分。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一些官宦人家也身居城市之中,但是他們本身并不創造市井文化,他們的根本仍然是依靠官位和權勢,并不通過自身勞動創造財富,因此他們都不算是市井人物。第三,市井人物并不參與農業生產,他們可以售賣農副產品,但決不是種植者,他們往往會參與到城市的商品貿易當中,他們的交際與生活都是相對自由的[2]。
三、明代小說中市井人物的特質
明代農業空前發達,人口激增,這就給城市的大規模擴展創造了可能。在這樣的景況下,城市的發展尤其到了明代中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大幅度擴張。封建統治者較為開明,重視農業、商業發展的同時,賦稅制度也有所革新,許多原先沒有人身自由的底層人群都在這一時期獲得了相對之前較高的人身自由度。在城鎮當中還出現了許多的手工藝加工者,他們散布在市井生活的各個角落,滲透在各行各業。在這一時期,市井生活逐步豐富多彩,因此在文人筆下,市井人物的特質也逐步明顯。具體來看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追求商業利益
明代之前,雖然也有唐宋盛世,但是不得不說在對于商業經營的放開方面,明代要明顯優于前朝。前朝大多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統治者認為百姓依賴田產生存,理所當然地把農業作為創造財富的根本,而在一些統治者眼中,經商之人多狡黠,如果放開商業經營,也容易讓底層百姓不好控制,容易出現政局動蕩的問題。到明代,這種格局得到一定的突破,其中既有統治階級較為開明的政策支持,也要得益于長期穩定的政治局面,讓社會財富得以囤積。而運河的修整完善帶來了水路暢通,交通便利,也促成了貨物的流通與文化的交流。在一批人先富裕之后,百姓看到了經商帶來的利潤,因此許多人棄農從商、棄文從商,甚至涌現了蘇州這樣的工商業為主的城鎮。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人們看到了從商帶來的好處,因此許多人希望通過經商來謀生,甚至有人希望通過商業經營獲得大量的財富,當時社會還涌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可見當時的市井文化之繁榮。身處其中的市井人物都以商業為謀生手段,這就從根本上注定了他們要依賴商業來生存,以盈利為基礎目標,有一些人甚至出現了為了逐利而不斷膨脹的欲望。在明代小說當中常常能夠看到市井人物這樣的橋段——通過提供小道消息而賺取銀錢,不給錢就一問三不知,拿到好處后就知無不言。有時候還能看到一些市井人物為了金錢出賣他人,甚至從事一些齷齪卑鄙的事,比如:《水滸傳》中典型的“王婆”,她之所以幫助西門慶與潘金蓮私通,并給潘金蓮出主意謀害武大,本就是出于對銀錢的渴望,她深知西門慶家財萬貫,自己的行為只不過是為自己謀取私利罷了,其實根本談不上與他二人有任何恩怨。這種逐利的心態在當時社會之下是市井小民司空見慣的,有的規矩本分,只為謀生,比如《水滸傳》當中的武大,就是如此。有的則是類似王婆那樣的無底線,只為謀財。無論如何,市井人物的特質之一就是“逐利”,他們從事商業行為,或者是生存在市井之中,都要依賴于“逐利”,他們并沒有田產傍身,想要生存下去,就要通過商業經營活動獲得銀錢,或是多些,或是少些,或是來自正途,或是取自旁門,或是積少成多,或是一夜暴富,總之,他們都是在為了利益奮斗著,生活著。而市井生活的斑斕多彩,也正是源自于市井人物對于“逐利”的根本需要。
(二)為他人提供服務
與農人不同,市井人物沒有田產,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沒有先期的優渥根基,因此許多人都是依賴為他人提供服務而獲得酬勞。在明代的小說當中最常見的這類人物包括:店小二、跑堂、掌柜、鐵匠、屠戶、老鴇、說書人、歌伎、民間藝人等等。單看這些職業就囊括了市井生活的諸多行業,其中男性多以出賣勞動力服務他人,賺取相對辛苦的微薄收入。而女性則依賴自身的容貌、技藝等提供取悅他人的服務。仔細比對發現,其中還有一類服務行業要依賴于市井人物的手工業制作能力,比如:鐵匠、屠戶這些,就更近似于常說的服務型商戶,他們需要掌握相應的技能技術,并且依靠這些技能技術進行商業活動,為他人提供服務。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朝代的小說當中,鮮有在酒樓、飯館從事店小二工作的女性人物出現,更談不上獨自經營或與夫君共同經營酒樓、飯館的女性人物。但在明代的小說作品當中這類女性極為常見,比如《水滸傳》當中的孫二娘,她是《水滸傳》當中為數不多的女將,號稱“母夜叉”,在投奔水泊梁山之前與夫君共同經營一間酒館,表面上是酒館,實際上劫人錢財。《金瓶梅》當中的王婆,先前也是經營著茶館,后來又從事了類似明代小說中對女性常規類的特殊職業“三姑六婆”[3]。此外,明代的許多小說當中都曾經看到過有女子唱曲賣藝的橋段,這些女性工作的場所往往也在各大酒樓茶館和飯店當中,可見當時女性獨立進行服務行業已經司空見慣。這一時期,女性的獨立生存價值得到了明顯的提升,這在市井人物的生活百態中當屬一種突破,她們既獲得了勞動上的自我獨立,也在財務自由上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三)眼界開闊但文化水平較低
與其說明代小說中的市井人物是一類人,不如說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類似階層的群體,這個群體由于從事經營活動,因此接觸的人三教九流都有,這讓他們有了各種談資,也見識到了鄉野農戶無法見識到的各色人群。往往在明代小說當中所刻畫的市井人物形象都是有些市儈的,主要是因為見的各類人多了,聽聞的各種奇聞異事也多了,也許還在經營的摸爬滾打中吃過虧,上過當,經歷過一無所知到無所不知的過程,因此人自然變得市儈起來。常見的青樓老鴇,她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們與牙婆、媒婆等形象相似,總是左右逢迎,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經營的買賣也并不光鮮亮麗,但自己卻不以為然,滿口得意。實際上,這類人雖然被文人刻畫得刁鉆圓滑,市儈奸詐,卻也是經歷了人生的磨難才練就了那樣的嘴臉和鐵石心腸的,總是生活所迫,在所難免。對于明代的市井生活而言,這里常見達官顯貴,文人墨客,卻少有真心之人,他們對市井人物的生活總是心生向往與好奇,不斷往返流連,但是真正要讓他們融入這種生活當中,變成市井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斷然是不愿意的。從根本上來說,這些人是看不起市井人物的,也嫌棄他們本來就不高的文化水平,厭惡他們身上的市井習氣,但又驚艷于他們的見識廣博,五彩斑斕[4]。所以說,明代小說當中的市井人物相當于是介于官宦文人與農人這兩個階層之間的特殊群體,他們既沒有官宦文人的出身地位與學識文化,又沒有農人可以依附的農田瓜地與茅屋草舍,因此他們是被夾在中間遭受嫌棄和鄙夷的。他們同時既有官宦文人沒有的自由自在與色彩斑斕,又有農人沒有的廣博見聞與銀錢流水,因此他們又是被夾在中間被人好奇和在意的。明代小說當中的市井人物,往往就是這么一種沒什么文化,卻有見識,沒什么資本卻又自由的人群,他們開創了一個特殊的局面,一種獨特的審美。
四、結語
在明代小說當中,市井人物絕對是特殊的存在,他們是相對最自由的階層,有著最色彩斑斕的生活圖景,也有著最豐富多樣的民生面貌。因此,這個階層的人物大都性格外放,他們簡單而直接,鮮少刻意美化自我,大多數時候都有著看著不高的追求和并不豐富的文化素養。但是他們的眼界十分開闊,見識的東西多,也有著極強的生存能力。此外,在明代小說中,市井人物往往透著一股子“愚”,這種“愚”并不是“傻”或者“蠢”,更像是一種“接地氣”的表現。他們更像是城市當中默默無聞的一個個配角,但卻樂得自在,都有著自己的快樂與追求。有時候在閱讀小說中會認為他們是“愚”的,但實際上這更是一種適應世俗生活的體現,身在市井,便要樂得市儈。能夠看到的是,女性的地位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明代小說的市井人物塑造當中有了明確的提升,她們或許還不夠完美,但是較之過往,已經足夠獨立,足夠特別。市井生活來源于市井人物,而市井人物本身就是市井生活、市井文化的締造者與參與者,或許說,他們本身就是市井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