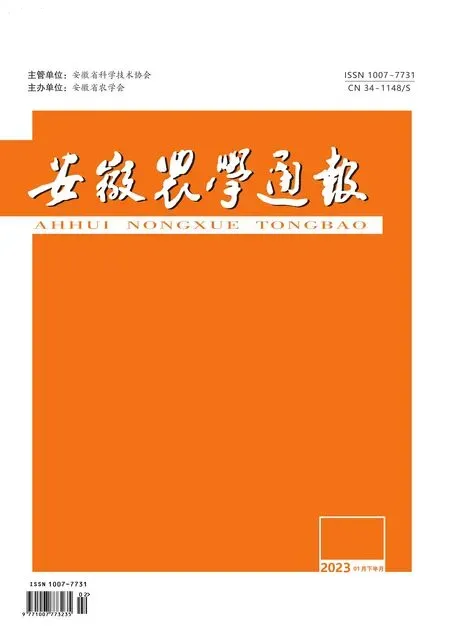石河子地區夏季降雨過程探空資料和雷達產品特征分析
劉曉初 徐臘梅 李瀟瀟 趙胡笳
(1大連市氣象臺,遼寧大連 116001;2石河子氣象臺,新疆石河子 832000;3中國氣象局沈陽大氣環境研究所,遼寧沈陽 110116)
強對流天氣是造成汛期氣象災害的重要天氣類型[1-2]。行業內普遍認為落地直徑不小于2 cm的冰雹、陣風風速達到17 m/s的對流性大風和雨強達到20 mm/h的短時強降水和任何強度的龍卷風均稱為強對流天氣[3-4]。石河子位于少雨內陸地區,短時強降雨標準為2個級別,分別為5和10 mm/h。因此,對流天氣伴隨的降雨為大陸型對流降雨,有必要從潛勢預報和臨近雷達產品對降雨過程進行分析,提升本地對流天氣預報預警水平[5-6]。6~24 h的強對流潛勢預報對落區和類型有一定指示作用[7-8]。研究發現,純粹的短時強降雨天氣與雷暴大風、冰雹天氣的探空資料參數特征值存在明顯差異[9-10]。李瀟瀟等[11]分析大連地區短時暴雨過程發現,某些探空參數對短時強降水有一定指示作用。另外,對流潛勢分析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CAPE值對抬升氣塊的溫濕狀況和水汽變化都非常敏感[12-13]。實際分析中要動態地看待穩定度的變化[14]。對流降水過程中,大氣一般處于中性熱力層結,降水趨于結束時,大氣處于穩定層結。除了潛勢預報,0~2 h的臨近預報對更加精細化的預報預警作用不可代替。不同類型強對流天氣有對應的雷達產品參數特征[15-16],天氣雷達中降水估測產品與實況的偏差主要由不適當的Z-R關系造成[17-18]。新疆作為西部內陸地區,汛期降雨過程顯示出大陸型強對流回波特征[19-20]。沿海地區短時暴雨的雷達回波多為介于穩定性和對流性之間的混合性降雨回波,呈現低質心特征[21-22],且不同地區有獨特變化規律[23-24]。以上研究對石河子地區汛期降雨過程預報預警有一定借鑒意義。
夏季降雨有突發性強,持續時間短,落區范圍小等特點,容易致災,另外,即使量級較低的降水對工農業生產也有一定幫助,因此,準確預報預警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本文利用常規觀測資料和天氣雷達資料,對石河子地區夏季降水過程做中尺度分析,發現特征參數,對當地的降雨和對流天氣預報預警提供一定參考指標,幫助預報員識別本地強對流天氣的系統結構及演變,促進強對流短臨預警系統的本地化應用。
1 分析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石河子位處北疆中段,東南高西北低,山地、沙漠、平原為石河子的主要地貌形態,全年降水稀少,氣候干燥,屬于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石河子地區為灌溉農業區,冬季長而嚴寒,夏季短而炎熱,年降雨量180~270 mm,年蒸發量1 000~1 500 mm。
1.2 資料選取及分析方法
該研究所用資料包括常規氣象觀測資料,即石河子地區地面觀測資料和克拉瑪依探空資料,探空資料時間分別為08:00和20:00;石河子C波段多普勒天氣雷達資料,時間分辨率為6 min。按照石河子地區降水量等級業務規定,該研究劃分如下,24 h降水量在6 mm以下為小雨,6~12 mm為小到中雨,>12~24 mm為中到大雨,24 mm以上為暴雨。小時雨強分為5和10 mm 2個檔次。關于落區,一共4個業務站,分別為石河子本站(356)、炮臺(352)、莫索灣(353)、烏蘭烏蘇(358)。24 h內,2個站及以下出現小雨,劃為局部小雨;3個站及以上出現小雨,劃為全區小雨;3個站出現降雨,1個站及以上出現中雨量級,劃為小到中雨,以此類推,直到全區出現降雨,1個站出現暴雨,劃為暴雨過程。關于探空資料,石河子地區上游最近的探空站位于克拉瑪依,與石河子直線距離160 km左右,海拔400 m,且周邊為戈壁荒漠。
2 降水過程發生規律
對地面觀測降水量實況統計分析發現,2018—2020年6—8月石河子地區共有53次降水過程。其中,局部小雨過程22次,約占42%;全區小雨過程21次,約占40%。由此可見,小雨過程占全部過程的82%。小到中雨過程5次,中到大雨過程4次,暴雨過程僅有1次。另外,從發生時段來看,發生在傍晚到夜間(17:00—次日08:00)的過程有43次,占81%,其中中雨以上量級僅有一次中到大雨過程發生在白天。
3 探空資料分析
3.1 能量參數
K指數是最常用的識別對流的參數之一,其定義為850與500 hPa溫度差,加上850 hPa露點溫度,減去700 hPa的溫度露點差。通常,K指數小于25,不容易產生雷暴;25~30,雷暴概率較小;30以上,雷暴概率較大。從定義看,低層水汽(850 hPa露點溫度)越大,層結越不穩定(850和500 hPa溫差),以及700 hPa飽和度越大,K指數越大。53次降雨過程整體的K指數中位數為29(表1),按照降雨量級分類,各個量級過程的中位數都小于等于30。只有2019年7月10日暴雨過程,K指數為32。K指數對降水過程有一定指示作用。全部個例的850與500 hPa溫差(T85)都達到28℃以上(表1),層結較為不穩定,指示作用強。克拉瑪依為荒漠站點,低層大氣水汽飽和度較低,850 hPa露點溫度(Td850)較低,中位數全部小于5℃,并且700 hPa溫度露點差較大,與東部沿海地區區別較大,降水指示作用不強。
CAPE值對抬升氣塊的溫濕狀況敏感,抬升氣塊的溫度或者露點溫度升高1℃,CAPE值分別平均增加200和500 J/kg,因此,當大多數降水過程發生在傍晚到夜間,而直接用08:00探空資料分析時,由于白天荒漠地區地表加熱作用顯著,傍晚近地面溫度(Ts)和露點溫度(Tds)與08:00的有明顯差別,CAPE值發生較大變化,無法有效表征對流降水發生前的周圍大氣環境。從各量級降水過程的CAPE值中位數(表2)也能看到,指示對流降雨作用不大。
3.2 溫濕狀況參數
探空最底層位于海拔400 m左右。探空底層溫度(Ts)中位數在23~27℃,露點溫度(Tds)中位數在8~11℃(表1),表明探空最底層大氣飽和度較差;而作為東部沿海平原地區的有利于降雨的低空水汽條件特征量,850 hPa露點溫度(Td850)應該較大,850 hPa溫度露點差(T-Td850)應該較小,此特征在西北地區概率很小。從各個量級降雨過程的中位數(表2)看,東部地區夏季降水前,850 hPa露點溫度可能達到12℃,甚至16℃,但是石河子地區該特征量的中位數僅為2~5℃,850 hPa溫度露點差中位數為12~20℃,表明探空底層400~1 500 m大多數為干層,對降雨指示作用不大。作為所在高度大氣實際水汽含量的參數,各個量級降雨過程探空底層比濕(Q5)中位數為7.0~8.6 g/kg(表1),700 hPa在東部平原地區已是降水過程水汽頂層,其高度的比濕(Q700)中位數為5.4~7.8 g/kg,具體到每個過程的探空資料,53次過程中有27次700 hPa比濕(Q700)直接大于探空底層比濕(Qs)或者大于按照正常遞減率到700 hPa的比濕,占比51%,表明特征濕層在700 hPa附近的指示作用更大。進一步分析發現,600~500 hPa的溫度露點差(T-Td600)小于4℃的過程有50次,占94%。與降雨過程有非常好的對應關系。

表2 2018—2020年6—8月石河子地區各量級降雨過程前探空資料的部分物理量
高低空的溫差反映了大氣垂直溫度梯度。700和500 hPa溫差(T75)中位數在14.0~17.5℃,850和500 hPa溫差(T85)中位數在28~32℃。與東部地區對流潛勢特征值基本一致。
3.3 動力穩定度參數
中等強度以上的0~6 km深層垂直風切變(SHR0-6)與大冰雹、對流性強陣風和龍卷等強對流天氣密切相關。另外,強對流天氣系統如多單體強風暴、超級單體和颮線等也產生在較強的深層垂直風切變環境中。中等強度(大于10 m/s)以上過程31次,強垂直風切變過程(大于19 m/s)6次,分別占比58%和11%。由此可見,降水可能只是對流天氣現象中的其中一種。環境潛勢也有利于雷雨大風等災害性強對流天氣發生。
當0℃層高度附近大氣飽和度較低時,濕球0℃層高度(H0)與0℃層高度差別較大。H0中位數在3.7~4.2 km(表1),很多過程干球0℃和濕球0℃的高度有較大差別,需要訂正后使用。抬升凝結高度(HLCL)是未飽和濕空氣塊干絕熱上升、剛開始凝結的高度。高度較低有利于強對流的發生和發展。HLCL中位數為0.8 km(表1)。

表1 2018—2020年6—8月石河子地區降雨過程前探空資料的部分物理量中位數
探空應用較好的例子是2019年7月27日過程(圖1b)。K指數達到28;CAPE值為920 J/kg,接近中等強度;850與500 hPa溫差高達32℃,大氣層結不穩定;0~6 km垂直風切變為20 m/s,強度較大,溫濕廓線呈上干下濕的“喇叭”形狀,有利于強對流發生。降雨發生在22:00左右,從雷達回波上看,多單體對流風暴呈南北帶狀排列。潛勢預報中探空特征參數指示作用較好。另外,2019年7月10日暴雨過程(圖1a),K指數達到32,并且在600 hPa附近濕層相對深厚,對短時對流性降雨有一定指示作用。另外,分析各個過程的溫濕廓線發現,近地面為西北風,大氣飽和度較低,中層為西南風,大氣飽和度較高。

圖1 2019年7月10日08:00(a)和27日20:00(b)克拉瑪依探空圖
4 雷達產品特征分析
夏季對流降水的量級大小取決于降水效率和持續時間。較高的降水效率與暖云層厚度有關,另外,還需要低層水汽的持續輸送。對流降雨通常分為大陸型和熱帶型,石河子地區明顯屬于大陸型。從圖1的2個個例探空圖看出,地面到850 hPa甚至700 hPa水汽飽和度都較差,600 hPa附近大氣才接近飽和,并且濕層厚度比東部沿海地區更小。大陸型對流降水的特征是強回波發展高度較高,質心較高,大粒子較多(大雨滴、霰和冰雹),密度小。因此,降水效率不高,天氣雷達中的降水估測產品與地面降水量實況的偏差就比較大。一般情況下,雷達有效的測雨范圍不超過150 km。結合到石河子地區的實際情況,炮臺和莫索灣測站位置相近,偏北;石河子和烏蘭烏蘇相近,相對偏南。一次降雨過程影響到各個站點的回波演變是不同,需要單獨分析。因此,53次降雨過程對應142次雷達回波演變。
4.1 組合反射率和徑向速度特征
組合反射率(CR)表示的是一個體掃中,定常仰角方位掃描中發現的最大反射率因子投影到笛卡爾格點上;優勢是不用查看每個仰角就能快速查看到風暴中的最大反射率因子;缺點是無法識別某個仰角上的有用特征。如表3,同樣按照降雨量級劃分,最大強度的中位數為25~35 dBz,一般強度在35 dBz以上才達到對流強度,按此標準,局部小雨、全區小雨過程一般僅為層云降水,中雨以上才有對流特征。從整體上看,降雨過程最大強度中位數為30 dBz,與冰雹、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有明顯差異。

表3 2018—2020年6—8月石河子地區降雨過程雷達資料部分參數的中位數
徑向速度(V)一般用來識別中小尺度速度對,中層高度具有一定速度的旋轉、中氣旋,或者不同仰角上大范圍的輻散幅輻合鋒面過境,判斷系統的發展;或者可通過最低仰角上雷達站附近的入流和出流速度判斷地面大風。雷達站附近距離地面1 km高度范圍內,風速達到15 m/s的案例僅為7次,占比5%,表明到達地面產生8級以上大風的情況很少,降雨與地面大風的伴隨關系也不強。
4.2 垂直累積液態水、回波頂高和雨量估測特征
垂直累積液態水(VIL)表示將反射率因子數據轉換成等價的液態水值。它的假設是所有的反射率因子返回都是由液態水滴引起的經驗導出的關系,其實質是反射率因子的垂直累積,代表了雷暴的總體強度。VIL數值的突然增大對冰雹預警有較好的指示作用。全部降雨過程的VIL中位數為0~0.5 kg/m2,總體上降雨不會伴隨冰雹。僅有2018年7月13日過程的VIL值達到20 kg/m2(表4),有可能伴隨冰雹。
回波頂高(ETPPI)與0℃層高度比較,0℃層高度的中位數在3.7~4.2 km。夏季-20℃層高度一般在6 km左右,如果對流風暴發展旺盛,45或50 dBz以上的強回波高度達到-20℃層高度,容易出現災害性冰雹,該研究的大部分降雨過程對應的回波頂高中位數都在6 km以下,只有中到大雨過程的回波頂高中位數達到7 km(表3),有可能出現強冰雹。
雨量估測中,如果降水粒子中的固態粒子(冰雹顆粒)較多,而不是密度較大、顆粒較小的暖云產生的液態水滴占多數,那雷達降水估測產品中的Z-R關系就偏差較大。在全部142次降雨實況與雷達產品的對比中,有19次回波頂高超過0℃層高度2 km以上,接近或超過-20℃層高度,占比13%,而近似于暖云降雨的回波占87%。因此,大部分產生降雨的雷達回波中,降水估測結果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從按照雨量劃分的1 h降雨量估測產品看(表3),局部小雨的中位數為0.5 mm/h,按照量級依次增大,降雨估測產品中位數也大致增大,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有一定參考價值。另外,產生暴雨不僅要有較長的持續時間,雨強也相對其他量級降雨過程更大。
以2019年7月10日的暴雨過程(圖2和表4)為例,影響石河子(356)和莫索灣(358)的回波最大強度為40 dBz,所在高度最高僅為3~4 km,回波頂高為7 km,對流發展并不旺盛,VIL最大值僅為0.5 kg/m2,沒有冰雹特征。從降水估測產品看,雨強達到6 mm/h,所有過程中最大,天氣現象以短時強降雨為主,雷達站西側上游不斷有回波東移經過測站,降雨持續時間較長,造成局地暴雨。

表4 2018—2020年6—8月石河子地區各量級降雨過程雷達資料的部分參數

續表4 2018—2020年6—8月石河子地區部分降雨過程雷達參數

圖2 石河子雷達2019年7月10日21∶51(a)和11日00∶15(b)0.5°基本反射率
從雷達產品特征上看,總體上,短時強降雨為主過程并不伴隨冰雹和雷暴大風。
5 結論與討論
石河子位于北疆中段,屬于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夏季降雨突發性強、持續時間短、落區范圍小,有明顯的大陸型對流降雨特征。該研究通過對石河子地區夏季降雨過程的探空和天氣雷達資料研究發現:①53次降雨過程絕大多數量級為小雨,并且發生在傍晚到夜間。②探空資料上,K指數、850和500 hPa溫差是對流降雨可靠指示參數。探空底層和850底層大氣飽和度較差,指示作用不強。③600 hPa附近濕層為當地獨特指標參數;600~500 hPa的溫度露點差小于4℃的過程有50次,占94%。與降雨過程有非常好的對應關系。④短時強降雨過程通常不伴隨冰雹和雷暴大風。⑤1 h降雨估測產品可靠度較高。西北內陸地區降雨效率不高,但是降雨持續時間較長,累積降雨量仍然有可能達到暴雨量級。
不足之處為大多數降雨過程發生在傍晚到夜間,08:00探空代表性較差。在現有條件基礎上,結合實況和模式預報,對08:00探空資料進行訂正,再檢驗預報預警的提升效果,可作為未來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