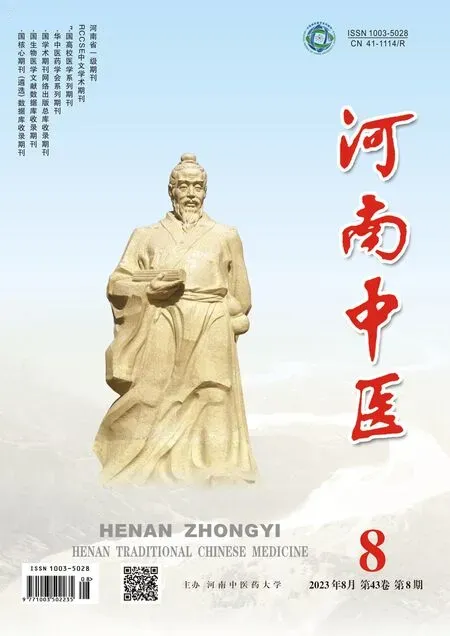中醫藥調控NLRP3炎性小體治療痛風研究進展*
馬小杰,李大可
1.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 250000; 2.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東 濟南 250000
痛風是一種常見的代謝性關節炎,發病率呈逐漸升高趨勢,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及工作。西醫治療痛風多采用抗炎止痛類藥物,中醫藥治療痛風更具有優勢。研究發現,尿素、膽固醇結晶及無菌顆粒等物質可以通過內吞作用進入細胞內,破壞溶酶體膜的穩定性并激活溶酶體蛋白酶,進一步激活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異蛋白酶(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1,Caspase-1),形成Nod 樣受體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yrin domain 3,NLRP3)炎性小體,促進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分泌,加重對機體造成損害[1]。本文就中醫藥調控NLRP3炎性小體治療痛風的研究進行系統整理,為治療痛風提供新思路。
1 痛風的中西醫概述
痛風是一種與代謝和遺傳因素有關的以血尿酸升高、局部關節腫痛為主要表現和特征的晶體性關節炎[2],主要是由于嘌呤代謝紊亂和(或)尿酸排出減少,導致血尿酸水平超過人體血清的溶解度,引起單鈉尿酸鹽(monosodium urate,MSU)結晶沉積于關節、軟骨等而引起的一系列炎癥性臨床表現。痛風的主要臨床表現為關節紅、腫、熱、痛[3],最常見的癥狀為第一趾跖關節腫痛,如不及時治療,可有痛風石出現,日久會引起骨質破壞及腎功能不全[4]。大量研究表明,肥胖、慢性腎臟疾病、代謝綜合征、高血壓、2型糖尿病、脂肪性肝病及心血管疾病等與高尿酸血癥和痛風的發生密切相關[5-11]。西醫治療痛風急性期采用非甾體藥物等抗炎止痛以緩解疼痛;緩解期主要目標為降低血尿酸水平,藥物主要通過抑制尿酸生成或促進尿酸排泄兩種途徑發揮作用[3,12]。西藥治療痛風療效較好,但會出現腹瀉、惡心、嘔吐、出血等胃腸道不良反應及腎臟功能損害等[13]。
痛風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亦有記載,最早見于朱丹溪的《格物余論》[14],但與現在所說的“痛風”相比有明顯的區別。廣義上的痛風應歸屬于《黃帝內經》 中的“痹證”[15]或《金匱要略》中的“歷節病”[16]等。近代著名國醫大師朱良春根據其濕濁瘀滯的病機特點為其提出了新的命名——“濁瘀痹”[17-18]。《素問·太陰陽明論》云:“傷于濕者,下先受之。”[19],故本病的初發癥狀為下肢腳趾的紅腫熱痛,病機以脾失健運、肝腎虧虛為本,濕熱痰瘀阻滯為標[20],亦形成本虛標實之證。由于患者先天稟賦不足,加之嗜食肥甘厚味、飲食不節,易損傷肝脾腎三臟功能,脾失健運,濕濁內生,郁久化熱,外受風寒濕邪侵襲,內外合病,濕熱瘀邪攻注筋骨關節而導致痹癥發生。中醫從整體觀念出發,運用辨證論治方法,調整人體陰陽,達到平衡狀態[21]。近幾年,大量研究發現中藥在抗炎、降尿酸有明顯優勢,且不良反應相對較少[22]。
2 流行病學研究
由于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及生活方式的改變,導致嘌呤的攝入量大幅度升高,血尿酸水平急劇變化,促使國內外痛風發病率不斷增長[23]。近來文獻報道中表明,痛風的患病率有以下特點:患病率逐年升高,發病人群趨于年輕化,存在性別和地區明顯差異[24-26]。目前,全球痛風發病率大約為7.9%[27],發達國家的發病率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根據我國流行病學統計結果發現,我國痛風患病率為0.86%~2.20%,其中男性占0.83%~1.98%,女性占0.07%~0.72%,男女發病比例為201[28]。
3 NLRP3炎性小體
炎性小體是由Tschopp研究小組最先發現并提出定義,是一種由巨噬細胞產生并激活的并由細胞質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參與組成的復合物[29],可感知微生物和內源性危險信號,通過各種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和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 rel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進行信號轉導[30-31]。目前,NLRP3炎性小體是科研領域中研究較多的炎性小體之一,是參與自身免疫的重要成員之一。NLRP3炎性小體由傳感器NLRP3模式識別受體、適配器接頭凋亡相關斑點蛋白(apptosis associated a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 domain,ASC)和效應分子前Caspase-1構成的蛋白復合物。NLRP3與銜接蛋白ASC結合,可激活Caspase-1并作用于IL-1β和白細胞介素-18(interleukin-18,IL-18)等細胞因子前體,促進促炎細胞因子IL-1β和IL-18等的生產及分泌,導致細胞的熱休克死亡及周身炎癥反應[32-33]。各種免疫細胞反應中均可見NLRP3炎性小體的存在,如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及抗原提呈細胞等。關于激活NLRP3炎性小體的機制研究說法過多,多數研究者認為其激活主要與離子流、線粒體功能障礙、活性氧基團(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產生以及溶酶體損傷有關[34-36]。
4 痛風與NLRP3炎性小體的關系
痛風性關節炎的發病與血尿酸水平的升高和炎癥反應密切相關,其信號轉導通路主要有NLRP3信號通路、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TLR)信號通路、嘌呤受體P2X7信號通路及絲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號通路等[37]。在痛風發病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是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及細胞因子IL-1β的產生。NLRP3炎性小體在激活前必須被啟動,啟動包括兩個信號[38]:信號1是由核轉錄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激活途徑介導,誘導了功能性炎性小體成分的表達,如NLRP3;信號2是由尿酸鈉晶體提供,觸發炎性小體的組裝。MSU晶體與質膜的相互作用促進了一種細胞反應,這種反應目前尚不清楚,但是NLRP3激活的標志,還有鉀通過離子通道流出和線粒體擾動,導致線粒體活性氧的產生和釋放到細胞質中[39]。臨床研究發現,NLRP3炎性小體及其下游炎癥因子的異常表達是導致痛風患者產生炎性反應和免疫反應的重要因素之一[40-41]。實驗研究證實,在急性痛風小鼠模型中,NLRP3缺失的小鼠不能對MSU晶體產生反應且無法產生具有活性的IL-1β。正常情況下,孤立MSU結晶不會引發痛風,沉積的MSU晶體可以被TLRs識別,促進NLRP3寡聚和炎性小體組裝,適配器蛋白ASC被招募到炎性小體中,導致Caspase-1的蛋白水解活化,活躍的Caspase-1促進pro-IL-1β、pro-IL-18的蛋白裂解,并進一步成熟為具有生物學活性的IL-1β、IL-18[42],增加IL-1β和 IL-18 的分泌。Caspase-1還促進gasdermin D的裂解,生成N端裂解產物,在質膜上齊聚,導致焦化孔的形成,這些孔破壞了細胞質膜的完整性,并可能有助于的炎癥介質的釋放。此外,ROS在NLRP3激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MSU晶體通過激活線粒體外膜透化作用損傷線粒體DNA并抑制其自噬,產生的過量ROS活化NLRP3炎性小體,從而誘導炎癥擴增[43]。雖然IL-1β的激活和NLRP3炎性小體在痛風中的介導作用已有大量研究,但涉及MUS觸發NLRP3激活的上游通路尚未完全了解。有研究發現[44-45],抑制細胞中NLRP3炎性小體的產生可使炎癥得到改善。因此,針對NLRP3發揮效應時需募集ASC和Caspase-1的特性而研發的選擇性拮抗劑,可能對迅速控制炎癥有幫助。
5 中醫藥對NLRP3炎性小體的調控作用
5.1 電針治療多項研究[46]證明,電針能夠緩解痛風發作時的臨床癥狀,通過降低炎性因子的表達量,從而達到抑制炎癥反應的目的。邱麗[47]、譙童茜等[48]通過電針急性痛風性關節炎大鼠模型的“足三里”“三陰交”等穴位發現,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受到抑制可能與IL-1β和IL-18的表達量減少、炎癥反應得到有效緩解有關。在電針治療痛風性關節炎的臨床研究中證明,電針治療痛風性關節炎能明顯抑制NLRP3、Caspase-1、ASC蛋白及IL-1β、TNF-α等炎性因子的表達,但在研究中也發現,NLRP3 mRNA表達水平增高[49-50],因此,NLRP3 mRNA的表達量研究存在爭議,可能具有雙向調控作用,需進一步研究。
5.2 單味藥及其提取物在大量痛風性關節炎的大鼠實驗研究中發現,萆薢總皂苷[51]、牛膝總皂苷[52]、土茯苓總黃酮[53]、三腳風爐水提物[54]、山核桃葉黃酮單體[55]、千斤拔提取物[56]、貓須草水提物[57]、短穗兔耳草提取物[58]、白頭翁皂苷[59]、鼠麴草醇取物[60]、虎杖醇提物[61]、葛根素[62]、牡丹花總黃酮[63]、異落新婦苷[64]等中藥提取物均可抑制NLRP3炎性體軸活化,通過抑制NLRP3的激活,從而降低NLRP3、ASC、Caspase-1的表達,減少其下游炎性細胞因子IL-1β、IL-6、IL-8和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的生成和釋放,改善關節炎癥反應,緩解疼痛。在使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和 MSU晶體刺激THP建造的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細胞模型中運用豨薟草醇提物[65]治療后發現,IL-1β的產生及活化需要TLRs與NLRP3炎性小體共同作用,NLRP3炎性小體是無活性的前體IL-1β轉化成有活性的IL-1β關鍵因素。其作用機制可能為通過抑制NLRP3炎性小體活化,使NF-κB信號通路受到抑制,故NLRP3 mRNA、NLRP3及IL-1β蛋白表達水平都明顯下調,減少炎癥因子的產生與釋放。研究證明,藥物通過抑制NLRP3炎性小體,影響NF-κB信號通路,減少IL-1β、TNF-α等促炎因子的釋放。
5.3 中藥復方中藥復方在痛風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其在抗炎、降尿酸和改善關節癥狀等方面有明顯優勢[66]。實驗研究一般以大鼠為研究對象,制備痛風性關節炎模型,研究中藥復方對NLRP3炎性小體及其相關炎性因子的抑制調控作用。
5.3.1 實驗研究桂枝芍藥知母湯出自《金匱要略》,在臨床上常用于治療痛風性關節炎,具有祛風除濕、通陽散寒、清熱的作用。現代藥理研究表明[67-68],桂枝芍藥知母湯有較強的抗炎鎮痛作用。房樹標等[69]通過大鼠痛風模型研究發現,桂枝芍藥知母湯能夠明顯改善大鼠的痛風癥狀,明顯降低NLRP3炎性小體、ASC及Caspase-1表達量,高劑量組可明顯抑制TNF-α、IL-6、IL-1β的分泌,但Caspase-12表達量明顯增加。有研究表明,Caspase-12表達量增加可以抑制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實驗證明,桂枝芍藥知母湯抑制炎癥可能是通過Caspase-12表達量增加抑制NLRP3炎性小體與NF-κB活化,進而減少IL-1β分化成熟,抑制炎性信號通路的活化[70]。賈萍等[71]通過實驗研究發現,高劑量豨桐丸能明顯降低尿酸鈉晶體誘導的大鼠痛風性關節炎中NLRP3炎性小體、TNF-α、IL-1β、IL-6水平。白虎加桂枝湯的功效為清熱利濕、通絡止痛,是治療濕熱痹證的經典方藥,臨床治療濕熱偏盛型痛風效果明顯。劉偉偉等[72]通過實驗研究發現,白虎加桂枝湯通過抑制NLRP3炎性小體激活,降低高尿酸血癥合并痛風性關節炎大鼠模型中NLRP3、Caspase-1、TNF-α、IL-6、IL-1β等炎性因子水平,并且升高IL-10等抑炎性因子水平,使炎癥反應得到明顯緩解。四妙散清利濕熱、通絡止痛,明顯改善血尿酸水平,為治療痛風的妙藥。劉亞飛等[73]在加味四妙方治療高尿酸血癥合并急性痛風性關節炎中的實驗中,發現NLRP3 mRNA、IL-1β、TNF-α表達均降低,其作用機制可能與調控NLRP3炎性體及下游炎性因子IL-1β和TNF-α的分泌有關。健脾化濕亦為痛風的常用治療原則,在通痹七物方[74]治療痛風性關節炎大鼠的研究中發現,中劑量藥物對NLRP3、Caspase-1、IL-1β 蛋白表達抑制最明顯,可能與作用靶點的量效有關。清熱養陰除濕丸[75]、蠲痹歷節清方[76]等中藥復方具有明顯的抗炎作用,可抑制NLRP3蛋白及mRNA表達,降低炎性因子IL-1β、IL-18、TNF-α的含量。加味三妙丸防治THP-1細胞痛風性關節炎的研究發現[77],中藥能明顯降低NLRP3、NF-κB、ASC、Caspase-1蛋白表達,抑制pro-IL-1β的產生,減少IL-1等炎性因子的分泌,表明加味三妙丸能通過抑制NF-κB 信號通路及NLRP3炎性小體活化,減少Caspase-1、pro-IL-1β的表達,從而抑制炎癥反應。
5.3.2 臨床研究中藥復方在治療痛風性關節炎方面臨床應用較為廣泛,大量研究發現其與NLRP3炎性小體之間關系較為密切。楊磊等[78]采用加味四妙散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結果顯示,加味四妙散可抑制NLRP3炎性小體的生成和活化。近年來,大量研究發現,中藥復方可通過抑制NLRP3炎性小體與Caspase-1表達,從而降低細胞因子IL-1β和IL-18水平,達到抗炎、降低尿酸的效果[79-81]。黃正橋等[82]通過采用不同實驗技術探討蠲痹湯治療濕熱瘀阻型痛風與NLRP3炎性小體表達的研究發現,NLRP3、Caspase-1 mRNA表達水平量有所升高,IL-1β、IL-8表達水平均明顯下降,作用原理可能為蠲痹湯在抑制炎癥的過程中下調NLRP3表達的負調控因子,從而減少Caspase-1的活化、NLRP3炎性小體激活,抑制IL-1β前體的生成,減少IL-1β細胞因子的生成。曹詩丹等[83]在研究清熱除痹方治療痛風性關節炎實驗中亦發現,Caspase-1及NLRP3 mRNA表達升高,ASC mRNA、ASC、Caspase-1蛋白、IL-1β、IL-8表達水表達降低,再次說明在中藥治療痛風抑制炎癥的過程中,NLRP3 mRNA可能具有負向調控作用[84]。國內各大研究發現,痛風患者的NLRP3炎性小體在mRNA、蛋白水平及抗炎因子的表達均為異常[85]。
6 結語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及不健康飲食習慣的存在,導致痛風發病率持續上升,若未給予及時治療,會產生不可逆的組織破壞、骨侵蝕、關節疼痛僵硬及腎臟損害,給患者帶來不便,影響生活質量。目前,對于痛風的治療,西藥以抗炎止痛、降低尿酸為主;中藥通過辨證論治,而發揮降尿酸、抗炎的作用,緩解痛風癥狀,避免復發。近來研究發現,NLRP3炎性小體在中醫藥治療痛風中具有重要作用,其通過抑制NLRP3炎性小體的組成及其下游炎性因子IL-1β、IL-18的表達來緩解痛風炎癥,但也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1)中藥復方治療痛風效果顯著,但其成分復雜,未能確定其具體起效的活性成分;(2)中藥多采用調控NLPR3炎性小體治療痛風,NLRP3炎性小體存在雙向調節作用,但其具體作用機制尚未清楚,仍需進一步探究。
總之,中醫藥在調控NLRP3炎性小體治療痛風中具有諸多特色和優勢,通過現代實驗技術為中醫藥治療痛風提供有力的藥理學及臨床證據,為中醫藥研究治療痛風提供理論指導,進一步研究NLRP3炎性小體,有望成為痛風預防和治療的新藥物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