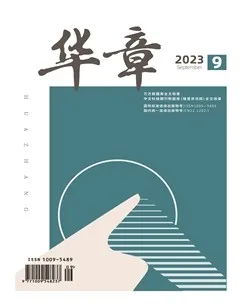論我國刑事訴訟中親屬拒證權的引入與適用
張佳翔 黃鈺
[摘 要]盡管2012修改后的刑訴法賦予了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拒絕強制出庭的權利,但并未真正免除親屬證人的作證義務。同時由于“筆錄中心主義”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根深蒂固,而“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仍未被貫徹落實,近親屬拒絕強制出庭的權利客觀上架空了被告人的質證權。親屬證人這一強制出庭豁免權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拒證權,我國刑事訴訟亟需引入完整意義上的親屬拒證權。在借鑒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的實踐探索的基礎上,理論上需進一步明確親屬拒證權的權利主體、權利內容、行使程序和權利保障,為將來我國刑事訴訟立法制度的構建提供有益的理論參考。
[關鍵詞]親親相隱;親屬拒證權;制度構建
一、問題的提出
親親相隱是我國的一項傳統法律制度。該制度所彰顯和維護的人倫親情具有普世價值,對于維護家庭和諧與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被不同歷史時期的立法所繼承并加以完善。盡管作為一項制度的“親親相隱”在當下我國出現了斷裂,但作為一種價值理念的“親親相隱”并未從普羅大眾的內心情感中抹去。2012年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賦予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與子女免于強制出庭的權利。總體上看,該條款的修訂無疑是一大進步,是對此次修法將“尊重與保障人權”確立為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具體呼應和貫徹。但是否就像贊賞者認為的那樣,我國就此正式確立了親屬拒證權?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陳光中教授所言,這樣的規定“與國際通行的親屬拒絕做證權相距甚遠,頗有‘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感”[1]。最終確立完整意義上的親屬拒證權,仍需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共同努力。本文將說明當今將親屬拒證權引入刑事訴訟的規范依據、理論依據,進而闡明如何構建真正完整意義上的親屬拒證權。
二、我國刑事訴訟引入親屬拒證權的依據
(一)規范依據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的規定“根據憲法,制訂本法”,由此可知《憲法》是制訂我國刑訴法的根本規范依據。不僅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同時《憲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婚姻、家庭受國家的保護”,而該條款位于《憲法》第二章,而該章專門用來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由此可知,家庭權在我國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那么國家自然就對公民的家庭權負有兩項義務,即消極的不予干涉公民家庭權的義務和積極的保護公民的家庭權免受侵害的義務。而親屬關系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之上,拒絕做對親屬不利的證言是人的本能使然,是人的一項自然權利。親屬拒證權對于人倫親情的保護,對于家庭和諧關系的維護來說都至關重要。考慮到家庭權的基本權利屬性,親屬拒證權作為家庭權的組成部分,也具有基本權利的性質。
(二)理論依據
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和睦關系著社會和諧。親屬拒證權作為儒家倫理的產物,與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西方的自然法學派認為“惡法非法”,只有符合人性的法才是良法。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這就意味著任何人只要符合證人的條件就必須作證,哪怕自己的證言會導致自己的親屬承受法律上的不利,這種一刀切的立法規定無疑是強迫個人違背自己的本性去履行法律義務。此外,若如此的話,很有可能將親屬推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對立面,會讓其產生被拋棄感,以至于對這個家庭和社會產生絕望,一旦如此,刑罰的特殊預防效果將大打折扣,其一旦重歸社會后再犯的可能性依然很大。這種立法不但難以獲得公民內心的認同,也很難稱得上是良法,而親屬拒證權的引入能夠解決法律義務與人倫親情之間的對立與沖突。
其次,親屬拒證權符合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論。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為人在實施某一具體行為時,根據行為時的主客觀情況,如果法律不能期待他實施合法行為,就不應該認為他的行為構成犯罪,也就是我們古老的法諺所說的“法不強人所難”。親屬拒證權正是刑法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鮮明表現,它在被告、犯罪嫌疑人的親屬證人迫不得已實施違法行為的境地下,不是強人所難而是給以充分的關注和同情,不僅體現了對基于血緣親情而為之行為的認可,還包括對人趨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蘊涵著獨特的人文關懷精神[2]。此外,親屬拒證權也符合美國法學家富勒所講的“法律的道德性”,富勒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性》系統論述了法治的八大原則,法的可行性便是其中之一。法的可行性意味著,任何一項法律都要考慮其所規范的對象的具體情況,不能強迫一般人實施其根本無法做到的行為。考慮到法所調整的對象具有一般性,即使某一個體能夠實施某一行為,但絕大多數人無法依照法的要求行為的話,那么這個立法就不具有內在道德即不符合“程序自然法”。而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關于強迫親屬作證的規定就不符合富勒所強調的“程序自然法”的內在要求,在刑事訴訟引入親屬拒證權無疑能夠提升現行《刑事訴訟法》的道德
品質。
三、我國親屬拒證權的制度構建
(一)親屬拒證權的權利主體
關于親屬拒證權的權利主體,我國學界主要存在著“單主體說”和“雙主體說”。單主體說又分為兩種,一種認為親屬拒證權的權利主體為被追訴人,另一種認為被追訴人的近親屬為權利主體;雙主體說認為該權利歸屬于被追訴人本人及其近親屬,并認為被追訴人的權利為主權利,近親屬的權利為從權利[3]。
筆者認為談論這一問題應放到中國語境下,在我國,無論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均將當事人或者被追訴人排除在證人資格之外,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是單獨的法定證據種類,與證人證言截然不同。行使親屬拒證權的邏輯前提是,拒證權人需具備證人資格,不具有證人資格,那么當事人不享有拒證權。從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角度考慮,若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能夠做自己案件的證人,那么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實踐中其都存在被強迫自證其罪的風險。而且親屬拒證權的目的是通過免除親屬的強制作證義務來避免親屬被迫做出對被追訴人不利的證言,從而避免親自將自己的親人送上被告席,也避免被追訴人的親屬遭受精神上和倫理上的折磨,進而維護親情倫常關系和家庭和諧。權利作為一種行為自由,意味著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行使。而任何一種關系都是相互的,對于親屬而言,其行使親屬拒證權的前提是其與被追訴人之間的親屬關系仍然值得去維護,而一旦二者之間仍有血緣關系只表象但已無親情之實質,那么親屬就可以放棄行使。而一旦將親屬拒證權賦予被追訴人,那么任何一個正常思維的被追訴人都會行使這項權利,這也就意味著親屬將被迫維持這種已經名存實亡的親屬關系,這也違背了一項權利的行使止于他人權利的邊界這樣一個公認的權利限制原則。另外,當被害人是被追訴人的近親屬時其是否享有親屬拒證權?當犯罪發生在熟人之間時,在我國法律語境下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只能是當事人而不能是證人,其對案件情況的描述是被害人陳述。如果是自訴類犯罪,被害人為了維護家庭關系可以通過不予告訴的方式實現維護家庭關系的目的,親屬拒證權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公訴類案件中,被害人也可以通過做出對被追訴人有利的陳述來達到與親屬拒證權一樣的效果,畢竟司法機關要尊重被害人陳述的自愿性,因此,當親屬成為被害人時,無需單獨賦予其親屬拒證權。至于親屬拒證權中親屬的主體范圍,筆者認為,應從我國家庭結構的實際情況出發,也要兼顧城鄉差異和社會可接受度,立法可將同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和外孫子女也納入親屬拒證權的主體范圍。
(二)親屬拒證權的權利內容
親屬拒證權至少應包括兩方面內容:第一方面,權利人可自主決定是否行使拒證權;第二方面,權利人仍可以辯方證人的身份出庭做證。
首先,任何一種類型關系均具有相互性,其關系主體需為復數,只有一方主體無法建立關系。因此,任何一種類型的關系的維護,需要雙方均認同他們之間的關系,或者說該關系的存在對其有意義有價值。親屬關系更是如此,而親屬拒證權作為一種以維系親情倫常為目的的權利設計,其更應該尊重權利人的主觀意愿,因此,應賦予權利人以選擇權,由其自主決定是否行使該權利,當權利人認為該親情關系的維系已無必要時,可主動放棄該權利的行使。其次,從權利的屬性上看,其作為一種行為自由,本身就意味著權利人享有主動選擇的空間,意味著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行使,因此,應賦予權利人以選擇權。此外,只有強迫親屬所做的對被追訴人不利的證言即控方證言才會對親情關系造成破壞,也才會違背親屬的主觀意愿,而親屬多數情況下會積極主動地做有利于被追訴人的即辯方證言,這不僅不會違背親屬的主觀意愿而且有利于實現親屬拒證權的設立目的。親屬拒證權本質上是禁止強迫親屬做控方證人,即拒證權實際上是指不利證言的拒證權,因此,權利人仍可以自愿選擇以辯方證人的身份出庭作證。
(三)親屬拒證權的權利邊界
親屬拒證權的設立本質上是兩種價值衡量取舍的結果。當出現親屬拒證權的行使將危及更大的價值這種情況時,應將親屬拒證權的行使排除在外。筆者認為,在以下兩種情形中,親屬拒證權應被禁止行使:第一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國防安全的犯罪不得適用。根據價值位階原則來看,國家法益高于一切,社會法益又高于個人法益。這種情況下,發現真相、懲罰犯罪的需求更為迫切,被追訴人與親屬間的私情理應讓位于公共的安全與幸福。第二是當犯罪發生在親屬之間時不得適用。前已述及,親屬拒證權的設立目的是通過免除親屬的強制做證義務來避免親屬被迫做出對被追訴人不利的證言,進而維護親情倫常關系和家庭和諧。由于親屬之間的犯罪行為嚴重傷害了彼此的感情,違背了人倫綱常,那么就意味著維護親屬關系的必要性已經喪失,其與發現真相之間的價值沖突自然就不復存在。
(四)親屬拒證權的程序保障
無救濟則無權利,任何權利如果缺乏必要而完備的保障手段就難以得到有效的實現。親屬拒證權是一項貫穿于偵查、起訴、審判這一刑事訴訟全流程的權利,而權利人行使權利的前提是知曉該權利的存在,因此,在不同的訴訟階段,偵查、起訴和審判機關在詢問親屬證人時應分別事先告知其具有拒證權。上述機關若為事先告知,那么其從親屬證人處獲得的對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不利證言當然無效,且不得作為采取強制措施、提請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定罪判刑的根據。相應地,親屬證人應向上述機關提供能夠證明其具備行使拒證權的法定資格的材料,其是否具備親屬拒證權最終應在庭前會議或者開庭時由法官調查清楚后做出最終認定。而且對于親屬證人放棄行使拒證權的選擇,也應有法官在庭前會議或者開庭時對于其放棄行使的自愿性、真實性、明知性進行審查認定。防止偵查和起訴機關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追訴犯罪而強迫親屬證人放棄拒證權。若在一審的審判階段法官未履行上述職責,導致被告人遭受不利制裁的,被告人可以程序違法為由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可通過撤銷原判實現對程序性違法行為的程序性制裁,進而切實保障親屬拒證權從“規范權利”轉變為“實在權利”。
(五)親屬拒證權的立法完善
盡管2012年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賦予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與子女免于強制出庭的權利,但這距離真正完整意義上的親屬拒證權相距甚遠。首先,該條款所確立的親屬范圍過窄;其次,并未完全免除近親屬的強制作證義務。盡管該條款的目的是維系人倫親情和家庭關系的和諧,但由于中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實際上奉行著一種被陳瑞華教授所定義為“以案卷筆錄為中心”的裁判模式,即法官普遍通過閱讀檢察機關移送的案卷筆錄來展開庭前準備活動,對于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詞證據,普遍通過宣讀案卷筆錄的方式進行法庭調查,普遍通過援引偵查人員所制作的案卷筆錄來做出裁決[4]。因此即使親屬證人不出庭,但其庭外所做的對被告人不利的證言仍會通過其他方式進入法庭,由于我國尚未確立傳聞證據規則,這實際上變相剝奪了被告人的質證權,對于被告人而言得不償失。因此,下一步的《刑事訴訟法》修改一定要汲取前述教訓。在接下來的立法中,首先,應明確規定親屬證人的拒證權,免除近親屬免予強制作證義務;其次,明確規定該拒證權貫穿于偵查、起訴、審判這一刑事訴訟的全流程;另外,明確規定偵查、起訴、審判機關詢問證人前的親屬拒證權告知義務,并規定未履行告知義務獲取的親屬證人不利證言一律無效;最后,針對剝奪親屬證人拒證權的程序違法行為,立法賦予被告人以上訴權,通過程序性制裁撤銷對被告人的不利判決。
結束語
綜上所述,親屬拒證權在刑事訴訟中的引入契合國人的情感認同,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和規范依據,也符合國際潮流,同時也與國內刑事訴訟保障人權這一改革趨勢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參考文獻
[1]陳光中.刑訴法修改中的幾個重點問題[N].人民法院報,2011-08-24(6).
[2]張本順.“安提戈涅之怨”與中國親屬拒證權的缺失:法的人倫精神解讀[J].法治與社會發展,2008(71):75.
[3]覃冠文.親屬免證:究竟是誰的權利:以親屬免證特權權屬為基點的展開[J].政治與法律,2016(1):154.
[4]陳瑞華.刑事訴訟的中國模式(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張佳翔(1992— ),男,漢族,河南平頂山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訴訟法學。
黃鈺(1996— ),女,漢族,河南周口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在讀碩士。
研究方向:訴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