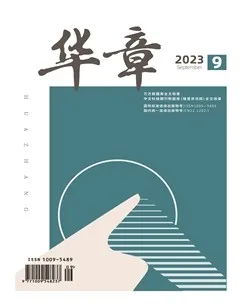芻議法律的正確性宣稱與法律權威
[摘 要]阿列克西通過對“正確性宣稱論據”做分析性論證,區分外在觀察者觀點和內在參與者觀點,論證法律必然做出正確性宣稱;用衍生出的不正義論據和原則論據證明正確性宣稱與道德之間的必然聯系。法律的正確性宣稱不僅沉重地打擊了法實證主義的基本立場,其內在要求也為法律權威的正當性提供理性基礎。
[關鍵詞]正確性宣稱;非實證主義;法律權威
羅伯特·阿列克西是德國法哲學家,其主張的法律與道德之間不可分的聯結命題展現了他作為一名非實證主義者的姿態。當時的德國通常遵循規范性論證思路,用法的合目的性、法的安定性作為評價標準來分析實證主義的分離命題,但阿列克西另辟蹊徑,將論證的結果導向了對分離命題的否定,提出聯結命題,這一論證的核心就是作為分析性論證的“正確性宣稱論據”[1]。正確性宣稱是阿列克西對實證主義進攻的重要“武器”,也有學者并不贊成該觀點,如德沃金認為,某個法律體系的代表是否提出某種宣稱是屬于經驗事實的問題,而非必然性的問題[2]。本文就此探討法律是否必然做出正確性宣稱、法律的正確性宣稱與道德之間的聯系以及法律的正確性宣稱與法律權威的正當性的關系。
一、正確性宣稱的證成
“正確性宣稱論據”是阿列克西證成聯結命題與瓦解分離命題的核心論據,它指向內容的正確性宣稱與“法律是什么”,同時通過區分觀察者角度和參與者角度,論證正確性宣稱與法律體系之間的必然聯系。
(一)正確性宣稱與兩個命題
正確性宣稱是聯結命題與分離命題相區別的要素,也是非實證主義主張法律概念區別于實證主義立場的決定內容。阿列克西認為法概念的三要素應是:權威制定性、社會實效性、內容正確性。內容正確性涉及規范是否在道德上被正當化,即法律是否提出“正確性宣稱”。如果法律并未提出正確性宣稱,那法律概念只包括權威制定性和社會實效性,那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命題則成立;如果法律概念除了包括前兩者,還必然做出內容正確性宣稱,那法律的效力就依賴于法律是否做出了前述宣稱。而且,如果這種內容正確性宣稱必然包含道德因素,那么法律與道德必然存在關聯。阿列克西的論證思路是:第一步論證法律必然做出內容的正確性宣稱;第二步是這種內容的正確性宣稱必然包含道德因素,證成法律與道德之間的必然聯系。
(二)正確性宣稱與觀察者觀點
觀察者觀點的人不去追問在特定的法律體系中什么才是正確的決定,而是追問在特定的法律體系中實際上是如何做出決定的。列舉個別規范“根據德國法,A被剝奪國籍”,外在觀察者考慮的則是某項規范文本是否符合被權威制定的、具有社會實效的法律體系所確立的效力標準,依據有效的規范文本得出的判決與依據法律所做的判斷應該是一致的,這是分析性論證。外在觀察者提出“根據德國法的有效標準,A依據規定被剝奪了德國國籍且具有實效,但這是法律嗎?”觀察者則轉變成批評者,霍斯特認為,這種轉變并不具有保證概念清晰和道德中立的合目的性,這是規范性論證[3]。從考察個別規范兩種論證思路所導出的結論來看,外在觀察者在使用“法律”時并未關注內容的正確性,沒有混雜道德因素,表面實證主義的分離命題對于外在觀察者是正確的。個別規范并不當然適用整個法律體系,因此還需追問:整個法律體系與道德之間是否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聯系。阿列克西列舉了無意義的秩序、掠奪或強盜的秩序以及統治秩序。前兩種秩序沒有一致性目標,不存在一般性的規范。為使長期掠奪成為“正當的”,通常會發展成統治者,掠奪秩序由此成為統治秩序。統治秩序與前兩種秩序的本質區別在于統治秩序提出了正確性宣稱。
總而言之,站在外在觀察者的角度,對于單個規范,正確性宣稱的缺乏最多導致它們出現法律瑕疵,而不會影響它的法律本性。與此不同,對于整個規范體系而言,如果完全沒有做出正確性宣稱,則不能稱之為法律體系。如果做出了正確性宣稱但未能滿足這一宣稱,這一法律體系最多是存在法律瑕疵的。
(三)正確性宣稱與參與者觀點
如前所述,從觀察者的觀點來看,分離命題只有在極端情形下會因為完全不提出正確性宣稱才會碰壁,然而在觀察者觀點中處于邊緣的正確性宣稱,在參與者觀點中轉而居于核心。立足參與者觀點考慮某個法律體系關于“什么是在這個法律體系中被要求、禁止、允許與授權者”。為了證成法律與正確性宣稱的必然聯系,阿列克西進行了舉例:
假設X國的《憲法》規定少數人可以統治多數人并規定“X是一個主權獨立、聯邦制且不正義的共和國”,這一條款顯然存在某種瑕疵。第一種解釋認為“不正義”這一措辭不具有合目的性,存在的僅僅是技術瑕疵。那也可以說制憲者也許確實要建立一個不正義的國家,但卻誤用了“共和國”這種表達,因而存在技術瑕疵的倒可能是“共和國”這一措辭;第二種解釋認為存在道德瑕疵。但是如果將存在實質道德瑕疵的條款(如種族清洗)置換此處的“不正義”,條款的意義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第三種解釋認為存在成規性的瑕疵。但是這一條款侵犯的不僅僅是制憲的習慣,還包括制憲實踐的核心要素——這一點可以通過憲法中的冗余條款表現出來:“X是一個正義的國家。[4]”阿列克西認為真正存在的是概念瑕疵,即任何宣稱必然隱含著對被宣稱行為的肯定,這種隱含的肯定不能與宣稱的外在肯定相矛盾。在此處的例子中,內容正確性宣稱也就意味著對正義的宣稱:制憲行為隱含著對制憲行為之正義性的肯定,但這與制憲者外在的宣稱“X是一個不正義的國家”發生了矛盾,它的荒謬來自于立憲所隱含的主張(即憲法是正義的)與公然表述的話語(即它是不正義的)之間的矛盾。為了避免這種矛盾,就不得不承認正確性宣稱與制憲行為存在著必然關聯。這一分析性論證表明,正確性宣稱必然或隱或顯地存在于法律之中,法律體系的參與者必然在任何層面上都或顯或隱地做出正確性宣稱。
二、正確性宣稱與道德的必然關聯
法必然提出正確性宣稱,這自然還不足以證明立法與道德之間的必然關聯。要做到這一點,還要說明法所提出的正確性宣稱的內容必然與道德相關。實證主義者反駁法律和道德的聯系可能會提出:一實證主義者可以說“內容正確性宣稱”雖然是必然的,但是對“正確性宣稱”的滿足卻是偶然的。未實現正確性主張并不會導致法律性質喪失。既然認為“正確性宣稱”通常情況下只具有適格性意義,只是在極端情形下才具有區分性意義,提出了但未能滿足這種宣稱的單個規范和法律體系即使存在瑕疵,但仍然是法律;二正確性宣稱只具有微不足道的缺乏道德蘊含的內容,因而不會導致法律與道德的必然關聯。而非實證主義者需要從不正義論據和原則論據中尋求支撐。
(一)不正義論據
不正義論據是對拉德布魯赫公式的理性重構。為了捍衛拉德布魯赫公式,阿列克西提出了八個論據。拉德布魯赫公式是對法律概念的規范性論證,但該公式本身并不排斥用“正確性宣稱”來證成。這樣一來,即使是在極端不法情形下,法官也必然宣稱其判決具有可證成性,制定法的不法在于其法律本性的喪失,道德批評內涵于法律批評,法律與道德在概念上就具有了必然關聯,但同時拉德布魯赫公式只能適用于單個規范的區分性關聯,而不能適用于整個法律體系。
(二)原則論據
原則論據涉及英美實證主義的核心議題:原則在法律規范中的地位和作用。該問題起源于哈特提出的法律語音的“開放結構”以及與此相關的“自由裁量問題[5]。實證法案件不可避免地存在開放性。落入這種開放領域的裁判無法獲得實在法上之標準的支持,將其稱之為“疑難案件”。對于疑難案件,凱爾森和哈特這樣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在開放領域中法官被授以類似立法者的權力可以采納法外標準依其自由裁量創造新法。阿列克西繼承德沃金對哈特的批判,肯定法律必然包含原則并提出了“原則論據”。
原則論據主張即便是被制定且有效的法律的開放領域,法官仍然受到法律約束,確切地說是以一種確立法律與道德之間必然聯結的方式受法律所約束,其基礎就是規則和原則的區分。這意味著原則有著不同的實現程度。阿列克西借由安置命題、道德命題和正確性命題三個命題證成法律與道德上的必然關聯。在這一證明過程中可以發現,“正確性宣稱”滲透到了阿列克西論證的每一個環節,成為一種必然性要求。根據“正確性宣稱”蘊含的“可證成性宣稱”,法律原則必然經由法官對法律理由的權衡而被安置在法律體系之中,而法律原則在內容上具有道德屬性,法律就必然與有些道德存在必然關聯。最后,根據“不正義論據”和“正確性宣稱論據”的雙重限制,使得被證成的道德必然趨向于正確的
道德。
三、正確性宣稱與法律權威之思考
阿列克西從語言行動理論的分析論證得出:法律必然做出正確性宣稱;拉茲從行動理論的角度得出:法律必然做出合法性權威宣稱。兩者基于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論證形式。下文擬區分兩種宣稱的界限,闡釋正確性宣稱與法律權威的關系。
(一)正確性宣稱與合法性權威宣稱
哈特認為,法律是一種對人們行為進行指導的社會規則,因為人們總是以內省的、規范性的態度來看待法律。根據拉茲的理解,人們的行動總是基于各種不同的理由,并在相互沖突的理由之間進行衡量。那么法律規范與理由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可解釋關系呢?如果說法律規范也是以理由的方式引導人的行為,那么其規范性又當如何解釋?拉茲認為,人們直接遵循的行動理由以一階理由的方式發揮作用,人們遵循某一理由而不是另外的理由取決于他對不同一階理由的權衡;規范則是以二階理由的方式發揮作用,規范在其效力范圍內排除了人們對一階理由的權衡,但它本身并不提供新的一階理由。規范具有的“排除一階理由的考量”是一種“排除性理由”。因此,一個規范體系以及它所認可的權力都會直接或間接規制某個行為,宣稱具有規制的權威。法律作為一種規范體系,宣稱具有至高無上的性質,它對所有的其他規范體系的建立和適用具有權威。拉茲的合法性權威宣稱是解決法律規范性問題,將法律看作是一種排除性理由;而阿列克西的內容正確性宣稱是找尋法律概念的定義要素,論據建立在分析性問題上。兩種宣稱是站在不同角度對問題思考的結果。
(二)正確性宣稱是法律權威正當性的理論權威
權威可以分為正當性權威和事實上的權威。事實上的權威一方面主張自己是具有正當性的或者被認為具有正當性,另一方面,它可以有效地把自己的意志施加到對之主張權威的受眾身上,但事實上的權威并不必然擁有正當性。正當性權威既可以是實踐權威,也可以是理論權威,還可以兩者都是。具有實踐權威的人或機構的命令可以構成它的受眾的行動理由,而理論權威給出的建議則構成認可其權威性的受眾相信某種事的理由[6]。拉茲主張合法性權威是法律的本質特征,如果法律是實施某一行為和排除相沖突因素的理由,而這一理由又是一個有效的或正當的理由,法律則擁有合法性權威[7]。從其思路可知,合法性權威宣稱應是屬于正當性權威的實踐權威,而正確性宣稱是針對法律內容提出的適格性要求,筆者認為,正確性宣稱為法律提供正當性的理論權威。
德沃金用權利理論來闡釋道德與法律之間必然存在聯系,法律的正當性根植于法律的道德權威。這種道德權威與正確性宣稱存在關聯和區分。當我們說正確性宣稱是法律權威是正當性基礎時,是處于立法階段的語境中;而當我們說法律有權威時,是處在法律實施包括法律適用、執行和守法的語境中。立法旨在創設法律的階段,道德規則對現實行為沒有任何約束力,談不上權威問題,而且它需要通過法定程序和方式轉變為法律規范,因而不存在成為法律權威的問題;在法律被創設之后,法律進入實施階段,產生現實的效力,在這一階段的部分道德規則本身會成為法律規范。正確性宣稱與道德必然有關聯,內容的正確性宣稱要求與道德保持一致,但又與一般的道德權威保持距離,正確性宣稱屬于法律權威的范疇。任何意向性行動都包含符合意圖的一般性宣稱,但法律做出的正確性宣稱與一般的言語行動相比,它還意味著對真實與客觀性的宣稱。因此,正確性宣稱針對法律內容提出符合道德的適格性要求,是法律權威正當性的理論基礎。
結束語
法律的正確性宣稱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法概念和法效力的理解。法律除了權威制定性和社會實效性這種事實面向以外,還具有正確性宣稱這種理性面向,這也是阿列克西提出的法的二階性質。一階正確性涉及正義本身,二階正確性不僅涉及正義,也涉及實證性。正義代表著法的理想或批判性的維度,實證性代表著它的現實、事實或制度性的維度。正確性宣稱作為二階宣稱,聯結了法的現實維度和理想維度。
參考文獻
[1]阿列克西.法概念與法效力[M].王鵬翔,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2]德沃金.認證對待權利[M].信春鷹,吳玉章,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3]馮威.法律的正確性宣稱:Alexy對法律實證主義的回應[J].朝陽法律評論,2010(1):122-141.
[4]拉德布魯赫,舒國瀅.法律的不法與超法律的法(1946年)[J].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1(00):429-443,476.
[5]哈特.法律的概念[M].許家馨,李冠宜,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拉茲,劉葉深.權威、法律和道德[J].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7,12(2):44-72+293.
[7]拉茲.法律的權威[M].朱峰,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夏文娟(2000— ),女,漢族,湖南岳陽人,湘潭大學法學院,在讀碩士。
研究方向:法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