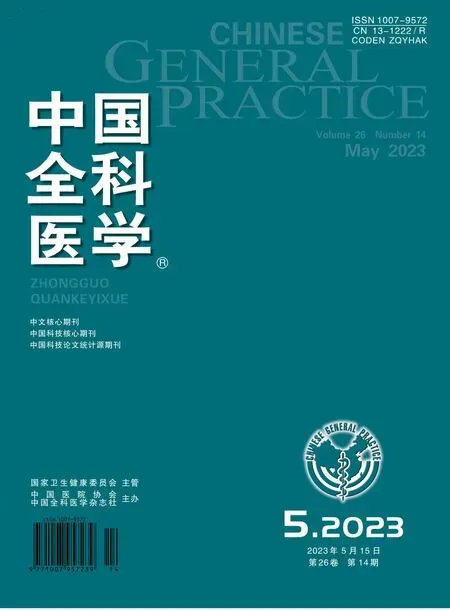基于十年隨訪的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聚集與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關系的隊列研究
馬萬瑞,馬乾鳳,吳競捷,王立群,王志忠,5*
心血管代謝性共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CMD)是指同一個體患有2種或2種以上的心血管代謝性疾病,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等心血管代謝性疾病已成為CMD主要共病模式之一[1],并占全球成年人疾病負擔的50%以上[2]。研究顯示,與60歲時沒有任何CMD的個體比較,患有1、2、3種CMD的個體預期壽命分別縮短6年、12年和15年[1]。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聚集(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 cluster,CRFC)指個體暴露2種及以上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如肥胖、血脂異常、糖耐量異常、血壓升高等,是導致CMD的重要原因。2015年我國約有80.8%的成年人有1種及以上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約54%的成年人存在CRFC[3]。國內有關CRF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行病學分布特征描述[3-4],有關CRFC與社區老年人群死亡風險的研究報道尚不充分,既往研究納入的心血管代謝性指標的數量有限,已不適用于健康大數據背景下精準醫學的需要。本研究通過一項隨訪10年的社區55歲及以上人群隊列資料,分析CRFC與≥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的關聯,為開展≥55歲人群的社區保健和主動應對老齡化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典型抽樣法,于2011年9—11月選取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和銀川市5個老年人口比例相對較高的社區,對符合納入標準的社區≥55歲人群開展一般情況問卷調查、體格檢查、超聲檢查和實驗室檢查[5]。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年齡≥55歲且每年在目標社區居住超過6個月的戶籍居民,知情同意后自愿參加。排除標準:(1)手術恢復期患者;(2)癱瘓臥床者;(3)嚴重精神癥狀者;(4)視力及聽力障礙者;(5)惡性腫瘤患者及癡呆患者。共有1 046例研究對象納入研究。本研究經寧夏醫科大學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寧醫倫字2018-115號),研究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1.2.1 基線調查 (1)問卷調查:收集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包括性別、年齡、民族、文化程度、是否獨居、是否再婚、是否吸煙(吸煙定義為過去一年中有持續2個月的時間,每周至少吸1次煙)、是否飲酒(飲酒定義為過去一年中平均每個月至少飲酒1次)。(2)體格檢查:由經過統一培訓的醫務人員測量研究對象的身高、體質量、腰圍、血壓,其中血壓連續測量3次,取其平均值。(3)超聲檢查:由超聲科專科醫師使用EMP-800型B超在調查現場完成。(4)實驗室檢查:采集研究對象前1 d禁食高脂食物、隔夜禁食8 h以上的靜脈血3 ml,并于抽血后2 h內送至實驗室。采用生化檢測試劑盒(柏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MOL-3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上海艾諾公司)檢測生化指標,包括:空腹血糖(FPG)、總膽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血尿酸(SUA)。
1.2.2 CRFC評價 本研究基線納入了9項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中心性肥胖、4項血脂異常疾病(高膽固醇血癥、高三酰甘油血癥、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癥、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高血壓、糖尿病、高尿酸血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具體診斷標準如下:(1)中心性肥胖,依照2005年國際糖尿病聯盟發布的中心性肥胖的定義,成年男性腰圍≥90 cm、成年女性腰圍≥80 cm[6];(2)4項血脂異常疾病,參照《血脂異常基層診療指南(2019年)》[7],①高膽固醇血癥:TC≥6.2 mmol/L;②高三酰甘油血癥:TG≥2.3 mmol/L;③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癥:LDL-C≥4.1 mmol/L;④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HDL-C<1.0 mmol/L;(3)高血壓,參照《中國老年高血壓管理指南2019》[8],在未使用降壓藥物的情況下測量血壓,收縮壓(SBP)≥140 mm Hg(1 mm 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DBP)≥90 mm Hg,或既往診斷為高血壓,目前正在口服降壓藥物治療。(4)糖尿病,參照《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9],FPG≥7.0 mmol/L,或既往診斷為2型糖尿病,目前正在口服藥物治療;(5)高尿酸血癥,參照《中國高尿酸血癥與痛風診療指南(2019)》[10],成年人空腹SUA>420 μmol/L(不分性別);(6)NAFLD,參照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學組修訂的NAFLD超聲診斷學標準[11],具備以下≥2項者:①肝臟近場回聲(強于腎臟)增強;②肝內管道結構顯示不清;③肝臟遠場回聲逐漸衰減。采用心血管代謝性因子危險評分評價因素聚集(或共病)效應,根據COLLINS等[12]的建議,首先控制一般情況變量后,通過構建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估計各個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的回歸系數β。然后以回歸系數β為權重將所有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的評分相加得出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總評分,其評分越高提示CRFC越嚴重,評分=中心性肥胖×0.257+高膽固醇血癥×0.146+高三酰甘油血癥×(-0.193)+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癥×0.132+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0.062)+高血壓×0.129+糖尿病×0.071+高尿酸血癥×0.486+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0.440)。
1.2.3 研究對象的隨訪和分組 本隊列隨訪起始時間為2011年9月,隨訪截止時間為2021年7月,隨訪終點事件為死亡。項目組分別于2017年、2019年和2021年完成了三輪入戶隨訪調查,對發現的死亡案例進行記錄同時通過身份證號和姓名等信息與國家死因監測信息庫比對,核實和補充死亡案例,累計完成了924例的隨訪,失訪率為11.7%。所有數據由項目組專人負責原始信息的保存和數據分析階段研究對象身份識別信息的隱匿工作。根據年齡分為55~64歲組(459例)和≥65歲組(587例)。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研究對象的隨訪時間采用精確法計算,以月為單位。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不同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危險總評分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的生存曲線,差異比較采用Log-rank檢驗;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全因死亡風險的影響因素,首先構建一般情況變量與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控制一般情況變量后,分別將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危險總評分、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危險總評分分層(劑量效應分析采用四分位數分為三組:<P50組,P50~P75組,>P75組)帶入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計算報告風險比(hazard ratio,HR)及其95%置信區間(95%CI),采用直接進入法篩選變量;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一般情況 研究對象年齡55~88歲,平均年齡(66.4±6.6)歲,截止隨訪結束,共觀察到了106例死亡案例,10年累計死亡率為10.13%。55~64歲組性別、民族、獨居情況、吸煙情況、高三酰甘油血癥患病情況、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患病情況、糖尿病患病情況、高尿酸血癥患病情況、NAFLD患病情況、隨訪結局與≥65歲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文化程度、再婚情況、飲酒情況、中心性肥胖情況、高膽固醇血癥、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癥、高血壓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不同年齡組一般情況、CRFC和全因死亡率比較〔n(%)〕Table 1 The socio-dem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 cluster,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participants by age group
2.2 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影響因素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 以是否死亡為因變量,以年齡、性別、民族、文化程度、獨居、再婚、吸煙、飲酒、中心性肥胖、高膽固醇血癥、高三酰甘油血癥、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癥、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高血壓、糖尿病、高尿酸血癥、NAFLD患病情況為自變量(賦值情況見表2),進行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結果提示,年齡、性別、獨居、文化程度可能是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3。控制了一般情況(性別、年齡、民族、文化程度、獨居、再婚、吸煙、飲酒)后,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發現,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總評分可能是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的影響因素〔HR=3.04,95%CI(1.55,5.97),P=0.001〕,且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總評分越高全因死亡風險越高,>P75組全因死亡風險高于<P50組〔HR=2.02,95%CI(1.16,3.50),P=0.013〕,見表4;如圖1所示,隨著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總評分的增加,個體預期中位生存時間縮短,>P75組累積生存率低于P50~P75組(χ2=4.259,P=0.039)和<P50評分組(χ2=12.455,P<0.00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表2 全因死亡風險影響因素的Cox回歸分析變量賦值表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table for associated factors of all-cause mortality risk incorporated in the Cox regression model

表3 全因死亡風險影響因素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risk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ssociated factors of of all-cause mortality risk

表4 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及其聚集與全因死亡風險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Table 4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risk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ssociation of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and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 cluster with all-cause mortality risk
2.3 不同年齡組社區≥55歲人群死亡風險影響因素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 以年齡組分層,結果發現控制了一般情況變量后,只有≥65歲年齡組是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的危險因素〔HR=2.79,95%CI(1.36,5.74),P=0.005〕,且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危險總評分越高全因死亡風險亦越高,>P75評分組全因死亡風險高于<P50組〔HR=1.83,95%CI(1.02,3.28),P=0.042〕,見表5。

表5 不同年齡組社區老年人全因死亡風險影響因素的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Table 5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risk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allcause mortality risk and the total cardiometabolic risk score stratified by age

圖1 <P50組、P50~P75組、>P75組人群全因死亡的生存曲線Figure 1 The survival curve for all-cause mortality risk for tertiles of the total cardiometabolic risk score
3 討論
全球疾病負擔研究顯示,心血管疾病是全球人口的主要的致殘和死亡原因[13]。我國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仍處于上升階段,已成為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14]。血壓、體質指數、血糖、血脂等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相互作用且具有共同的致病通路[15],然而,單一的因素與老年人群死亡風險的關聯在早期不容易被發現[16],探討多個危險因素的綜合效應與人群健康的關系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隨著疾病防控關口的前移和老年人存在一種或多種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異常的比例增加,研究CRFC與不良健康結局的關聯具有重要意義。
既往研究納入指標多以中心性肥胖、TG升高、HDL-C降低、血壓升高、血糖升高作為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3-4],而脂肪肝、高SUA等重要的心血管代謝性指標未被重視[10,17]。研究提示高尿酸血癥和NAFLD是重要的代謝性紊亂組分,與人群心血管代謝性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本研究基于既往研究構建的CRFC模型[18],并計算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危險總評分以評價心血管代謝性指標功能紊亂對健康的綜合效應,結果發現在單獨的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與全因死亡風險關聯不顯著的情況下,控制了性別、民族、文化程度等一般人口學變量和吸煙、飲酒等危險行為因素后,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危險總評分是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的影響因素,且存在劑量-效應關系,即危險因素危險總評分越高其全因死亡風險越高。基于現代全人全生命周期健康保健理念,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之間是相互作用、逐漸進展的,因此采用CRFC評價社區≥55歲人群健康風險更敏感,有助于開展社區早死高危人群的早期識別和社區綜合干預,進而降低死亡風險、延長壽命。
在不同年齡人群中CRFC與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存在差異,≥65歲組的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總評分是社區老年人全因死亡風險的影響因素,且危險評分越高死亡風險亦越高,但在55~64歲組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總評分不是社區老年人全因死亡風險的影響因素,可能與該組本身死亡風險低,樣本量不足有關,尚需進一步延長隨訪觀察時間驗證。本研究亦發現性別、獨居、文化程度是社區老人全因死亡風險的影響因素。國外大樣本隊列研究提示獨居老年人死亡風險增加20%[19],文化程度與大多數主要死亡原因呈負相關[20],男性的預期壽命持續低于女性[21]。因此在開展社區老年人保健工作中,應結合人群一般人口學特征,進行精準預防,有望提高干預的效率。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首先,受樣本量的影響,研究沒有充分考慮具體的死因風險,需要在今后的大樣本研究中驗證。其次,研究未收集研究對象的飲食、運動、藥物使用等情況,目前尚無法排除其對各項代謝指標的影響。最后,未能發現年齡55~64歲組與社區老年人全因死亡存在統計學關聯,尚需繼續隨訪觀察驗證。
綜上所述,單一的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對社區≥55歲人群的死亡風險的影響是有限的,但多項風險因素綜合作用于同一個體則表現出明顯的風險累加效應,CRFC可能是社區≥55歲人群全因死亡風險的危險因素,及時識別心血管代謝性危險因素并給予早期干預,可能對降低死亡風險、延長人群壽命有一定的意義,這一發現對于利用個體健康大數據開展高危個體的早期識別也具有重要意義,并為老年人早死的精準預防提供了參考。
志謝:特別感謝寧夏回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所在資料收集過程中提供的幫助。
作者貢獻:馬萬瑞、王志忠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數據分析、文章的撰寫;馬乾鳳、王立群負責數據的整理與核查;吳競捷負責文獻資料的收集與整理;王志忠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