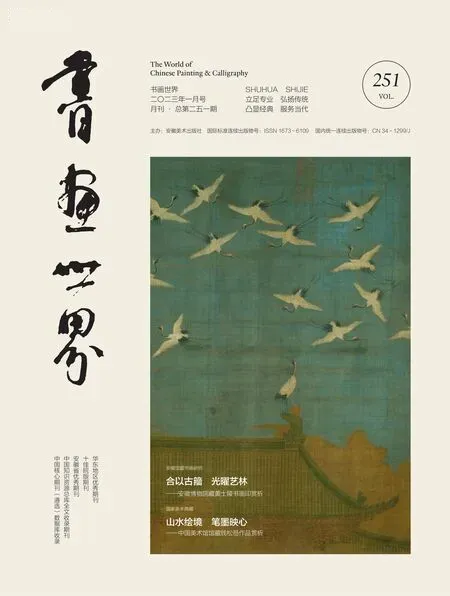合以古籀 光曜藝林—安徽博物院藏黃士陵書畫印賞析
文_季永
安徽博物院
回望百年前的中國晚清書畫家群體,黃士陵(圖1)如一顆明星熠熠生輝。他工篆書,善治印,精考據,涉丹青,藝術創作全面多能,尤以開創篆刻“黟山派”而馳譽嶺南,蜚聲海外。與其相仿的人物大略只有海上吳昌碩可為頡頏,而考慮到吳昌碩的藝術成熟期已是民國時期,則黃士陵可稱明清流派印學的最后一位大師。

圖1 黃士陵像
黃士陵一生勤奮,刀筆耕耘,治印萬余方,書畫作品傳世亦甚夥。目前其傳世作品的收藏以安徽、廣東、上海三地為大宗。安徽博物院現收藏有黃士陵書畫印等各類相關文物近百件,這些藏品多得自其故鄉黃山,主要為其后人及親友舊藏,可謂傳承有緒,也為我們學習和研究黃士陵藝術提供了珍貴而可信的資料。
一、蒙養徽黟 聲隆嶺南
黃士陵(1849—1909)①,字牧甫、穆甫,別號倦叟、倦游窠主等,安徽黟縣西武鄉黃村人。黟縣為徽州文化的發祥地之一,而黃村亦為詩書之鄉。黃士陵的父親黃德華能詩文、擅小篆,通文字訓詁之學,有《歸田錄》《竹瑞堂詩鈔》等傳世。黃士陵幼承家學,八九歲即可操刀篆印,名聞鄉里。
清同治二年(1863),因太平軍兵燹所及,黃士陵家境變故。后其父母俱喪,黃士陵遂離家至江西南昌,在胞弟厚甫所開的“澄秋館”照相館以刻印賣字為生。黃士陵曾在其“末伎游食之民”印邊款中,記錄了這段心路歷程:“陵少,遭寇擾,未嘗學問。既壯,失怙恃,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計,溷跡市井十余年,旋復失業,湖海飄零,借茲末伎以糊其口。今老矣,將抱此以終矣。刻是印以志愧焉。”后因為南昌一書店所寫書簽,被江西學政汪鳴鑾賞識,漸與名流交游切磋,書、印遂得以大進。②其間,29歲的黃士陵創作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印譜,已充分顯現出其師法皖、浙兩派篆刻的扎實功力和探索多變印式的創作才情。
清光緒八年(1882),黃士陵移居廣州,開始了最重要的人生階段。他先后結識了志銳、沈澤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一大批社會名流和文人學者,交游益廣,眼界益寬。后又得志銳舉薦和資助,于光緒十一年(1885)入北京國子監,問學于王懿榮、盛昱、蔡賡年等學者大家。其間他受命摹宋本《石鼓文》,校改石經,研求周金漢石,為日后藝術創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③清光緒十三年(1887),黃士陵南歸廣州,入時任廣東巡撫吳大澂幕府。其間二人切磋金石,并編輯拓制《十六金符齋印譜》。清光緒十六年(1890)應張之洞邀請入廣雅書局任校對,凡廣雅書局所刻書籍,其扉頁的篆書多為黃士陵手筆。居粵十數載,黃士陵在書法篆刻上溯源周秦,博涉諸家,藝術成就漸臻化境。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黃士陵作別廣東歸黟。兩年之后,應端方邀請攜子黃少牧赴武昌。其間協助端方編輯《匋齋吉金錄》《匋齋藏石記》等圖書,得到端方的贊賞。光緒二十九年(1903),復歸黟縣居“舊德鄰屋”直至辭世。斯時的黃士陵已名滿海內,由他開創的“黟山派”篆刻也成為晚清印壇的一大宗派。
二、高古雅麗 書精篆籀
黃士陵在書畫印諸多方面均有突破時代的成就,而奠定這些成就的基石是他的書法。
安徽博物院收藏的黃士陵最早的書法墨跡為書于清同治十年(1871)的行書冊頁。這件作品與署名“椒園”的青綠山水《小桃源》冊頁(圖2、圖3)合裝一卷。黟縣四面環山,自古有“桃花源里人家”之譽,李白游蹤至此,曾寫下《小桃源》詩。畫作落款“椒園”舊題,椒園其人未詳,或為擅長青綠山水的晚清吳門畫家顧逵(號椒園)。黃士陵應是根據此圖而題詩作跋,所書兩首五言古體詩作者不詳,皆為詠桃花源之主題。從書法看,取法何紹基為多,亦流露出后來瘦硬生拙的筆意。落款署“九千五百九十三字齋主人”,可見此時的黃士陵對《說文解字》之學的癡迷。

圖2 椒園 小桃源

圖3 黃士陵 《小桃源》題跋
晚清時期金石碑學風靡一時,黃士陵生逢其時,于篆書用功最深。他早年師法鄧派,亦受到吳熙載、趙之謙、楊沂孫、徐三庚諸家的影響。作品形式以對聯、條屏居多,亦體現出他鬻字兼而酬贈的筆墨生活。
《隨群欣樂篆書七言聯》(圖4)乃《蘭亭序》集字聯,為黃士陵辛巳年(1881)秋八月所書,可見他此時的篆書以鄧石如為基兼取趙之謙的傾向。筆法中的方折處理,似乎是反向借鑒了篆刻的技法,體現出其早年融通求變的創作態度。斯時他尚客居南昌,即將于歲末赴廣東,書、印俱已頗具功力。

圖4 黃士陵 隨群欣樂篆書七言聯
《芝草水流篆書十二言聯》(圖5)書于丁亥年(1887)秋七月,上款“皖生”即黃廷珍(字皖生)為黃士陵族侄,黃士陵先后為其治印兩方。此時黃士陵自北京國子監返廣州入吳大澂幕,其篆法受到《石鼓文》的影響,結字變長為方,而筆法則顯然帶有吳大澂篆書的筆意。這也宣告了他從鄧派小篆而上窺周秦的蛻變。

圖5 黃士陵 芝草水流篆書十二言聯
光緒二十八年(1902),歸鄉三載的黃士陵應舊交、時任湖廣總督端方的邀請,赴武昌協助整理編輯《匋齋藏器目》。半生與吳大澂、端方等收藏大家的交游切磋,讓黃士陵獲觀了大量的金石文字資料,使其在技法、學問、眼界等方面均不斷突破。《水禽河鯉篆書七言聯》(圖6)即為這年的作品,篆法純以金文為之,用筆精健渾穆,古意盎然。黃士陵此時的篆書已熔鑄篆籀,功力爐火純青,一掃清代以來篆書家以小篆法寫大篆的積習,達到了超越時賢的境界。

圖6 黃士陵 水禽河鯉篆書七言聯
《夏小正篆書八條屏》(圖7)為黃士陵晚年篆書巨制。這件作品創作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是時他已再度歸里四年,而距辭世僅兩年。《夏小正》相傳為夏朝記錄農事的歷書,書寫此文也透露出晚年的黃士陵留意農耕、寄興筆墨的心跡。吳大澂亦有《夏小正》篆書墨跡傳世,我們將吳、黃兩家墨跡并觀,明顯看出黃士陵水準高出一籌。

圖7 黃士陵 夏小正篆書八條屏
黃士陵楷、行書作品非常少見,我們只能從其傳世作品的小楷題跋以及尺牘中略窺端倪。他的楷、行書方峻瘦硬,但不是取法歐陽詢那樣的唐楷,而是借鑒唐以前鐫刻金石的古法,顯得瘦硬整飭,不同流俗。(圖8)

圖8 黃士陵 《贈子嘉周文王鼎博古圖》題畫書法
三、窮流溯源 印開宗派
黃士陵與吳熙載、趙之謙、吳昌碩并稱晚清四大篆刻家,是中國篆刻史上開宗立派的大師級人物。他的篆刻初學鄧石如、陳鴻壽,后服膺吳熙載、趙之謙,再上探周秦,合以古籀,最終成為一代印學宗師。正如其弟子李尹桑所說:“悲庵之學在貞石,黟山之學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漢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黃士陵對沖刀的技法運用、對章法的精意安排、對篆法的廣泛取法,可謂開現代篆刻創作形式之先河,深刻影響了其后從齊白石到當下的無數印人。
安徽博物院共藏有黃士陵篆刻11方,其子黃少牧篆刻1方。這些印章年代貫穿其創作生涯,見證了黃士陵篆刻不斷蛻變的發展歷程。其中最早的印章為刻于光緒七年(1881)的“安雅”朱文印(圖9)。“安雅”兩字豎排,揖讓錯落,變化有致,可見秦詔版與漢代碑額篆書的影響。邊款云:“光緒辛巳長至,牧父作于珠江。”長至即夏至,由“作于珠江”可知是時他已至廣州。這推翻了以往印學界認為穆甫至廣州時間為光緒七年冬的說法。

圖9 黃士陵 安雅(附邊款)
在整理資料時,一方“皖生”印章(圖10)引起了我的注意,或許是因一個“皖”字。這方印章明顯取法鄧石如。邊款云:“完白山人篆刻古奧渾芒,為晉唐以來第一作手,后學者罕能追步。試一摹之,或可得其仿佛耳。穆父書倩小厓捉刀并記之。”此印未題年款,捉刀者小厓亦不知何許人,故此印雖被收錄入黃士陵印譜中,安徽博物院仍按小厓作品標注。“皖生”即上文所提到的黃廷珍,亦為黟縣黃村人,后入浙江商籍,為邑庠生,能詩詞,精中醫,愛金石書畫。《黃士陵印譜》中還收入白文“黃廷珍印”,邊款云:“擬曼生翁意為皖生研侄作,時戊寅秋七月,行六叔士陵。”兩印一朱一白,邊款風格一致,應為同時所刻。此類邊款與穆甫成熟風格不類,考慮到“皖生”印的邊款云“倩小厓捉刀”,則二印邊款或皆為小厓所刻。戊寅為光緒四年(1878),時黃士陵尚在南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印譜》即刊行此時。心經諸印惜已不存,而此二印可算作黃士陵紀年最早的印作實物了。④

圖10 黃士陵 皖生(附邊款)
安徽博物院收藏的黃士陵為李芙元所制名印一對(圖11、圖12)作于光緒辛巳年秋(1881),是時其即將從南昌赴廣州,篆刻師法吳熙載而漸成自家風格。館藏“家在黃山白岳之間”朱文印,邊款云:“鐵兄囑刻,癸丑三月,士陵。”癸丑為1913年,與舊說黃士陵去世在1908年冬相差很大。以前也有學者依此印邊款為證,認為黃士陵卒年在1913年以后。此印為鄧石如風格的黃士陵早年作品,而此印邊款用刀怯弱,與其邊款差距較大。故此說不足信。晨欣、董建二先生依據黃士陵去世時的挽聯,以及“時年六一”的印章款識,皆認為穆甫去世應在1909年1月。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老穆六十后作”(圖13)與“黟山病叟”(圖14)白文印一對為黃士陵晚期印作。

圖11 黃士陵 李英元印(附邊款)

圖12 黃士陵 蘊真(附邊款)

圖13 黃士陵 老穆六十后作

圖14 黃士陵 黟山病叟
穆甫長子黃少牧篆刻能傳家學,安徽博物院藏有其為徽州名醫程修茲所制“程修茲”白文印一方。
四、摹古寫生 畫啟新風
黃士陵不見早年畫作傳世,然其自幼聰慧,耳濡目染于徽州的文墨興盛,對丹青繪事自不陌生。其客居南昌,在照相館謀生期間,對西洋照相借光存影之技巧應有所了解。而在客粵及北京國子監時期,投入巨大精力拓制、描摹鼎彝器物,使穆甫對物象的造型、紋飾表現能力得到極大的錘煉。從摹畫鼎彝,到寫生花卉,然后將鼎彝與花卉結合,黃士陵在無意中竟然開創出一條中西合璧的繪畫新路。
安徽博物院收藏黃士陵畫作條屏30余件,冊頁一冊計13頁,多為鼎彝博古、寫生花卉,且多為歸里后所作。
清朝乾嘉以后,大批文人、學者投入金石考據之中,以研古為樂。而摹繪、拓制歷代鼎彝器物是中國古代金石學的重要內容。傳世商周秦漢鼎彝重器多為宮廷重寶,或為權貴秘藏,普通人極難窺見。而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刊刻,為更多學人了解、研究歷代青銅器物提供了便利。僧六舟等人創新金石傳拓技藝,拓制器物全形拓,并題寫考證文字,形成了獨特的金石拓片藝術。同時,金石考據的發展使文人、學者獲取了更多的資料,繼而影響到書畫創作風氣的轉變。吳熙載、趙之謙、吳昌碩等人將金石文字的書寫技法和金石氣息導入繪畫,更是開創了中國文人“詩書畫印”融合發展的新境界。黃士陵是金石傳拓發展中的重要人物,他憑借精深的治印技巧,摹刻前代器物文字,頗得盛昱、吳大澂、端方等金石學權威的推許。尤其是在吳大澂幕府期間,受命拓制、摹繪許多愙齋重器,使其金石拓繪技巧達到了巔峰水準。
安徽博物院藏《黃牧甫鐘彝鉤本冊》(圖15)為黃士陵雙鉤摹寫鐘鼎器物的圖冊,古器物多摹自《西清古鑒》、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等金石學名著,也有潘祖蔭等金石家所藏鼎彝重器。黃士陵采用雙鉤白描技法,傳承前輩金石著作中的摹古技巧,器物繪制細致而準確,并將銘文工整摹寫,有些還注明器物出處。此冊雖無年款信息,然從繪制風格看,應屬其在粵時期摹古作品。

圖15 黃士陵 黃牧甫鐘彝鉤本冊
繪制鼎彝不僅成為黃士陵學習古器物的重要方式,這些繪制圖更成為他酬贈友人的佳品。《贈子嘉周文王鼎博古圖》(圖16)落款署“丁酉冬十月”,時黃士陵供職廣州廣雅書局。此圖受贈者子嘉即徽州書畫名家吳鴻勛,也是著名女畫家吳淑娟的父親。這一時期黃士陵的繪器手法趨于成熟,改雙鉤白描而為濃淡暈染,頗似西人素描寫真之法,應是身處廣東,受到西洋藝術手法的影響。

圖16 黃士陵 贈子嘉周文王鼎博古圖
通過對一套館藏《黃士陵摹繪鼎彝器四條屏》的研究,我們了解了更多的信息。這套四條屏并非同時期作品,一件為1894年款,一件為1906年款,分別屬于其在粵及歸黟時期,另兩件沒有年款。其在1894年款作品款識中云:“蟾清仁兄大人囑,即希指謬。歲在閼逢敦牂夏四月,穆甫自黟西畫寄。”“蟾清”未考何人,應是穆甫客粵時之友。“閼逢敦牂”是古時歲星紀年法中的“甲午”,即光緒二十年(1894),而款云“自黟西畫寄”,因穆甫故居在黟縣西之黃村,其曾經歸黟未見于記載。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戰爭,這一年穆甫身染風邪,加之廣雅書局人事變動,其回鄉休養亦在情理之中。
《博古圖》(圖17)立軸題“穆甫黃士陵”,無年款,從風格看應是客粵歸鄉前后的作品。圖中先摹繪三件古鼎彝器物,再繪各種折枝花卉插于器中。古奧樸厚的墨色古器與妍麗生動的折枝花卉相得益彰,別有一番韻致。盡管乾嘉以來亦不乏金石墨拓與清供花卉相結合之作,但是黃士陵仍然以其高度寫生的風格而獨具特色。分析他將摹繪古器物與寫生花卉結合的嘗試,其創作動機或有自我求變求新之內在驅動,或有市場需求之外在呼喚。總之,黃士陵通過摹古與寫生的結合,開創了獨特的繪畫形式。

圖17 黃士陵 博古圖
黃士陵筆下的花卉畫既有傳統工筆花卉的筆墨勾勒技法,也吸收了西洋繪畫的光影感,別具古雅靜謐的意蘊。直到歸鄉去世前幾年,他于書印創作的同時仍然繪制了許多寫生花卉作品。1906年,他為友人蟾清繪制了《寫生工筆四季花卉四屏》(圖18)。畫中各寫四季花卉,先以白描勾勒,再以淡墨暈染,最后罩以淺淡色彩。他在《水仙天竺圖》上題寫道:“師宋人粉本,參用西國理法,以為蟾清仁兄大人屬,即希指謬。”這里明確自言其畫兼師中西的創作手法。

圖18 黃士陵 寫生工筆四季花卉四屏
14世紀中葉后,東西方交流日益增多,而廣東則因沿海的地利而成為最為活躍的地區。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喬瓦尼在澳門大三巴教堂繪制了油畫《救世主》。隨后,西洋繪畫漸次影響開來。廣東沿海與西方通商日久,廣彩瓷器等工藝品源源不斷銷往歐洲,其中許多是依照西方客戶的要求而繪制了西方風格的圖案。巨大的商業利益也促使眾多的中國從事繪畫者學習效仿西洋畫法,而這一風氣也漸次影響到了嶺南文人繪畫。居巢、居廉兄弟以高度寫實的花鳥繪畫風靡一時,他們傳承宋明院體畫技法與惲壽平沒骨畫法,也可窺見西洋繪畫的痕跡。黃士陵早年在南昌接觸過照相術,客粵時期熏染于嶺南中西文化融合的大環境,因而得以借鑒西洋寫實繪畫技法,開創了中西合璧的花卉畫創作新境。
正是黃士陵繪畫借鑒西方寫實技法的特點,讓一件館藏《日本美人圖》(圖19)一直被歸入其名下。這件《日本美人圖》繪一女子面容姣好,身著和服,手持團扇,倚欄獨立。此圖繪畫技法極為寫實,具有西方攝影寫真的技巧,與中國傳統仕女畫法區別很大。詩堂有時人李肇沅題詩跋。李肇沅,字劭初,廣東順德人,曾在廣雅書局任校勘工作,與黃士陵為同事。落款“戊戌初秋”(1898),為黃士陵歸黟前一年。細查此畫有原題簽,上有“厚甫美人,劭初題”,從字跡看應為穆甫所書。另有小字“即黃牧父繪日婦像”,是后代收藏者所書。厚甫即黃士陵在南昌開照相館的胞弟,則知此圖實為厚甫所繪,后贈予穆甫。穆甫赴粵隨身攜帶此畫,并請同事李肇沅題詩,后一直攜歸故里收藏一生。從詩文“輕攜團扇感前緣”“獨抱孤芳少素心”之句,隱約可覺此女或與穆甫交誼不淺,抑或有一段情感的往事。

圖19 黃厚甫 日本美人圖
五、倦游歸來 偃息家山
1898年秋,黃士陵結束客粵生涯返回故鄉黟縣。雖后來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應端方邀請游幕武昌,一年后旋即歸黟不再復出。此時的穆甫已積累相當的資本,遂修筑“舊德鄰屋”以終老。1909年正月辭世,歸葬于黃村北之汪家山。⑤(圖20)

圖20 黃士陵墓(位于安徽黟縣西武鄉黃村汪家山)
關于黃士陵歸鄉的原因,舊說多歸于病。黃士陵晚年有“黟山病叟”一印,說明其身體情況確實不佳。在安徽博物院藏《黃士陵致謝筠亭尺牘合冊》中保存著許多珍貴信息,讓我們有所發現。其中《十月八日札》寫道:“陵亦于仲秋初被風邪所侵,發燒三晝夜,紅子布滿四肢。藥三劑,七日始痊愈。”《五月十六日札》又云:“陵咳疾起自年少時,今廿余年矣。乍發乍已,惟今發尤長,三月至今近六十日,諸藥均效效。后不數日又來醫師云,須常服枇杷膏與梨膏,則可隨愈。”可知黃士陵自少時便身體有疾,早早回鄉親近故土也是常理。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多年客居他鄉,游食刀筆,應酬事務,讓本來就身體虛弱的黃士陵身心疲憊。其晚年喜用“倦游窠主”一印,也可見心跡。黃士陵《致謝筠亭尺牘合冊》有《九月二十二日札》(圖21、圖22),應是1887年秋穆甫在北京國子監學習期間所作。謝筠亭來信盛贊穆甫奉命修補《石經》的業績,而穆甫回信說:“來書謂我修補石經是不朽之業事,垂名將來。覽之面熱汗下也。鄭板橋不云乎?丈夫不能立功天地以養生民,乃區區借筆墨為糊口,其實可羞可恥事。”作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徽州學人,黃士陵沒有科舉功名,雖然游幕于吳大澂、張之洞、端方等權貴幕府并得到賞識,但畢竟只是文字筆墨之事,并不能建立大的功業。其內心的苦悶是可以想象的。加之黃士陵天性耿介,其在廣雅書局工作期間與同事難免生出嫌隙。在《致謝筠亭尺牘合冊》的《九月十三日札》(圖23)中,他與老友訴苦:“書局收掌一席幾被同人奪去,其所欲奪者二人皆往時知好,或托以腹心,或寄以妻孥。以此度之,其視我不為淺矣。一見利害便反眼不相識。”客居他鄉,再遇同事的鉤心斗角,更讓穆甫身心疲倦。

圖21 黃士陵 致謝筠亭尺牘合冊之一

圖22 黃士陵 致謝筠亭尺牘合冊之二

圖23 黃士陵 致謝筠亭尺牘合冊之三
我們還應看到,黃士陵的過早返鄉與其自身思想不能適應時代發展有關。黃士陵生長于徽州,自身聰慧勤奮,后憑文字書印之學獲賞于公卿顯貴。但歸根到底說,他只是如自己所說的“末技游食之民”,是以筆墨謀生的舊文人。而他客居的廣東,恰恰是中國近代風云激蕩的中心。自1895年公車上書到1898年維新變法,康有為、梁啟超等廣東籍文人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改革浪潮,后來廣州更是成為醞釀中國近代革命的搖籃。而黃士陵以及他所交好的官員們或忠君敬職,或潛心學問,他們面對革故鼎新的時代風云,顯得思想保守。與其格格不入地待在廣東,不如早早歸去故里。關于這一點,不得不說黃士陵與稍晚于他的同鄉黃賓虹有著本質的不同。
退居桃花源般的黟縣黃村故里,黃士陵拋卻了客粵時的紛繁塵囂,沉浸在鐘愛的書畫印的世界里。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的藝術創作爐火純青,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品。如果說過早地隱退對于黃士陵而言是一個歷史的遺憾,那么其專心創作、佳作不斷的最后時光,對穆甫、對我們后世都是一個幸運的補償。
注釋
①關于黃士陵的去世時間,舊說為1908年冬。黃山晨欣、董建兩位先生依黃士陵作品落款以及黃士陵去世時友人挽詩的時間,定作1909年1月。
②見傅抱石《關于印人黃牧父》、錢君匋《我所知道的黃士陵》諸文章。
③見清末著名詞人周岸登《慶春宮》。
④見《黃牧甫印集》,葉玉寬主編,安徽美術出版社1990年版。
⑤2022年10月,筆者與黃士陵研究專家晨欣、主持修墓的時任黟縣副縣長姚曉俊先生一道考察黃士陵故居,并祭拜了黃士陵墓地。黃士陵墓地舊時曾遭破壞,近年來隨著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呼吁,當地政府對墓地進行了重修,上海陳茗屋先生題寫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