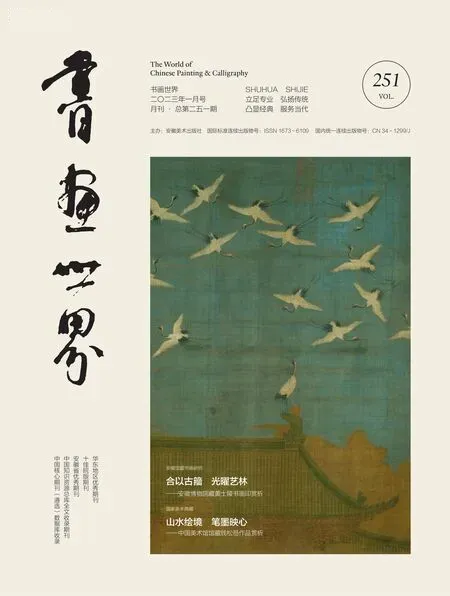明清時期徽州山水圖式研究—談新安畫派山水畫中的形式與情感
文_李超峰 代國娟
巢湖學院美術(shù)與設(shè)計學院
內(nèi)容提要:從藝術(shù)創(chuàng)作角度而言,畫者的情感與其繪畫的圖式密不可分。這種情感的體現(xiàn)與藝術(shù)家人生際遇相關(guān),且直接影響其藝術(shù)風格。經(jīng)歷了朝代更迭,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新安畫派的藝術(shù)家通過藝術(shù)抽象、概括、提煉重塑了徽州的自然山水,形成了風格獨特的以線性為主、幾何化、簡約化的徽州山水圖式,呈現(xiàn)出清新自然又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繪畫風貌,豐富了徽州地域文化的精神內(nèi)涵。
蘇珊·朗格說:“把這些內(nèi)容傳給我們知解力的就不是相關(guān)的信號而是符號形式。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程中借用具體真實的情感進行情感概念的抽象,抽象出的形式便是情感符號。這一點類似語言與思維的關(guān)系,藝術(shù)就是這樣成為一種表達意味的符號。運用全球通用的形式,表現(xiàn)著情感經(jīng)驗。”[1]12蘇珊·朗格為藝術(shù)下了如下定義:“藝術(shù)即人類情感符號的創(chuàng)造。”[1]12從藝術(shù)創(chuàng)作角度而言,畫者的情感與其繪畫的圖式密不可分,息息相關(guān)。這種情感的體現(xiàn)與藝術(shù)家人生際遇相關(guān)。經(jīng)歷了朝代更迭,地處徽州的新安的畫家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了風格獨特的新安畫派藝術(shù)圖式。
一、新安畫派成因及情感線索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其中有大批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讀書人奮起反抗,捍衛(wèi)大明王朝的政權(quán),他們拒絕向“異族”清朝統(tǒng)治者屈服稱臣,堅守氣節(jié),以“明朝遺民”自居,新安畫派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新安畫派以漸江、查士標等為代表,經(jīng)歷了明王朝的崩塌,且這種經(jīng)歷存在不可抗拒性。因文人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具有“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但因清朝的入關(guān),抱負化為泡影。既然不能兼濟天下,則力求獨善其身,他們遠離朝堂,寄情書畫,把游覽中看到的山河景象化為筆下的峻嶺奇松、疏流寒柯以宣發(fā)其郁郁苦悶之情。新安畫派的畫家們多以自己家鄉(xiāng)的徽州山水為表現(xiàn)對象,寓情于景,在畫面表現(xiàn)上自成體系,筆墨獨到,有鮮明的士人格調(diào),畫面中不論是懸崖、松石,還是峭壁峻嶺,都呈現(xiàn)出精謹簡約的畫面效果,畫面空間處理、筆墨關(guān)系上形成了獨特的徽州山水圖式。
二、新安畫派山水畫中物象形態(tài)的幾何化
普列漢諾夫有言:“藝術(shù)表現(xiàn)人們的感情,也表現(xiàn)人們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的表現(xiàn),而是用生動的形象來表現(xiàn)。”[2]形象的表現(xiàn)、情感的表現(xiàn)是藝術(shù)的一個特征。傳統(tǒng)的中國山水畫發(fā)展歷程中,自元代始文人畫興起,畫家多注重畫面物象造型的變化關(guān)系,講究繪畫用筆的書寫性,注重“以書入畫”“書畫同源”,采用有變化的曲線塑造內(nèi)斂、綿柔的物象造型,如文徵明傳世繪畫作品中的山石造型大小相間,以虛實、輕重、強弱不同的線條塑造了山石的力量感和秩序感。變化的曲線一是契合了傳統(tǒng)文人對精神的追求和感悟,二是中國畫區(qū)別于其他畫種的一項重要的造型元素。但因時代、時事的變遷,新安畫派的畫家們借助曲線無法滿足他們情感抒發(fā)的需要,開始了藝術(shù)語言的新探索。縱覽新安畫派山水畫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新安畫派一改傳統(tǒng)的曲線造型,反其道行之。新安諸家在處理畫面物象形態(tài)時帶有很強的主觀性,畫中的山石、樹木、房屋、流水等物象在造型處理上都被畫家加以歸納,舍繁入簡,以一種較強的幾何形風格出現(xiàn)。由此可見,新安畫派畫家群體“舍曲取直”,偏愛直線造型,這種用筆差別使得新安畫派的作品氣息與前代的文人畫有了本質(zhì)的區(qū)別。以大明遺民自居的新安諸家,借助畫筆來宣泄心中憤懣和不認同,以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表現(xiàn)自己心中的徽州山水,把胸中的郁郁之情傾瀉表現(xiàn)于自己的山水畫面中。
新安畫派代表人物漸江的作品中直線的運用尤為突出,情感傳達亦最為強烈。其以獨特的幾何形塑造黃山的自然之景,他的繪畫風格傳承上溯可至董、巨、倪、黃,雖然“元四家”之一的倪瓚對其繪畫風格影響巨大,但他又不拘泥于倪瓚的用筆、用墨方法,提出“敢言天地是吾師”的口號,正是這種繪畫理念成就了漸江獨具一格的繪畫風貌,他所畫的徽州山水較之真正的徽州自然山水更具有圖式性。黃山地處“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皖南地區(qū),有獨特的峰林結(jié)構(gòu),是典型的花崗巖體與冰川遺跡地貌,斷裂和裂隙縱橫交錯,山石裸露,奇松異石很多,黃山奇險的風光成為文人墨客繪畫的素材。漸江把這種奇妙的黃山之景內(nèi)化于心,外現(xiàn)于筆,他畫中的黃山奇崛生姿,畫面造型基本都可以歸納成大小不一、形態(tài)各異的幾何圖形,如他的《天都峰圖》。陳傳席先生對漸江畫面幾何形的使用做了最好的詮釋:“漸江極善用各種式樣的幾何體,有的大幾何體(長矩形或橫矩形)中套中幾何體,中幾何體中又套小幾何體,大幾何體和中小而繁的幾何體相間組成,疏密有致。”[3]同樣的處理方式在他的另一幅作品《始信峰圖》中也得以完美的體現(xiàn),畫面中的始信峰雖脫胎于客觀自然的始信峰,但其中的山石造型不是完全對照現(xiàn)實客觀的物象進行描摹,而是以一種概括的、理想化的、多變的幾何形錯落交疊,把怪石林立、錯綜復雜的山峰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種經(jīng)過取舍和提煉后的造型,使畫中山峰盡顯,凸顯漸江自己的筆墨語言與造型符號,達到了繪畫形式與個人情感的完美統(tǒng)一。新安畫派另一位代表畫家查士標的《長林邃壑圖》也是幾何形造型風格的代表,畫中山石采用比較方直的線條,將山石輪廓和山石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分別概括成大小不一的、不規(guī)則類的幾何形,畫面中大小三角形互為呼應,畫面整體、統(tǒng)一。新安畫派這種以幾何形表現(xiàn)徽州山石的造型方法一方面是情感使然,寄托對故國的哀思和對新朝的不屈,另一方面是對于家鄉(xiāng)山水的熱愛,取景于黃山、白岳,使他們的繪畫作品具有強烈的流派造型特征,把徽州山水“無峰不石,無石不松”的構(gòu)造表現(xiàn)得充分到位,通過大小各異的幾何形組合表現(xiàn)心中的山水形象,將情感跡化徽州山水特有的圖式,寄托他們對大明王朝的追憶和對大好河山的熱愛。
三、徽州山水畫中空間構(gòu)成的平面化
山水畫講求畫面的景物的排列和布局,對畫面空間的追求是歷來評判山水畫高下的標準之一,南朝謝赫在《古畫品錄》的“六法論”中就提出繪畫要“經(jīng)營位置”,五代時期,荊浩提出繪畫要根據(jù)實際自然景物來苦心經(jīng)營畫面,要運用“氣、韻、思、景、筆、墨”的山水“六要”表現(xiàn)全景式山水,他在畫面空間處理上把近景、中景、遠景全都表現(xiàn)在畫面中來描繪山重水復、層巒疊嶂的山水風光,空間上有“咫尺千里”之感。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提出了“高遠”“深遠”“平遠”幾種山水畫的空間處理方法,雖然南宋的馬遠、夏圭把全景山水變?yōu)椤榜R一角”“夏半邊”的特寫式構(gòu)成,但在空間處理上畫面仍然偏向清深幽遠的空間意境。
而新安畫派的畫家們在“置陳布勢”上采用獨特的空間平面化處理,他們在表現(xiàn)徽州山水的時候,不再遵循前代山水畫空間“可居、可游”的理念,而是把自然中的真山水與自己的胸臆相糅合,把自然中的遠近空間壓縮,使近景、中景和遠景之間的空間感覺平面化般的拉近,就黃公望的《天池石壁圖》與漸江的作品《松壑清泉圖》對比來看,兩者對空間的處理方式迥然有異。黃公望的《天池石壁圖》畫面構(gòu)成繁復氤氳,筆墨關(guān)系皴擦渾厚天成,用筆層層推進,表現(xiàn)了山巒遠近層疊、樹木蓊郁的山脈起伏之景。畫面中的山峰連貫,徐徐展開,最終將畫面推向最高處的天池峰頂,讓山峰有一種由近及遠、由低至高的鳥瞰之姿。而漸江的《松壑清泉圖》卻與這種傳統(tǒng)山水的縱深式空間表現(xiàn)完全不同,他在畫中運用線性來塑造山體的結(jié)構(gòu),借助山的氣勢來表現(xiàn)空間的節(jié)奏,畫面中景的山體上大面積留白,隨著山體的推遠拔高,山石的結(jié)構(gòu)才略顯復雜,高處山體結(jié)構(gòu)逐漸加密,越來越多的結(jié)構(gòu)用筆、用線分割與近處空白山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右下角的松樹筆墨關(guān)系濃重,三棵松樹的造型刻畫精妙,它們生動自然地相互依偎,聚散有致,更加襯托得主體山石氣勢雄峻,清冷挺拔。畫面主要的山體平面結(jié)構(gòu)顯得簡約潔凈,加上與近景繁密的松樹和遠景的溪流瀑布形成疏密對比,最終使畫面之景呈現(xiàn)出奇縱穩(wěn)重、幽深空曠的氣息。這種對空間平面化的處理,一方面是源于大自然的饋贈,黃山山景對其有最直觀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漸江對徽州的山川之美、對黃山的偉俊秀逸的感悟,是景隨人意的直觀表現(xiàn),是其對自然觀照的體悟,亦與其自身沉靜堅忍的性格相呼應。他取法于自然,寄情徽山,書寫出其心中的浩然之氣,他對空間平面化的處理寄寓了對故國大好河山的無限懷念和熱愛,也是徽州山水圖式化的特殊呈現(xiàn)。
四、徽州山水中筆墨關(guān)系的簡約化
中國山水畫中的筆墨不是簡單的濃淡顏色關(guān)系,它承載著文人的修養(yǎng),真正的筆墨能傳遞出畫者的情感、素養(yǎng)和其自身的文化氣息。董其昌先生在《畫禪室隨筆》的雜言中有言:“以蹊徑之怪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4]正是因為畫家對筆墨精妙的追求使山水畫比自然山水更具有藝術(shù)的審美意義,這也是山水畫的重要價值所在。相較于前人對筆墨的追求,新安畫派崇尚筆墨關(guān)系的簡潔化,在表現(xiàn)徽州山水的表現(xiàn)上,他們惜墨如金,不輕落筆,并“以簡疏的筆墨,使其筆下的自然山川呈現(xiàn)出幽澹之美,蓄涵著勃勃生機”[5]。一如新安畫派李永昌的《黃山圖冊》,畫幅雖小,但構(gòu)圖得宜,繁簡咸妙,畫中的屋宇、舟亭、林木、石磯等皆用筆簡練,賞讀時可見,即使在面積較大的石壁上落筆也極為謹慎,或用干筆皴擦,或以淡墨略掃,畫面無一廢筆。就畫面而言,乍看似空空無物,仔細品讀卻白處有畫,這正應了《徽州文化全書·新安畫派》引言中的概括:“從創(chuàng)作技法看,新安畫派的畫家,特別是漸江及其忠實繼承者,大都側(cè)重以線造型,大量使用塊狀結(jié)構(gòu),極少皴擦與渲染。”[6]漸江的《西巖松雪圖》是新安畫派創(chuàng)作技法的典型的代表,其描繪了徽州的雪景山色,畫中崖危嶺峻,青松盤曲,近處的松樹以濃重的焦墨畫成,樹干以干筆略作皴擦,整座山體除了外輪廓氣定勾斫外,內(nèi)部結(jié)構(gòu)鮮有刻畫,山石以大面積的直線條進行勾勒,山丘上的松樹用筆肯定,與其后的淡筆山石形成了強烈的墨色反差,整塊山體晶瑩剔透,筆墨關(guān)系已減至極致。同時,畫中的用筆注重線條的意趣性,使畫面呈現(xiàn)出強烈的蕭疏荒寒之感。從用筆上來看,版畫般的刀刻意味明顯,用筆猶如不露刀鋒的篆刻所成,樸拙荒茫,充滿金石之氣。從構(gòu)圖上看,此幅作品與漸江其他的山水畫軸一樣,以層巒與疏木構(gòu)成了畫面的主調(diào),謝堃在《書畫所見錄》中稱漸江“愛用鼠足小點,攢取巒頭峰頂者,此特與世異耳”。從這幅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漸江在表現(xiàn)徽州山水時候的這種“與世異”的獨特用筆,新安畫派的這種疏冷清寂的筆墨關(guān)系既是他們遭遇國運不祚,想隱居山林安于清凈和清貧的退守,也是他們固守讀書人的道德文章氣節(jié)的彰顯,畫中的草石渚岸空曠高古,體現(xiàn)著新安畫派畫家群體特有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同時,新安畫派的繪畫風格與徽州山水的特殊風貌亦有直接的關(guān)系,新安畫派師法自然,直師造化,漸江長期居住于黃山、白岳之間,對徽州的山水識于目、化于心,他將見到的層巒疊嶂、老樹虬松一一表現(xiàn)在自己的畫面中,其畫面既帶有強烈的主觀創(chuàng)造性,又兼具對自然山水的真切感受。
結(jié)語
綜上所述,徽州山水給新安畫派帶來了無限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靈感,新安畫派諸家創(chuàng)作出來源于自然山水,又“與自然脫離,與此同時,使其外觀表象達到高度的自我完美,成為一個不用分析解釋便可以直觀把握的概念性形式”[1]19。換言之,新安畫派的藝術(shù)家通過藝術(shù)抽象、概括、提煉重塑了徽州的自然山水,使黃山等自然風景的外觀表象達到高度的自我完美,成為明清時期典型的以線性為主、幾何化、平面化、簡約化的經(jīng)典山水圖式。概括、提煉后的形象、輪廓、節(jié)奏、運動都比自然山水包含了更多的內(nèi)容與意味,作為有機整體的藝術(shù)形象就成為一種新安畫派畫家的感情符號。新安畫派這種師造化、師古人,又不拘泥于造化、不拘泥于古人的繪畫方式,使徽州山水在中國山水畫中極具靈性,觀者欣賞他們的畫作時仿佛身臨其境,能切身感受到徽州雨后清新的空氣、清冷消寂的冰雪。新安畫派的山水作品是中華民族時代變遷、歷史和命運緊密相連的深刻證明,也是畫家聊以安撫內(nèi)心、凈化內(nèi)心的強大力量。在他們筆下,徽州山水圖式呈現(xiàn)出清新自然又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繪畫風貌,豐富了徽州地域文化的精神內(nèi)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