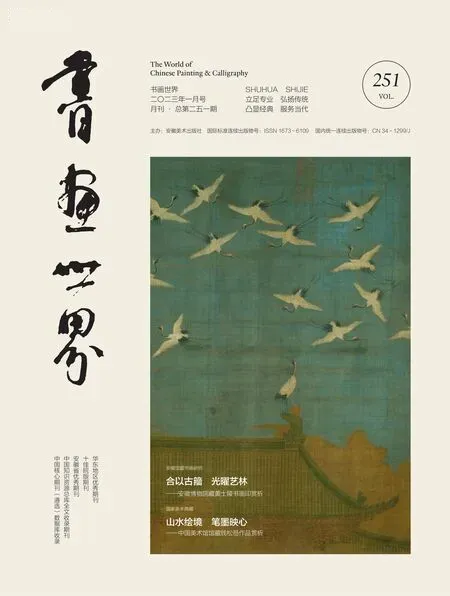武梁祠畫像與《女史箴圖》在女性題材方面的意蘊表現
文_沈玉香 路揚
安徽師范大學
女性題材繪畫濫觴于東周,至魏晉隋唐時期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藝術傳統體系。在宏觀的角度下考察中國繪畫中女性題材作品,我們可以發現自東周到宋代,女性題材的繪畫一直占著相當大的比重。本文所探討的蘊含道德勸誡意味的女性題材繪畫自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便已產生了許多代表性作品,其中就包含本文作為案例將要進行分析的山東嘉祥武梁祠的列女畫像以及《女史箴圖》等。而伴隨著繪畫藝術的發展,不同畫面中對于相同內容的表現也逐漸產生不同的藝術面貌,本文以畫面表現的內容為基礎進行分析,通過對不同階段的女性道德勸誡題材繪畫的對比,探究此類繪畫的更多內在意義。
一、文化背景
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的文化思想,強調以儒家思想為治國根本,伴隨著漢武帝對該主張的采納,儒學成為官方確立的正統思想,而儒家倫理的核心在于“三綱”。班固在《白虎通義》中明確表示:“三綱者何謂也?君臣、父子、夫婦也。”[1]在之后的很長時間里,《白虎通義》作為官方讀物將儒家思想進行了統一并進一步推廣,儒家思想日漸盛行,影響了從君主到百姓的言行舉止和思想意識,且逐漸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漢成帝時期,時任光祿大夫的劉向根據儒家思想對古代文獻中的歷史人物故事進行重新闡釋,以便后人學習。劉向編撰的《列女傳》共匯編了105名歷史女性的故事,其中包含各時期的賢妃貞婦,目的在于進一步幫助皇帝“由內而外”地推廣儒家思想,引導女性認知何為“賢明”“貞順”“母儀”等優良品德,但是這些女性楷模“向上”在幫助帝王正確娶妻選妃的同時,也無形中“向下”規范了女性的品行,體現出其中的說教功能。也正是這本書,在把“三綱”從思想意識形態轉變為視覺藝術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以《列女傳》為藍本不斷出現了更多關于規范女性的著作,如《女誡》《女史箴》等,而關于女性道德勸誡題材的繪畫也隨之出現,眾多藝術家創作出許多經典的作品,在中國繪畫藝術史中留下濃重的一筆。
二、列女題材圖像分析
(一)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
始建于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前后的山東嘉祥武梁祠里的一系列列女題材圖像,被認為是目前關于女性道德勸誡題材中現存較早的一個典型案例。在這個被認為是漢代畫像典范的家族祠堂里,一系列表現女性歷史人物的畫面緊隨著十二個古代帝王出現,畫面中所表現的故事均來源于《列女傳》,以具體的歷史故事和直觀的視覺表現傳達出封建社會女性面對丈夫與家庭應當具備的女性道德。
其中以“楚昭貞姜”為例,故事原本講述的是楚昭王在一次外出游玩中,將自己的夫人姜氏留在了宮中漸臺之上。在游玩的過程中他聽聞江水在不斷上漲,很可能會淹沒漸臺,于是他派使者前去營救,然而匆忙之中他忘記將信物交給使者。由于到了夫人面前的使者拿不出信物,夫人堅持不與其離開。當使者去而復返帶著信物回到漸臺時,漸臺已經崩塌,夫人也被洪水沖走了。楚昭王聽聞后感嘆道:“夫人為保全節操而死,身處險境依舊堅守諾言,成就了貞潔的美名。”于是便賜給夫人“貞姜”的名號。
繪畫作品具有空間性,在表現一個空間范圍內的故事情節時,往往呈現出的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頃刻”[1],武梁祠中的畫像“楚昭貞姜”(圖1)便是如此。面對上述繁復的故事情節,畫家選擇了使者第一次回到漸臺與姜氏對話的一瞬間,既能夠引人去探究故事的前因,又能夠為下文姜氏拒絕與使者同走,后不幸遇難做鋪墊,可謂故事中極具轉折的一瞬間。就畫面的整體空間來看,如果將畫面看成由四個矩形空間構成,那么畫面中僅有的兩處表明了使者與姜氏的位置關系,使者跪于階下似乎在說著什么,一名侍從將使者所言傳達給姜氏,姜氏給予回應。由此可以推斷畫面中的一條條黑色的豎線就如同漸臺之上的一根根立柱,起到對建筑空間進行劃分的作用,從左到右分別意味著室外與室內,室內又可被細分為前廳與后院。而畫面上下方的矩形、三角形等則是象征著宮殿中的屋頂、斗拱、臺基,以最簡明的方式刻畫了中國古代的建筑結構。就畫面中的人物表現來看,每一個人物都好似剪影一般,看不到具體的容貌,但可以通過簡單的肢體語言以及身形體態大致區分其中的人物狀態。故而可以看出武梁祠的畫像其創作的重點并不在于畫面的描繪,而是對《列女傳》中故事內容的再現。通過對故事內容的精準表現從而達到對女性的規勸與訓誡,并且讓這樣的思想內容跨越生與死的距離,以達到對女性個人思想意志發展的全方面壓制。

圖1 東漢 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拓片局部“楚昭貞姜”)
(二)顧愷之《女史箴圖》
作品《女史箴圖》(圖2)是畫家顧愷之根據西晉作家張華的著作《女史箴》而創作的。《女史箴》原文共有12節,故而《女史箴圖》亦有12段,但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僅存有唐代摹本,且僅剩9段,分別展現了“馮媛當熊”至“女史司箴敢告庶姬”9個故事。畫家通過對畫面中女史們的身姿、儀態、服飾的生動描繪,生動地再現了上層婦女日常生活場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處時代的婦女生活面貌。但實際上,《女史箴》的作者張華在創作之初實則是以女史的角度向女性讀者傳達出一系列的道德訓諭,在表現上層婦女生活的同時,將這些上層婦女應該具備的道德品行蘊藏其中,以達到其說教的目的。而顧愷之在據此進行藝術創作的過程中,一方面將書中故事盡可能地完整展現,另一方面也生動地表現了不同人物的個性形象。

圖2 晉 顧愷之 女史箴圖(局部“馮媛當熊”)24.8cm×348.2cm(全卷)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以《女史箴圖》中所描繪的“馮媛當熊”為例。一日,漢元帝率眾人圍看斗獸之景,后宮佳麗們圍坐一旁。然而一只黑熊突然躍出且直逼漢元帝而來,見此場景,馮婕妤挺身而出,擋在漢元帝的前面護其安全。所幸隨行的士兵及時上前制服,并未傷到他人。正是如此驚險的一幕被畫家選擇并記錄了下來,只見畫面中的漢元帝雖還坐在原位,但是那向上飛起的胡須似也暴露了其內心的慌張與害怕。隨著他的視線所及之處,馮婕妤映入眼簾,只見她衣帶飄飄、身形纖瘦,然而就是如此一名弱女子卻在面對失控的黑熊時毫無懼色,毫不猶豫地擋在黑熊與漢元帝的中間。在她身旁的兩名士兵雖聯手制服了黑熊,但其中一人手執武器向前刺去的同時卻張口吶喊,而另一人不僅面露懼色,而且踟躕退步不敢向前,二人的驚慌失措與馮婕妤的鎮定自若形成了鮮明對比,更加凸顯了馮婕妤的優良品行。而造成這一幕產生的“罪魁禍首”——黑熊,在畫家的筆下亦是仔細描繪,無論是向前撲的肢體動作或是動物身上的毛發塑造皆生動形象。
顧愷之表面上是描繪馮婕妤與漢元帝之間的故事,實際上卻是在凸顯畫中女主角馮婕妤的個人品行,尤其是用其他后宮婦人慌張失措的失儀之態進行反襯,產生極致的差距。可以說,高度還原并再現《女史箴》的內容只是其創作目之一,傳達作者張華隱藏在書中的意蘊才是更重要、更真實的目的之本。
三、意蘊表現
(一)外在表現
通過對武梁祠畫像和《女史箴圖》部分畫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同樣是以道德勸誡為題材的女性繪畫,兩者在畫面表現上已經產生了極大的不同。后者的畫面人物具體而生動,設色豐富而艷麗,不再是武梁祠中簡單的黑白人物形象,就連人物內在的情緒變化都可以通過面容或肢體語言側面展現。這種對女性勸誡的表達和女性美麗面容的表現,反映了當時的畫家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對“女性美”的塑造,這也意味著女性不僅要具有美麗的內在,外貌上也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這種現象可以歸結為畫像的教諭內容與新出現的審美欲望產生了聯動,亦是內容與審美之間張力的表現。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女性對于美的追求,為后來女性繪畫的發展做了鋪墊,同時促使勸誡題材的女性繪畫樣貌不斷推陳出新。例如清代畫家焦秉貞所創作的《歷朝賢后故事圖冊》,意在借古代賢良后妃的懿德來宣傳封建社會的倫理思想,為后宮中的妃嬪們樹立楷模,但是畫面在創作時卻采用了新興的美人圖創作樣貌,再一次體現了女性繪畫中內在勸誡與外在美之間的完美結合。
(二)內在要求
這些作品的創作原型皆來源于文學作品,故而根據這些文學作品的創作目的便可對畫面的中心主旨探討一二,無論是《列女傳》又或是《女史箴》,其本質的出發點都是作為明確的儒家道德教材而編寫。故而支撐起畫面的不僅僅是人物塑造、色彩表現等繪畫語言,更是具有社會和道德含義的儒家思想準則。那么,“楚昭貞姜”中表現的不僅僅是姜氏對楚昭王的諾言,更是妻子對丈夫、王后對君主的義務,這也正是對應了“三綱”中的君臣、夫婦。而姜氏不與使者直接對話,而是通過侍從傳達這一點,再結合畫面使者在外、姜氏在內的空間位置關系,不僅顯示出“男女授受不親”的儒家原則,更加強調了姜氏對于女德的絕對遵守。《女史箴圖》中的“馮媛當熊”亦是如此。
結語
對武梁祠畫像以及《女史箴圖》中部分畫面的分析研究,不僅讓我們對此類題材繪畫的藝術表現之變有了初步了解,而且通過對此類繪畫內在意蘊的探討,我們對女性繪畫有了更加清晰的認知,這也為今后開展對女性繪畫的專題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