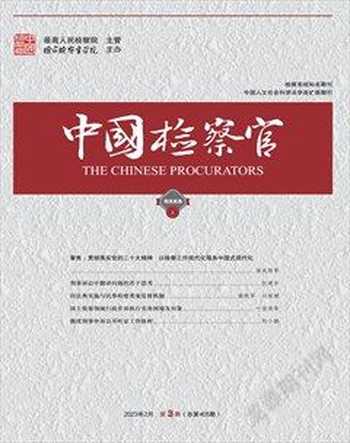輕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盜竊”犯罪的檢察應(yīng)對(duì)
徐清
摘 要:司法實(shí)踐中,“多次盜竊”被視為行為犯,次數(shù)認(rèn)定較為嚴(yán)苛,刑事處罰相對(duì)嚴(yán)厲,不符合輕罪治理的時(shí)代要求。建議針對(duì)“多次盜竊”定罪量刑中的突出問(wèn)題,構(gòu)建“次數(shù)+數(shù)額+情節(jié)”一體的立案標(biāo)準(zhǔn),積極探索建立不起訴標(biāo)準(zhǔn)、緩刑適用標(biāo)準(zhǔn),適當(dāng)限縮打擊范圍、稀釋刑罰的強(qiáng)度,在司法辦案中彰顯法治溫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盜竊”犯罪中的深層矛盾,防患未然,促進(jìn)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關(guān)鍵詞:輕罪治理 多次盜竊 次數(shù)認(rèn)定 罰金刑
最高檢工作報(bào)告顯示,檢察機(jī)關(guān)起訴殺人、搶劫等嚴(yán)重暴力犯罪由1999年的16.2萬(wàn)人降至2020年的5.7萬(wàn)人、2021年的5.3萬(wàn)人。[1]2021年,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占比14.89%,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緩刑、單處附加刑的輕刑案件占比 85.11%[2],輕罪[3]成為犯罪治理的主要對(duì)象。相對(duì)于重罪治理,輕罪治理更考驗(yàn)司法人員對(duì)刑事政策、法治理念和社會(huì)治理觀的整體把握。如何在司法辦案中彰顯法治溫度、司法善意,提升治理效能,是輕罪治理背景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本文以“多次盜竊”為視角,探索提出輕罪治理中的不足,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完善建議。
一、“多次盜竊”犯罪的司法樣貌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修正案(八)》將 “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列為與“多次盜竊”并列的非數(shù)額型盜竊定罪模式。4種行為中,入戶盜竊還侵犯住所安寧,攜帶兇器盜竊存在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現(xiàn)實(shí)可能性,扒竊觸犯了貼身禁忌。那么,何種“多次盜竊”具有與上述3類行為同質(zhì)的違法性,理論上爭(zhēng)議較大。為呈現(xiàn)“多次盜竊”犯罪的實(shí)然樣貌,本文將研究對(duì)象限定為2022年的生效裁判文書(shū)。在中國(guó)裁判文書(shū)網(wǎng)以“2022”“多次盜竊他人財(cái)物,其行為已構(gòu)成盜竊罪”“盜竊罪”為關(guān)鍵詞,共檢索出150篇裁判文書(shū),“多次盜竊”主要呈現(xiàn)以下特點(diǎn):
(一)犯罪主體前科劣跡占比高
150件案件共涉及被告人159人,其中累犯、犯罪前科及前罪未執(zhí)行完畢的74人,占比 46.54%。不少人因盜竊犯罪“二進(jìn)宮”乃至“三進(jìn)宮”,刑滿釋放不久又走上犯罪道路。
(二)犯罪行為以“小額多次”為主
若參考我國(guó)大多數(shù)地區(qū)2000元的“數(shù)額較大”入罪標(biāo)準(zhǔn),150件案件中犯罪金額未達(dá)2000元的共104件,占比69.33%。2001元及以上的18件,還有28件因贓物無(wú)法核價(jià)等原因未認(rèn)定具體犯罪金額。從盜竊次數(shù)看,盜竊3-5次的占比77.33%。簡(jiǎn)言之,約7成的“多次盜竊”犯罪盜竊次數(shù)不滿5次,盜竊金額未達(dá)我國(guó)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數(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
(三)刑事處罰相對(duì)嚴(yán)厲
根據(jù)近3年《全國(guó)法院司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我國(guó)1年以上 3年以下有期徒刑判決率約為23%,不滿1年有期徒刑判決率約為17%,拘役判決率約為15%,緩刑判決率約為25%。[4]然而,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多次盜竊”以相對(duì)嚴(yán)厲的監(jiān)禁刑為主:150件案件159個(gè)被告人中,被判處有期徒刑99人,其中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5人,占比 3.14%;不滿1年有期徒刑94人,占比59.12%,高于全國(guó)平均數(shù)42個(gè)百分點(diǎn);拘役21人,占比13.21%,低于全國(guó)平均數(shù)約2個(gè)百分點(diǎn);緩刑26人,緩刑判決率16.35%,低于全國(guó)平均數(shù)約9個(gè)百分點(diǎn)。此外,還有13人被判處罰金刑,罰金判決率8.17%。
二、“多次盜竊”犯罪定罪量刑的若干問(wèn)題
(一)將“多次盜竊”視為行為犯的傾向有待商榷
一些地方性規(guī)范文件指出,“多次盜竊”是指在兩年內(nèi)實(shí)施3次以上盜竊行為,但數(shù)額累計(jì)未達(dá)到較大以上的情形。[5]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以及扒竊,屬于行為犯,行為人只要實(shí)施了4種行為之一,就構(gòu)成盜竊犯罪,不以取得財(cái)物為既遂的標(biāo)準(zhǔn)。[6]從公開(kāi)的裁判文書(shū)看,將“多次盜竊”視為行為犯的傾向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一方面,未竊得財(cái)物的行為納入次數(shù)認(rèn)定;另一方面 ,財(cái)物價(jià)值不影響次數(shù)認(rèn)定。這種不考慮侵犯法益的嚴(yán)重性,將“多次盜竊”視為行為犯的傾向有待商榷。
從“多次盜竊”歷史變遷看,定罪量刑始終與盜竊數(shù)額或犯罪情節(jié)密不可分。1979年刑法中的盜竊罪是絕對(duì)的數(shù)額犯,“多次盜竊”僅在累計(jì)盜竊數(shù)額達(dá)到“數(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時(shí)才定罪處罰。1992年“兩高”《關(guān)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首次將“多次盜竊”納入懲治范圍,但適用范圍限定為“多次扒竊”和“入戶盜竊多次”。1997年刑法建立了“多次盜竊”“數(shù)額較大”二元定罪模式,為確保“多次盜竊”與“數(shù)額較大”具有同質(zhì)的違法性,司法解釋進(jìn)一步限制了“多次盜竊”的適用范圍,即1年內(nèi)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chǎng)所扒竊3次以上的,認(rèn)定為“多次盜竊”。《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修正案(八)》將原來(lái)作為 “多次盜竊”限定條件的“入戶盜竊”“扒竊”獨(dú)立治罪,并不意味著無(wú)須考慮“多次盜竊”行為的違法性和應(yīng)受懲罰性。在對(duì)“多次盜竊”進(jìn)行司法解釋時(shí),有意見(jiàn)主張,“多次盜竊”無(wú)論被盜財(cái)物數(shù)額多少、情節(jié)如何,應(yīng)當(dāng)一律追究刑事責(zé)任,但是這一意見(jiàn)最后沒(méi)有被采納。[7]不論是否竊得財(cái)物、不論盜竊何種價(jià)值的財(cái)物一律入罪的做法,不符合立法本意。
(二)次數(shù)認(rèn)定不考慮概括故意擴(kuò)張了打擊范圍
基于一個(gè)概括的犯罪故意,實(shí)施了若干個(gè)盜竊行為的,能否認(rèn)定為一次盜竊,理論界有不同意見(jiàn)。有學(xué)者主張?jiān)谕粫r(shí)間、同一地點(diǎn)針對(duì)同一被害人所實(shí)施的盜竊才是一次盜竊[8]。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主客觀兩個(gè)方面,如行為人的主觀意思、時(shí)間、地點(diǎn)的相對(duì)集中性等進(jìn)行實(shí)質(zhì)判斷[9]。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2016年3月《關(guān)于 “多次盜竊”中“次”如何認(rèn)定的法律適用請(qǐng)示》的答復(fù)意見(jiàn)主張實(shí)質(zhì)判斷。從收集的2022年生效裁判文書(shū)看,一般立足于客觀主義和行為刑法立場(chǎng),次數(shù)認(rèn)定以不考慮概括故意為原則、認(rèn)定概括故意為例外。150件案件中,共 11件案件被告人在同一時(shí)間段,同一街道、商超或村莊連續(xù)作案,僅1件以概括故意認(rèn)定次數(shù),其余10件均按盜竊行為數(shù)認(rèn)定次數(shù)。
這種不考慮概括故意認(rèn)定次數(shù)的做法,可能不當(dāng)擴(kuò)張了“多次盜竊”的打擊范圍。盜竊罪的保護(hù)對(duì)象是具有較大價(jià)值的財(cái)產(chǎn)法益,“多次盜竊”卻將次數(shù)作為入罪標(biāo)準(zhǔn),說(shuō)明次數(shù)反映了行為的應(yīng)受懲治性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正如1984年“兩高”《關(guān)于當(dāng)前辦理盜竊案件中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wèn)題的解答》指出,要把偶爾失足的,同多次盜竊的加以區(qū)別,要把一般盜竊,同慣竊、重大盜竊加以區(qū)別。簡(jiǎn)言之,“多次盜竊”的“次數(shù)”應(yīng)當(dāng)具有屢教不改、作案時(shí)間跨度長(zhǎng)、盜竊惡習(xí)深等特征。浙江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關(guān)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jiàn)》就指出,“同個(gè)晚上在同一條或相接壤的馬路上連續(xù)盜竊多輛汽車內(nèi)的物品的,可以認(rèn)定為一次盜竊;同個(gè)晚上在同一個(gè)小區(qū)內(nèi)連續(xù)盜竊多輛自行車的,可以認(rèn)定為一次盜竊”[10]。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在“同一時(shí)間”“同一地點(diǎn)”連續(xù)實(shí)施盜竊行為的,不宜認(rèn)定為多次。
(三)小額重罰合理性存疑
有學(xué)者在136570個(gè)盜竊案件中,采用分層隨機(jī)抽樣方法抽取1806份判決書(shū)研究發(fā)現(xiàn),當(dāng)盜竊數(shù)額小于等于40萬(wàn)元時(shí),盜竊罪的“涉案金額”基準(zhǔn)罰金刑金額=872.13+0.32×盜竊數(shù)額。[11] 鑒于絕大多數(shù)“多次盜竊”的“涉案金額”低于2000元,若參照這一公式,則基準(zhǔn)罰金應(yīng)當(dāng)少于1512元。但實(shí)踐中“多次盜竊”罰金刑多高于1512元。150件案件159個(gè)被告人中,被判處1500元以下罰金的53人,僅占33.33%。罰金1500元以上的占106人,占比66.67%,其中,罰金1501-2000元的55人、2001 -3000元的30人、3001-4000元的9人、4001-10000元的12人。
“多次盜竊”罰金刑畸重的根本原因在于罰金刑上限過(guò)高。2013年“兩高”《關(guān)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第14條明確了罰金刑計(jì)算規(guī)則,有犯罪數(shù)額的,“應(yīng)當(dāng)在一千元以上盜竊數(shù)額的二倍以下判處罰金”。沒(méi)有盜竊數(shù)額或者盜竊數(shù)額無(wú)法計(jì)算的,“應(yīng)當(dāng)在一千元以上十萬(wàn)元以下判處罰金”。《刑事審判參考》“蒲長(zhǎng)才盜竊案”明確了“多次盜竊”屬于非數(shù)額型犯罪,應(yīng)當(dāng)“在一千元以上十萬(wàn)元以下判處罰金”,使得“多次盜竊”罰金刑上限高達(dá)十萬(wàn)元,帶來(lái)了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多次盜竊”主刑、罰金刑與侵犯法益、犯罪惡性不匹配等“小額重罰”傾向,往往引發(fā)民眾質(zhì)疑,一些同案不同判、合法卻不合理的裁判還影響了司法權(quán)威。
三、輕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盜竊”犯罪的檢察應(yīng)對(duì)
近 20 年來(lái)我國(guó)刑事立法活動(dòng)呈現(xiàn)出明顯的輕罪治理特征,體現(xiàn)為輕罪數(shù)量增加,犯罪圈層擴(kuò)大;預(yù)防性司法理念明顯,犯罪門(mén)檻降低。輕罪治理的目的更多是防患于未然,而非增設(shè)犯罪。[12]針對(duì)“多次盜竊”定罪量刑中的突出問(wèn)題,應(yīng)自覺(jué)適應(yīng)輕罪治理的時(shí)代要求,統(tǒng)一執(zhí)法尺度,強(qiáng)化行刑銜接,推動(dòng)訴源治理,助力國(guó)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
(一)處理好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關(guān)系
未達(dá)“數(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的“多次盜竊”和行政處罰之間有犬牙交織之處, “多次盜竊”上升為犯罪,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犯罪數(shù)額、犯罪情節(jié)等因素綜合認(rèn)定。建議地市級(jí)或省級(jí)層面在充分調(diào)研的基礎(chǔ)上先行先試,探索建立“次數(shù)+數(shù)額+情節(jié)”一體的“多次盜竊”立案標(biāo)準(zhǔn),處理好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關(guān)系。對(duì)于盜竊三次且涉案數(shù)額未達(dá)當(dāng)?shù)亍皵?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四分之一,且有以下情形的,屬于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guī)定“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rèn)為是犯罪”不予立案:(1)未受過(guò)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初犯、偶犯;(2)發(fā)生在親友、鄰里、同學(xué)、同事之間的小額盜竊并獲得被害人諒解的;(3)因保暖或充饑盜竊少量生活用品的、廢舊用品等價(jià)值不大財(cái)物的;(4)歸案前主動(dòng)將原物放回原處或歸還被害人,或積極退贓退賠的;(5)其他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
(二)處理好從寬與從嚴(yán)的關(guān)系
堅(jiān)持寬嚴(yán)相濟(jì)刑事政策。一方面,對(duì)累犯、前罪尚未執(zhí)行完畢的再犯,被行政處罰后一年內(nèi)又再次盜竊他人財(cái)物等主觀惡性較重的,在醫(yī)院盜竊病人及其親友財(cái)物,盜竊救災(zāi)搶險(xiǎn)優(yōu)撫等財(cái)物的,涉案數(shù)額較大或采取破壞性手段盜竊等情節(jié)惡劣的,原則上應(yīng)配置監(jiān)禁刑,堅(jiān)決予以懲治。另一方面,堅(jiān)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通過(guò)公檢法聯(lián)合發(fā)文形式就次數(shù)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不起訴標(biāo)準(zhǔn)、緩刑適用標(biāo)準(zhǔn)等統(tǒng)一執(zhí)法尺度,適當(dāng)限縮打擊范圍、稀釋刑罰的強(qiáng)度。建議對(duì)“多次盜竊”犯罪數(shù)額未達(dá)當(dāng)?shù)亍皵?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二分之一的,若行為人是初犯、偶犯,案發(fā)后認(rèn)罪悔罪,積極退贓退賠,且未造成嚴(yán)重后果的,適用不起訴。綜合考慮盜竊次數(shù)、盜竊數(shù)額、前科劣跡,盜竊手段、對(duì)象、后果等情節(jié),建立緩刑適用規(guī)則。探索制定非數(shù)額型罰金型裁量規(guī)則,積極扭轉(zhuǎn)“小額重罰”的現(xiàn)狀,建議“多次盜竊”涉案金額未達(dá)當(dāng)?shù)財(cái)?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四分之一的,罰金原則上為1000元。涉案金額未達(dá)當(dāng)?shù)財(cái)?shù)額較大標(biāo)準(zhǔn)二分之一的,罰金原則上不超過(guò)2000元。
(三)處理好檢察權(quán)的能動(dòng)性與被動(dòng)性的關(guān)系
作為傳統(tǒng)的刑事檢察業(yè)務(wù),盜竊等刑事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具有被動(dòng)受理的特點(diǎn),但一放了之、一捕了之、一訴了之并不符合輕罪治理的時(shí)代要求。要處理好檢察權(quán)的能動(dòng)性與被動(dòng)性的關(guān)系,深入分析“多次盜竊”案件中的深層矛盾,防患未然,促進(jìn)溯源治理。對(duì)于不起訴案件,一些地方檢察機(jī)關(guān)如南京、蘇州、無(wú)錫等地建立了不起訴移送行政處罰銜接工作規(guī)定、不起訴非刑罰處罰工作指引,對(duì)被不起訴人進(jìn)行行政處罰的同時(shí),制定公益勞動(dòng)、社會(huì)服務(wù)等任務(wù),強(qiáng)化了行刑銜接,織密社會(huì)治理法網(wǎng)。針對(duì)多次盜竊犯罪主體前科劣跡占比高,檢察機(jī)關(guān)應(yīng)主動(dòng)作為,可建議相關(guān)社會(huì)保障部門(mén)將一些刑滿釋放、無(wú)固定生活來(lái)源的行為人納入社會(huì)低保體系,幫助提升職業(yè)技能,積極防范其再次走上犯罪道路。針對(duì)一些自助購(gòu)物領(lǐng)域暴露出一些安全隱患和監(jiān)管漏洞,充分發(fā)揮檢察建議和普法宣傳參與社會(huì)治理的作用,建議自助購(gòu)物商家在自助結(jié)賬區(qū)、商品被盜高發(fā)區(qū)等區(qū)域張貼顯著提醒標(biāo)志, 督促經(jīng)營(yíng)者承擔(dān)應(yīng)有的社會(huì)責(zé)任,防止普通人因?yàn)橐荒钪钣|犯刑法,從源頭上規(guī)制盜竊行為。
*江蘇省南通市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kāi)發(fā)區(qū)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shū)記、副檢察長(zhǎng)[226001]
[1] 參見(jiàn)2020年、202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bào)告》,最高人民檢察院網(wǎng)https://www.spp.gov.cn/gzbg,最后訪問(wèn)日期:2022年10月19日。
[2] 參見(jiàn)《2021年全國(guó)法院司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最高人民法院公報(bào)網(wǎng)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a6c42e26948d3545aea5419fa2beaa.html,最后訪問(wèn)日期:2022年10月19日。
[3] 關(guān)于輕罪標(biāo)準(zhǔn),本文根據(jù)2020 年最高檢張軍檢察長(zhǎng)在向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報(bào)告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情況時(shí),將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輕罪案件標(biāo)準(zhǔn)。
[4] 參見(jiàn)《2019年全國(guó)法院司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2020年全國(guó)法院司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2021年全國(guó)法院司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最高人民法院公報(bào)網(wǎng)http://gongbao.court.gov.cn,最后訪問(wèn)日期:2022年10月19日。
[5] 參見(jiàn)2015年浙江省高級(jí)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關(guān)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jiàn)》,北大法寶網(wǎng)https://www.pkulaw.com/lar/17923379.html?from=singlemessage,最后訪問(wèn)日期:2023年1月10日。
[6] 參見(jiàn)2013年北京市高級(jí)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辦理盜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的若干意見(jiàn)》,北大法寶網(wǎng)https://www.pkulaw.com/lar/6c8c3a422d7542586364b83d74069c50bdfb.html?way=listView,最后訪問(wèn)日期:2023年1月10日。
[7] 參見(jiàn)胡云騰、周加海、周海洋:《〈關(guān)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2014年第15期。
[8] 參見(jiàn)張明楷:《刑法學(xué)》(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52—953頁(yè)。
[9] 參見(jiàn)羅開(kāi)卷:《盜竊罪行為類型解析》,《刑法論叢》2015年第3期。
[10] 同前注[7]。
[11] 參見(jiàn)文姬:《盜竊罪中罰金刑裁量規(guī)則研究》,《南大法學(xué)》2021年第4期。
[12] 參見(jiàn)代桂霞、馮君:《輕罪治理的實(shí)證分析和司法路徑選擇》,《西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