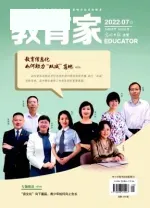“大學小鎮”鄉村振興模式的思考與探索
陳劍平

2021年4月,在寧波大學與寧波市鄞州區東吳鎮簽訂鄉村振興戰略合作協議的會上,我提出了“大學小鎮”鄉村振興模式思路框架,這是我在提出“現代農業綜合體”10年后,到寧波大學工作4年多后,就如何推動發達地區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落地實施的再度思考。
其后,我們以此思路框架為核心申報寧波市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專項,并獲得了立項支持。這一年多來,“大學小鎮”作為寧波大學校黨委、東吳鎮黨委的黨建與地方治理、高校事業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雙融雙促的高校助力鄉村振興的新模式,得到了快速發展,并初見成效。2022年9月,此模式作為教育部第五屆省屬高校精準幫扶典型項目,得到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的認同,成為高校圍繞國家重大戰略,積極推動區域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也是寧波大學履行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服務民生的職責,培養了解國情、鄉情和民情的青年人才的有效路徑。
很多人問我,提出“大學小鎮”鄉村振興模式的邏輯思維是什么。其實,大學有大,小鎮有小;大學并不大,小鎮并不小。
大學有“大”,也有“小”
所謂大學,有大學者、大教授、大學生,也有大項目、大設備、大樓,名頭夠大,氣派夠大。大學里的老師大多博學多識,有學者風范。但大學也有“小”的一面。在東吳鎮的“大學小鎮”鄉村振興實施過程中,部分參與的老師專業面窄,對鄉村的關注點比較單一,更缺乏對鄉土社會、基層政務運轉、國情農情的全面認識,有的甚至缺乏與基層干部和鄉親的共情能力。一名老師上的課,可能幾年都沒有太大變化。理論與現實之間,書本與實踐之間,缺乏生動有效的連接,缺乏產生質變的最后一躍,我覺得這就是大學的“小”。
總而言之,我們的大學老師,不能自以為“大”,因為在復雜的中國基層現實面前,很多時候我們的視野和格局都還不夠大,我們的理解過于偏執。這種格局和視野,不但對自己的研究事業發展不利,更對培養人才不利,我們培養出的學生就無法適應復雜多變、不確定性時常發生的社會現實。
小鎮有“小”,也有“大”
這里所說的小鎮,不是房地產商開發的“農業小鎮”,而是指我國最基層的鄉鎮。之所以對應“大學”稱其為“小鎮”,首先是在中國政府序列中,鄉鎮屬于最小的行政單元,全國大概有4萬多個,絕大部分出了本縣,沒有多少人知道。其次是鄉鎮的產業普遍“小”,即使是以農業為主的鄉鎮,其耕地總面積也不大。發達地區的鄉鎮都在抓工業,但基礎不牢。另外,小鎮的生活范圍“小”、眼界“小”,雖然發展的心情非常迫切,卻因為眼界的局限,存在盲目跟風的現象。
但小鎮也有“大”的一面。鄉鎮作為我國最基層的行政單元,一頭連著城市,一頭連著農村,在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鄉鎮就是這根“針”。因此,弄清一個鄉鎮的經濟社會結構和政務運轉,就可以窺視整個中國基層鄉村的經濟社會結構和政務運轉。所以說,小鎮并不“小”,折射出的是“大”面貌。
總之,小鎮既“小”也“大”,關鍵在于研究者從哪個角度去看,以及如何去挖掘、去發現,并能夠設計出獨特的產品,建立適宜的商業模式。
“大”與“小”的相互轉換
2022年,全國有4個縣級市被國務院重新定位為大城市,其中包括寧波的慈溪市和金華的義烏市。雖然這兩個是縣級市,但其體量、產值、重要性超過了一些地級城市或省會城市。這就是由“小”縣城轉換成“大”城市的例子。再舉個例子:瑞士的達沃斯小鎮,坐落于一條17公里長的山谷內,面積約28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3萬。但就是這么一個“小”鎮,竟然辦成了世界政商云集的達沃斯論壇,還在天津設了一個分論壇。義烏、慈溪“小”,達沃斯“小”,卻都辦了大事,聲名遠揚。所以一個地方的“小”或“大”,自在人為,而不在人言。
寧波大學是一所36歲的年輕大學,短時間內不大可能成為如同清華北大一樣的大學。但如果我們能夠充分利用專業齊全的優勢,動員多學科師資力量參與東吳的“大學小鎮”模式,很有可能在不長的時間里把東吳鎮建設成鄉村振興模板、全國最有標志意義的小鎮之一。
大學最重要的職責是培養人才,鄉村最需要的也是人才,如果寧波大學把人才培養放到“大學小鎮”的實踐中,讓大學生和研究生在參與小鎮鄉村振興中,設計出自己的未來,在鄉鎮中創新創業,不僅能為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戰略以及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科學設計和技術支撐,提供富有朝氣和活力的新鮮血液,也能助推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怎樣培養人才的教育改革,引導高校解決中國鄉村的“大”問題,產生創新思維和模式的轉變。這也是“小”與“大”的轉換。
“大學小鎮”鄉村振興模式的基本邏輯
地處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中國廣袤鄉村地區,鄉村振興的標準和目標當然不同。比如,目前浙江很多鄉村的經濟發展都走在了全國前列,但與真正一流的現代化鄉鎮相比,還有較遠的距離。這時,浙江應該作為深化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馬前卒,在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大戰略中繼續擔負起探索、開拓的責任。
我在浙江基層調研中看到,一些地方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面對新時代、新征程和新要求,不知道該往哪走、該怎么努力,鄉村振興不知該如何推進。因此,大學理應主動積極地參與鄉村振興,把學問和辦法用在解決基層發展的真問題上,如同當年浙江的鄉鎮企業,周末把上海工程師請來,用專家的頭腦和智慧幫助自己發展。我們寧波大學,本身就是為解決發展的實際問題應運而生的,在面對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國家戰略時,更應該向改革開放之初的浙江企業家學習,學他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股勁頭。
這也是我們嘗試用“寧波大學+東吳鎮”這樣一種“大學小鎮”鄉村振興模式來解決問題,承擔起大學推動鄉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盡責任的基本邏輯和基本考慮。
大學能為小鎮做什么
寧波的鄉村、浙江的鄉村,自然稟賦相差不多,沒有誰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和智力就是核心發展要素。永康沒有任何金屬礦藏,卻成了世界聞名的五金之都;義烏資源貧瘠,卻成為世界的小商品之都。他們能有今天,是因為他們千方百計想盡了辦法。
以知識和智力經濟看,東吳鎮的任何資源、任何要素都有市場化的可能。比如桂花樹,浙江到處都有,但為什么那么多人圍繞桂花做文章,卻都沒有做出品牌?關鍵問題在于同質化、普通化。產品無非就是桂花糕、桂花蜜、干桂花、桂花香水。如果讓東吳鎮自己去謀劃,或許也逃不出別人做過的這些產品。如果寧波大學潘天壽建筑與藝術學院的師生把桂花當成一個課題研究,在桂花上進行天馬行空的藝術創意,再過濾一下找出適合東吳鎮開發利用的資源,形成東吳鎮獨特的桂花藝術和產品,不正是東吳求之不得的嗎?所以,藝術家的創意、知識和智力產品,有著無限的可能性。
日本新潟縣南部的兩個村莊越后、妻有,位于自然環抱的山間,其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穩定的農業文明也為這片土地帶來了淳樸的美。但是,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兩個村莊與其他日本傳統村落一樣面臨著人口流失、房屋空置、空心化、老齡化等諸多問題。為尋求發展,他們找到了一位從小在新潟長大的國際策展人北川富朗,經過長時間深入思考之后,他創設了“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來到當地,把作品創作在農田和自然環境中。順勢利用逐漸荒蕪的農田、被人漸漸遺棄的農舍,把這些頹敗的因素變成了資源,通過藝術家的思考和創作,共同完成“自然擁抱人類”的主題,把城市的人吸引回自然中,重振現代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的農村。大地藝術節始于2000年,每三年舉辦一屆,辦到現在,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戶外藝術節。
過去幾年,我們也在嘗試,比如寧波大學潘藝學院在東吳鎮天童老街啟動了美術、仿古家具教學與實驗基地,我們也要為寧波的鄉村發展,絞盡腦汁。
“大學小鎮”能給大學帶來什么
對于老師而言,我們要把小鎮發展的難題和困境,作為一個課題來對待,思考出辦法,去實踐中檢驗。還是以桂花為例,如果我們真能創意出桂花產業,不可替代,那么市場一定會給出回報,而我們作為知識產權的擁有者,也同樣變成了利益的共享者。在此過程中,智力的付出對知識分子并不是負擔,而是樂趣;與鄉親們結下的友誼,更是一筆珍貴的財富。若要完成這些,絕不是輕而易舉的,對老師來說,眼下就需要跳出本專業的學習,不僅學習鄉村振興的方針政策,還要學習東吳鎮的歷史文化,學習世界范圍內農村發展的思路和經驗。對老師而言,這是一個新的挑戰。
當我們面對一個個來自鄉村發展的真實課題時,要動腦筋的不僅僅是老師,還包括同學。老師要帶著學生們到真實的鄉村世界去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認識和理解國家與基層社會的能力,今后這些學生無論從事什么職業,有了基層實踐這一課墊底,做什么都會更加實事求是和腳踏實地。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浙江農村早已不是傳統農村的概念。看看奉化滕頭村人均年收入7.5萬,一點不輸上海;看看東吳鎮的基礎設施建設,跟寧波城里沒什么兩樣。在浙江已經城市化的鄉村,要思考的是怎么能夠在高水平上創業,創出獨具一格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正給年輕人提供了無數的發展機會。寧波這座城市,務實是她的基因,開埠至今,始終如此。我們寧波大學的學生,也應該被這個優秀的特質浸染,務實地面對自己的青春,開拓自己的未來。
當小鎮發展遇到困境有求于我們,而我們無法幫他們去解決的時候,其實也暴露出大學自身存在的問題。大學的學科設置能不能有效銜接現實發展?如果不能,如何做出調整?當然,我們也會意識到其實小鎮所需要的東西,有一些我們提供不了,因為學校沒有相關的專業設置,或者沒人做過,甚至都沒人想過。那我們就可以在實踐中,根據需要調整、整合學校的專業。
寧波大學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引下應運而生的大學,生于改革開放且在寧波這個具有務實創新商業精神的城市駐扎了36年,血液里自然流淌著改革開放、敢闖敢試、創新包容的基因。希望通過“大學小鎮”這樣的模式,在鄉村振興中貢獻我們的智慧,讓老師們受益,讓相關學科受益,讓學校受益。
責任編輯:鄧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