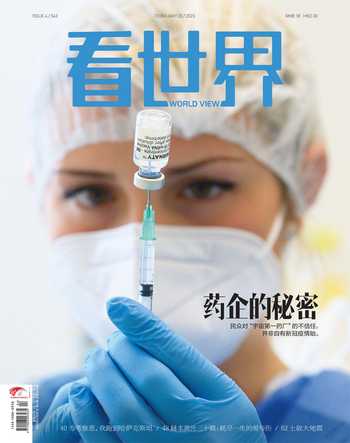赫本離世三十載:耗盡一生的愛與傷
木濃

《羅馬假日》劇照,奧黛麗飾演安妮公主
30年前,日內(nèi)瓦湖畔的一個早春傍晚,奧黛麗·赫本在心愛的18世紀石頭農(nóng)舍“和平之邸”靜靜閉上雙眼,帶著微笑的嘴角,和還沒有來得及滑落的一滴淚水。
“如果我走了,那是因為時間到了。一切都會如期而至。”離開前,她曾不止一次提到,“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她坦然接受生命的終結(jié),正如她對生命中無數(shù)次傷害的釋然:拋棄、戰(zhàn)爭、饑餓、背叛、流產(chǎn)、疾病……也正如她自若說出的:“我的人生比童話故事還精彩。我也曾遇到困境,但在隧道那一頭,總有一盞燈。”
背負著傷痛,并用更廣大的愛和力量去治愈傷痛,是因為她深信,人之所以為人,是必須充滿精力、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成長,而非向他人抱怨。她堅信并踐行了“你有兩只手,一只幫助自己,一只幫助他人”。
她風華絕代、光芒萬丈的人生沒有留下遺憾,只是到了最后,仍不明白“為什么有那么多兒童在經(jīng)受痛苦”—不是返璞歸真,而是她歷經(jīng)浮華,仍一如《羅馬假日》中安妮公主的本真。
“黑色表演”唯一的光
奧黛麗的兒子肖恩曾回憶,母親對他說過:“如果將來我要寫自傳,開頭會是這樣: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六周后,我告別人世。”
那一個春天,因為一場百日咳,這名新生兒一度停止呼吸,全身變紫,因為母親埃拉把她翻來覆去地拍打和保溫,“天使”奇跡般地重回到人間。
然而,幸存后的奧黛麗,童年并不幸福:父親對自己和其他家人異常冷漠,與母親頻繁爭吵—在許多年后,他似乎被證明了有情感障礙;生于貴族家庭的母親受過嚴苛的教育,性格嚴肅,加上經(jīng)歷第一次婚姻的失敗后,與奧黛麗的父親結(jié)合,感情又很快破裂,因此受到極大傷害,更加孤僻、挑剔,幾乎未曾對奧黛麗流露過絲毫的感情。
少數(shù)的觀眾只能保持沉默,不能鼓掌。然而,他們卻被奧黛麗稱為“我一生最好的觀眾”。

《蒂凡尼的早餐》劇照
家庭的冷戰(zhàn)、爭吵,令奧黛麗時常偷偷哭泣。渴望得到愛,也渴望付出愛,成為她終生追尋的目標。“小時候,我的夢想之一,就是有自己的孩子。”奧黛麗后來回憶說,自己看到街上或娃娃車上的寶寶就想抱,“讓母親很難為情”。
還沒來得及努力獲得父親的“回心轉(zhuǎn)意”,6歲的時候,父親突然收拾行李,一走了之;幾個月后,埃拉接到法律文件,確定婚姻告終。此后的幾十年,奧黛麗都沒有再見到父親。
被父親拋棄帶來的不安和傷心,成為奧黛麗永難愈合的傷口。然而,還沒來得及緩過神來,更大的災(zāi)難來襲。1939年5月,因為戰(zhàn)爭爆發(fā),埃拉帶著奧黛麗和兩個兄長回到荷蘭的娘家,以為找到了避難所。然而,在一個普通的早晨,戰(zhàn)火燒到了家門口。

《羅馬假日》劇照,奧黛麗以此劇獲頒1953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10歲的奧黛麗親眼見到德國卡車駛進市內(nèi),5天之內(nèi),荷蘭淪陷了。幾世紀積累的財富帶給埃拉家族的安穩(wěn)生活,一瞬間化為烏有。小奧黛麗被迫提前明白人性的冷酷:“我親眼看見它、感覺它、聽到它—它永遠不會消散。”
那不只是噩夢,因為她就在現(xiàn)場:戰(zhàn)火蔓延,肺結(jié)核暴發(fā),敵人對居民的掠奪和居民之間的搶奪,父親的缺席,兄長的失蹤,唯一的舅舅被迫害……恐懼、饑餓、寒冷、疾病、絕望肆虐,這個“人間地獄”里唯一的光,是小奧黛麗依然不愿意放棄的芭蕾舞。
她深深熱愛著芭蕾舞,無數(shù)次想象過成為一名舞者。在黑暗時期,想要跳舞的熱忱,仍遠大于對德軍的恐懼,她用“黑色表演”延續(xù)自己的夢想—和幾位同學冒險私下做舞蹈演出,為反抗軍籌款。表演場地的門窗緊閉,少數(shù)的觀眾只能保持沉默,不能鼓掌。然而,他們卻被奧黛麗稱為“我一生最好的觀眾”。
1945年5月4日,奧黛麗16歲生日那天,自由終于來到,兩名兄長陸續(xù)歸來,一家終于團圓。或許是此生第一次,她看到母親的臉上流下淚水。6月,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送來救難物資,奧黛麗和整個家族都參與了發(fā)放救援物資的工作。“這基于己饑己溺這個美好的古老觀念,是我所受的基本教養(yǎng)—其他人比你重要。”奧黛麗后來說,所以要如母親所言“不要抱怨,只要接受”。
《修女傳》改變靈魂
1945年夏末,奧黛麗和母親住進阿姆斯特丹一間診所,義務(wù)負責各種雜務(wù),直到1946年初完成任務(wù)。埃拉找到廚師的工作,支付生活所需和女兒在芭蕾舞學校的學費。
那年夏天,長久以來的困頓生活終于擊倒了奧黛麗,她第一次受憂郁之苦,且一生受其折磨:長時間昏睡、抑郁消沉、沉默寡言……這種情況直到年底有所好轉(zhuǎn),埃拉得到帶領(lǐng)女兒前往倫敦學舞的建議,并毅然決定前往。埃拉,這位不茍言笑又堅強剛毅的曾經(jīng)的女爵,用整理垃圾、洗刷樓梯的管理員工作,支撐女兒的夢想。
然而,現(xiàn)實總是不如人意。即使醉心苦練,奧黛麗還是不得不接受事實,錯過了最佳學習年紀的她,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名專業(yè)舞者。
懷孕的好消息僅短時間令其振奮,因為流產(chǎn),她又被打擊得心智渙散。
生活不允許自己在夢想破碎的痛苦中沉溺太久,奧黛麗找到了劇團的表演工作,同時兼做模特。她既可愛,又孤單無助、需要拯救的特質(zhì)難以言喻,得到眾人的喜愛。工作的伙伴們隱隱感覺到,“她遲早會成為明星”。

《修女傳》劇照,奧黛麗飾演路加修女
1951年11月,《金粉世界》上演,奧黛麗在兩個小時內(nèi),經(jīng)歷了從默默無聞到一炮而紅,成為百老匯家喻戶曉的明星。而真正令她成為時代傳奇的,是經(jīng)典之作《羅馬假日》。也許,其實是她成就了《羅馬假日》的經(jīng)典—即使在當時,人們也評價,如果沒有奧黛麗,《羅馬假日》只是一部“平庸的感傷之作”。
1953年,奧黛麗以《羅馬假日》獲頒1953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并獲得多個大小機構(gòu)的獎,不到25歲,便已經(jīng)獲得老練的專業(yè)演員即使花費數(shù)年或數(shù)十年也未必能得到的成就。
帶來的除了機會和榮耀,還有巨大的壓力和不安。“就像有人給你一件太大的衣服一樣,你得長成那個模樣。”帶著對自己極高的要求,她長時間承受著精神崩潰的折磨。1995年3月,懷孕的好消息僅短時間令其振奮,因為流產(chǎn),她又被打擊得心智渙散—這種致命的打擊,在她的一生中出現(xiàn)了5次之多。
盡管一生中的數(shù)十部電影作品中不乏重要之作,但最為關(guān)鍵且改變她的,是以凱特和路加兩位修女為原型的《修女傳》。奧黛麗在故事中,找到許多她所傾慕并認同的特點,而兩位修女對她的一生也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親愛的靈魂即將蓬勃發(fā)展,更加深入,甚至超越她自己的期望。”
她曾在給凱特和路加的信中寫下:“探究路加修女的心靈和想法,讓我不得不深入探索自己。如此這般耕耘我的靈魂,我所體驗的一切已經(jīng)在沃土中播下種子,希望能收獲一個更美好的奧黛麗。”她在復(fù)活節(jié)的電報上寫下:“喜樂復(fù)活節(jié),你們摯愛的奧黛麗修女。”在她隨后的人生中,在鏡頭之外、舞臺之下,她洗盡鉛華,一如修女一般,保持著簡樸單純的生活。
她晚年的親密友人羅伯特·沃德斯說,這部影片和劇中角色,最像她在騷動混亂中的時刻,在她面對難解的困境時。29歲的奧黛麗,在路加修女身上感受到了一種“期待更多”的渴望,同時明白自己正朝某處邁進,盡管還不清楚目標和方向。
用愛和寬恕包容棄養(yǎng)父親
肖恩說,奧黛麗堅信愛能治愈任何傷口,而且會讓生命變得更美好。他形容自己的母親就像生長在陰暗處的樹木,盡管見不到陽光,樹枝還是會千方百計地向陽光的方向生長。
肖恩是奧黛麗的第一個孩子。1960年,當他出生的時候,奧黛麗終于感受到美夢成真的喜悅。對于她來說,電影不過是童話故事,和兒子在一起的才是真正的自己。1967年,為了兒子,奧黛麗成為了一名全職媽媽,過著平淡的日常生活,并于1970年41歲時,生下了第二個兒子盧卡。

1988年3月,奧黛麗在埃塞俄比亞援助當?shù)貎和?/p>
來勢洶洶的病情,只留給她兩個多月時間,去告別這個深深愛著的世界。
擁有兩個孩子,充分慰藉了她在情感上的缺憾,但同時她也不得不經(jīng)歷了兩段以被背叛收尾的婚姻。肖恩后來說,也許部分原因是“在整個童年都被控制欲極強的外祖母弄得筋疲力盡之后,母親希望能夠過感情自然流露的生活,但是她選中的兩個男人都并不適合這樣的生活,他們都需要學習如何去處理自己的感情”。
事實上,奧黛麗的父親和母親都需要學習如何處理自己的感情。劇作家里歐納·蓋許與埃拉成為朋友后發(fā)現(xiàn),她“和奧黛麗一樣很有幽默感”,但兩母女“不能共享歡笑”:“埃拉扮演的是嚴母的角色,一提起女兒,就變了個人—喜歡批評奧黛麗的作為,但另一方面,埃拉傻起來很傻,就像奧黛麗一樣。只是她們不知道母女倆其實很像。”
奧黛麗說,母親從未向自己表達她的愛,但她知道母親對自己的疼愛,為自己所做的犧牲:“若非母親,我一定會迷失。她一直是我的共鳴板,是我的良心。”
而因為奧黛麗的堅持,她終于找到多年杳無音訊的父親。即使重逢時,父親依然如此漠然,對女兒的擁抱無動于衷,但奧黛麗在擁抱的瞬間,已決定原諒他—她已經(jīng)釋懷了,不再為他帶來的傷害抱憾。此后,她贍養(yǎng)父親和他的妻子至終。而他直至去世前,才終于向別人坦承自己的遺憾,及為女兒感到驕傲。
用愛和寬恕包容他人,也許是因為她始終認為,施比受有福,施予就是生活。“如果你不再想施予,就沒有生活的目標。”1988年3月1日,奧黛麗正式申請成為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親善大使。
接下來5年,她四處奔波,到世界的窮鄉(xiāng)僻壤去,討論無家可歸的兒童、消除貧民窟,以及提升婦女權(quán)利的計劃,直到1992年11月1日,她被發(fā)現(xiàn)盲腸里長了惡性腫瘤。來勢洶洶的病情,只留給她兩個多月時間,去告別這個深深愛著的世界。
“她就像彩虹盡頭那罐黃金。”導(dǎo)演史丹利·多南說。奧黛麗·赫本,一個遙遠的名字,一個美好的似夢非夢。也許彩虹是她來時的路,也許彩虹消散時,我們也不敢確定,她是否來過這人間。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