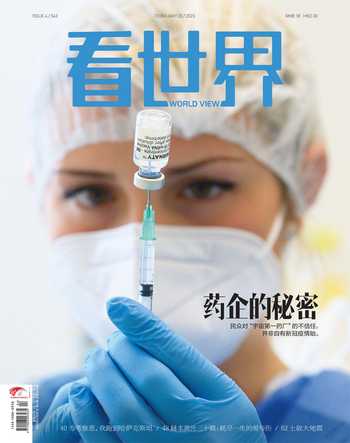艾滋藥在南非

鄧晨
自從1980年代末醫學界開始運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艾滋病,至今已經有超過25種藥品進入市場。它們通常都是用來阻礙艾滋病毒利用宿主細胞復制下一代的過程。例如,早期的“齊多夫定”瞄準的是“逆轉錄酶”的運作,目前最多使用的藥物之一“多替拉韋”針對的是“整合酶”,近年來展露希望的長效型藥物如“來那卡韋”則是阻止病毒外殼破裂,使其無法釋放遺傳物質。
藥物意味著患者活下去的機會,當藥廠越堅持制藥專利及利潤,則等同于增加醫療機構或患者的購買成本。然而,藥廠也宣稱藥物從研發、臨床試驗到生產營銷是復雜而昂貴的過程,成功的新藥背后有著大量的試錯及失敗的嘗試,還要加上其他藥廠的競爭風險。從患者、藥廠到政府都有各自的需求出發點,加上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不同的議程便產生了沖突和角力。
南非是世界上艾滋患者最多的國家,這來自早期疫情未獲有效處理。前總統姆貝基當年宣稱艾滋不是病毒造成,政府官員還建議民眾采用偏方。這其實也與南非政府對國家處境的意識有關:廢除種族隔離體制及殖民的遺產是其首要關注,主張社會面的改造才是解決衛健問題的根本。姆貝基認為,花費高昂的經費向歐美藥廠購藥只會加劇跨國依賴。
1997年時南非當局立法引進較便宜的仿制藥,結果遭到39家國際藥企聯名控告侵權。基于南非等非洲國家基本不可能負擔高昂藥價,國際輿論普遍批評藥企的行為,終使得藥廠在2001年降價并授權南非企業生產。官方雖然放開醫院使用新型藥物,但推行力度十分有限,待到2008年姆貝基下臺后才全力推動。這對患者來說已經來得太晚,數十萬患者失去了生命。
由于新型藥物的使用,艾滋病患如今只要長期服藥便可妥善控制,艾滋不再是無法治療的絕癥。南非經濟困難而且有著大規模貧困人群,要為數百萬患者提供終身的免費藥物,需要巨大的經費支出。南非去年向藥廠爭取到每名患者每月約26元人民幣的藥價,這較原本的價格降低了三成,不過整個治療體系仍然高度依賴外援資助,無法只靠本國財政支撐。
為了縮短患者與治療資源間的距離,南非的醫療體系將開處方藥的權力下放到護士及藥師;把取藥點從診所轉至大街小巷的藥局,使得患者更容易取藥且不需面對異樣的眼光。基于貧困社區需要更多宣傳及協助,政府培訓大批衛健人員進入社區協助病患;為了降低長期規律性服藥的門檻,近期衛生部準備試點每月注射一次的長效型預防針。
強調艾滋傳播的社會面有其原因。比如,南非患者的女性多于男性,以及疫情在貧民窟的傳播,這些就與貧困社區的生活狀態及性別觀念有關,來源于不平等的性關系或缺少防護的性關系。但是,南非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造是緩慢且困難的,而藥物對身受病痛的患者提供了快速的幫助,這可能是患者“回到社會”的第一步。
艾滋病是南非貧困問題的要素之一,患者因此喪失經濟能力或遭遇人際障礙。如今,藥物讓患者可以像非患者一樣交友、工作或生育。南非目前或許因此是一個“依賴藥物”的國家,但隨著醫療的進展,將來也許會迎來根治艾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