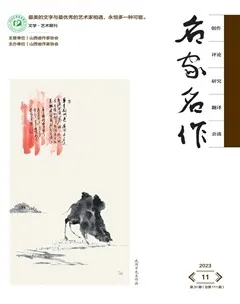于堅自然主題詩歌意象分析
馮雯莉
于堅是“第三代詩”或“后朦朧詩”詩潮中的代表人物,“70 年代初開始寫詩,1979 年在正式出版刊物上發表詩作。在80 年代初的新詩潮中,曾是‘大學生詩派’的主要成員,與韓東、丁當等創辦民間詩歌刊物《他們》。他曾將自己80—90 年代的寫作分為三個階段:80 年代初以云南人文地理環境為背景的‘高原詩’;80 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口語化寫作;90 年代以來‘更注重語言作為存在之現象’的時期”①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317 頁。。對于于堅的“高原詩”時期的詩歌研究是相對較少的,因為這一階段的詩歌還沒有很明顯地體現出他鮮明的詩學理論,但其思想內涵及優美的藝術風格和抒情性,仍然使其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很有研究的必要。
詩歌是人主觀情感的表達與抒寫,詩歌與自然的關系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界是詩人們汲取靈感和題材的源泉,對自然的描繪無法擺脫詩人的主觀意識和態度。于堅詩歌對于人與自然的認識,就是崇敬自然、尊重自然、熱愛自然、回歸自然,他筆下的自然世界正是將這種情感作為依托建立起來的。本文將集中解讀于堅自然主題中怒江、雄鷹、大樹的詩歌意象,闡釋于堅詩歌創作的自然觀。
一、于堅詩歌中的自然世界
閱讀于堅以云南人文地理環境為背景的‘高原詩’,會發現于堅詩歌內容中一個重要的元素:自然。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云南紅土地上的詩人,他用他的詩建構起一個詩意的自然世界,這個世界中大到高原山峰、河流,小到花草樹木、野獸蟲魚,都被作者升華充滿著原始的神性光輝。在詩人的放大鏡下,它們的形象超凡脫俗,異常強大,甚至一度超越人類,作者在此并非過多地歌頌這些自然事物對人類的益處、與人類的緊密關系,而是更多地展示這些自然事物真實的生命,致力于還自然以本真,是純然的自然、獨立而未被異化的自然。這些詩有著傳統的自然意象,滲透著自然之美、人文情懷,表現出詩人對于人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渴望以及敬畏自然的思想,使當代讀者更易于理解、接受。筆者將舉出一些于堅有代表性的自然主題的詩歌加以解讀,主要對其中蘊含的自然意象作出分析,以揭示這類詩歌的共性。
二、于堅自然主題詩歌意象
(一)怒江:詩歌中的智者
在我故鄉的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會聽到人們談論這些河
就像談論他們的上帝
—— 于堅《河流》②本文所引的于堅的詩歌若無特別注明,皆出自《于堅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版),以下不一一注明。
20 世紀80 年代,于堅對云南高原上河流的寫作在他的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并在藝術水平上取得較高的成就。怒江是于堅鐘愛的一條河流,經常出現在他的文本中。在《怒江》一詩中,怒江是一條逃離文化、逃離隱喻的河流,它孤獨地前行,但這條被詩人遺忘的、陌生的河流,仍默默地滋養著云南大地,使萬物生長,“在遙遠的西部高原它進入了土層或者樹根”,這正是它的作用。作者在這里沒有歌頌那些被稱為“父親”的河流,歌頌的是一個無名小卒,一條云南的大江,它不慕虛名,不求被歌功頌德,不求居于政治話語的圈子內,但仍可滋養萬物,繁衍新生,起到一個“父親”的作用。這種默默奉獻的精神、堅忍的力量,正是于堅所歌頌的。還原一條普通河流的本真面貌,不虛偽、不浮華,它只是代表萬千被隱沒的河流,為它們說話正名。
在于堅筆下,怒江的形象并不美觀,它沉默、粗獷、豪放,“怒江的濤聲使人想犯罪”,它是“道烏黑的光”,“披著豹皮”穿梭于高山之上,這正是它原始真實的形象。但試看于堅的《橫渡怒江》一詩,怒江卻是披著智者的光環登場的。
在詩作開篇,于堅巧妙而形象地將在暮色時分流淌的大怒江比作晚年在峽谷間散步的大哲學家康德,這一比喻是突兀而新穎的。于堅在此正是要突出他們兩者——大怒江與大哲學家康德——的“神似”。怒江的流淌被作者賦予了意義,而不再是無意義的流淌,開篇作者就試圖告訴我們,這條河流并不簡單,這一比喻已將現實中的怒江升華為詩歌世界中的怒江,怒江有了哲學思想,不再僅僅有形象,它被賦予了一種康德式的理性的哲學品質,并被納入了永恒的范疇,成為一條有著哲學品質、有思想的精神性的大江。這注定了怒江的不平凡。可悲的是,怒江的思想卻只能被“石頭看見”。
第二節,詩歌寫出了普通人面對“永恒”時的無知,千千萬萬年,怒江沉默地流淌著,滋養著人們,它的思想卻不被人知。接下來,于堅又將怒江比作“一身黑衣的大法官”,“千千萬萬年”來一直冷靜地審判著我們匆匆的生活、狹隘的生活。詩歌第三節,怒江更成為一面閃閃發亮的鏡子,能照出人心的善惡,它永恒地審視著過江的人們,而奔忙于自己生活的盲目無知的人們卻只是一閃而過的影子。面對永恒的怒江,人只是匆匆而過的影子,人類在此不具有實體,人靈已在人世的匆忙中岌岌可危了,沒有了靈魂的人類在詩人眼中正像是影子一樣,而怒江仍保持著靈魂。在詩歌最后一節,作者寫道:“無論他們朝向哪一岸/革命或者叛徒/都一樣要面對怒江。”這強化了怒江的永恒性和精神性。怒江成為人們反觀自身的地方,在這里,人們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回歸內心開啟尋找自己的精神之旅,是否需要渡江。
回到詩歌的題目——橫渡怒江,于堅所認為的“渡江”其實只是一種精神性的渡江,是一種精神上的歷練。面對怒江,面對永恒,人們要做出自己的選擇,是選擇渡江還是逃走。在此,渡江成了精神修煉、提升的過程,跨越了這江面,也就是敢于正視自己的內心,精神就此可以抵達更高的境界。于堅正是將永恒的、精神性的怒江與盲目無知、生命短暫的人類進行對比,以攻破人類中心論,自然只能是人們崇拜的對象,人們對自然只能是無條件信仰、無條件敬愛,與之融合,和諧相處,這樣才能找回人的精神家園。
這樣怒江的形象就圓滿了,它既有外在形象,又有了內在的精神,且二者渾然一體,成了一個完整的意象,其代表于堅對怒江、對自然的一種態度,一種對自然的最高度的崇敬,人類需要借回歸自然而尋回人類逐漸丟掉的精神價值。
(二)雄鷹:詩歌中的帝王
在更高處 在靠近天空的部分
我看見兩只鷹站在那里 披著黑袍 安靜而謙虛
——于堅《避雨之樹》
鷹的意象在于堅詩歌中多次出現,它像一個活躍的精靈穿梭于詩行中。除在其他詩篇中的描寫,1979 年,于堅創作了《鷹·第一首》,1984 年創作《鷹·第二首》,1987 年創作《鷹·第三首》,對鷹的書寫是和作者的內在精神氣質相通的。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首先,于堅敬畏原生態的自然,他筆下的雄鷹更是戰士的形象,他對鷹的書寫正和他的自然觀一致。于堅寫出了鷹的神性,如鷹“只是隨便扇扇翅膀就超越了一切哲學宗教和詩歌”①于堅:《一枚穿過天空的釘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04 頁。。鷹是一個被于堅無限歌頌和崇敬的對象。《鷹·第一首》,“今天早晨一些鷹起飛了/飛過窗外的高山/世紀已晴朗/風暴不知去向/巖石上紅銹斑斑/革命時代/它們是部落的圖騰/和英雄們一起出征/黑色的領袖/率領無數天空/滾過隆隆的硝煙/啊鷹你永遠的誘惑啊/就要攪動我的靈魂/使我日夜不安”②于堅:《一枚穿過天空的釘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32 頁。。鷹作為一個英雄的象征, 受人尊敬。于堅熱愛自然,渴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他認為人類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和自然平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應該和自然平等對話,和諧共處。比如“鷹在我腳下的天空翱翔,風在我耳旁的森林喧響,我安靜如高原,撥開白云,望見山地在遠方”“我撥開白云,我走過鷹的身邊,我走下陰郁的高山,和陽光一起流向大地,和大地一起長滿陽光”③于堅:《一枚穿過天空的釘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33 頁。。可見,在于堅的世界中,人類是可以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而且于堅更將自然放到和人類平等的位置來書寫,以此提高了自然的地位。
其次,在一個詩歌不斷被邊緣化、精神衰微的時代,于堅堅守著他的詩歌理想,他說,“在任何方面,我都可能是一個容易媚俗或妥協的人,惟有詩歌令我的舌頭成為我生命中唯一不妥協的部分。”④于堅:《〈于堅的詩〉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第400 頁。他詩歌中鷹的堅韌不拔的形象正昭示詩人堅守理想的信念。在《鷹·第一首》中,鷹代表的就是一種高度,一種詩歌的立場。鷹在天上展翅高飛,比所有的人都接近太陽,因此,鷹的意象在于堅筆下象征著高度,是一種信仰、理想。在《作品57 號》中,鷹是堅韌的、不妥協的,如同山峰一樣,它象征著詩人不屈不撓的靈魂,那顆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保持精神獨立的靈魂。它曾是帝王部落的圖騰、英雄的象征,但如今英雄寂寞,這個英雄只能出現在詩人心中,成為其詩歌中的帝王,統領其詩歌的靈魂。
最后,鷹高踞于蒼穹之上,人們在仰望天空的時候,往往可以看到鷹,天空成了鷹的棲息之所,這是一般鳥類無法企及的高度,也只有鷹才能達到如此高度,高處不勝寒,因此,鷹往往是孤獨的,它獨享著天空——那片最后的自由天空。于堅羨慕鷹所擁有的自由和高度,因為在天空中更便于與世界進行對話,鷹的孤獨正是于堅孤獨的內心的體現,他在孤獨地舞蹈,孤獨地作詩,保持著精神上的獨立,堅持追問那更高的存在世界。
(三)避雨的樹:詩歌中的母親
于堅對自然懷有深沉的愛戀,自然在他的筆下都被賦予了神性,他敬畏自然、感激自然,因為他知道自然才是生命的源頭、萬物的始祖。避雨的樹體現了于堅對一棵高大的榕樹所懷有的愛,這愛正像是對自己生母一般的深沉厚愛,是作者將自然作為人類棲居之所的意識和生態意識。這棵高大的榕樹以博大的胸懷包容了大地上的一切生靈,包容了于堅詩歌中眾多重要生靈。大樹深深扎根于大地,就像全部詩歌的總干,包納了于堅詩歌的眾多元素、情感和精神。
在詩中,“我”是一個避雨的人,和其他避雨者一樣,依偎在這棵大樹的懷抱下,躲避一場暴雨。大樹張開它的手臂無私地把人們全部庇護在它的懷抱里,互不相識的人們躲避在樹下,接受它的饋贈,人們“一齊緊貼著它的腹部”,如同初生兒在母親胸懷中獲取安全一般,“它的氣味使我們安靜/像草原上的小袋鼠那樣/在皮囊中東張西望”。這樣,一幅母親為孩子遮風擋雨的場景仿佛浮現在我們眼前,使于堅從中感受母親的氣息,獲得母親的溫柔。“它是那種使我們永遠感激信賴而無以報答的事物/我們甚至無法像報答母親那樣報答它/我們將比它先老/我們聽到它在風中落葉的聲音就熱淚盈眶/我們不知道為什么愛它 這感情與生俱來”。這就是于堅對這棵大樹的深情厚愛,如對母親的愛和感恩一般,這種奉獻是人類永遠無法報答的,因為人類的時間與自然的時間相比,人類的生命是短暫的。這棵樹提醒人們春天的到來,但現在的人類是如何對待這如同母親的大樹的呢?我們給予它的是斧子,把它的肉切開,用作冬天取暖的柴火。我們給它的是死亡,“這死亡慘不忍睹這死亡觸目驚心”,這是對人類莫大的諷刺,人類喪失了報恩之心、敬畏自然之心。我們尚且連報恩都無以為報,卻還不斷地傷害它,這是于堅對人類的痛斥,對自然遭到破壞的憤慨。
一棵永恒的大樹,永遠是人類最終的避難所,是人類最終的家園,它是人類最后的拯救和歸宿。“雨停時我們棄它而去/人們紛紛上路/鳥兒回到天空”,大樹從不會抱怨人類,它仍在無限次地包容人類、庇護人類,難道這還不足以使人們感恩于自然的饋贈、愧疚于我們對自然的破壞。最后,作者給了這棵大樹一個美好的結局,“那時太陽從天上垂下/把所有的陽光奉獻給它……像一只美麗的孔雀/周身閃著寶石似的水光”。雨過天晴,太陽出現,再次給予大樹以陽光滋養,大樹再給人類滋養庇護,大自然就是這樣不斷地護佑人類。最后,大樹再一次煥發精神,透露神性,散發出詩意的光芒。
三、于堅自然主題詩歌觀
怒江、雄鷹、大樹,它們脫離世間俗物,無功利、無畏淡定的存在,它們不僅給人類提供物質材料,更成為人類精神世界的支撐,成為人類生命的庇護。永恒、神性可以說是于堅筆下自然存在的常態,自然萬物都超越了生死的阻隔而精神永恒地存在于他的詩作中,這也是于堅寫作的一個宗旨:為永恒而寫作。
通過對于堅自然主題詩歌創作中的意象分析,并結合一些重要的詩歌文本,我們發現,這些意象都體現著作者的思想、情感、理想,與作者的精神氣質相通,同時這些意象也構成了于堅優美而神奇的自然世界。于堅對自然淳樸的感受和書寫,嘗試還自然本真。他批判了人類中心論,尊重自然生命,揭示了自然的神性、永恒性和精神性,渴望人與自然“天人合一”。面對人與自然關系不協調的一面,詩人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生態立場,用詩歌的精神、真誠的情感喚醒人們沉睡的心靈,正是于堅詩歌的價值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