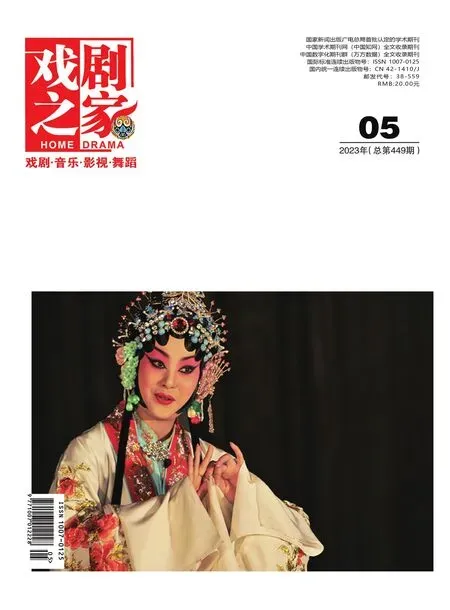公案戲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路徑新探
王艷梅
(重慶人文科技學院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慶 401524)
戲曲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挖掘優秀戲曲文化資源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戲曲文化實現新發展的必由之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1]。2017 年1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下簡稱“兩創”方針)的內涵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秉持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揚棄繼承、轉化創新,不復古泥古,不簡單否定,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不斷補充、拓展、完善,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并將“實施戲曲振興工程”“挖掘整理優秀傳統劇目”作為重點任務之一[2]。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則將“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納入“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范圍[3]。作為中華戲曲的優秀傳統劇目,公案戲因其獨特的創作題材、超然的審美情趣、針砭時事的社會面向,備受大眾青睞而長盛不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客觀審視公案戲的發展源流、文化意涵,探討公案戲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新路徑,無疑對滿足民眾的文化需求,促進戲曲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
一、公案戲的界定
公案一詞最早源自“說公案”。《都城紀勝》記載:“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樸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4]明清時期涌現了大量以“公案”為題的作品,這些作品以懲奸除惡、洗冤雪枉為內容,逐漸引起人們對公案題材的關注。1934 年,鄭振鐸在其《元代“公案劇”發生的原因及其特質》中對公案戲做了開拓性界定。他指出,“‘公案劇’是什么?就近日所傳的《藍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包公案》《海公案》一類的書的性質而觀之,則知其必當為摘奸發覆,洗冤雪枉的故事劇無疑”[5]。由是觀之,可以得出公案戲三重特征,一是以訟獄事件為主題,二是以社會問題為主線,三是以平冤昭雪為結局。這三重特征交相輝映,促進了公案戲的繁榮發展。
二、公案戲的發展源流
公案戲以懲惡除奸、洗冤雪枉的清官良吏斷獄為核心母題,在不斷發展過程中構建起獨特的敘事話語與表現程式,甚至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道德準則、行為規范。梳理公案戲的發展源流,有助于我們從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理解此劇目的文化意涵。
(一)元雜劇與公案戲的發展繁榮
公案戲是元雜劇的重要組成部分,元代是公案戲發展的高峰。這與元代的社會制度密不可分。首先,元代實行民族等級制度。元朝政權建立后,按照民族所屬將全國民眾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這四個等級在政治、文化、經濟上的待遇各異,從而導致權豪勢要橫行、社會秩序混亂。其次,元代法律對不同等級寬嚴不同。特別是對特權等級的袒護,導致法律不公,出現特權等級違法亂紀,而法律執行無力的現象。如《元史·刑法志》中的“八議”制度就規定了刑律對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八類人的減免制度。再次,科舉取士長期廢止,文人地位低下。從太宗九年(1237)至仁宗延祐二年(1314),元朝廢止科舉考試長達78 年。科舉入仕之路中斷,戲曲創作成為讀書人借以“澆心中之塊壘”的最好方式。公案戲作家們突破了宋代說公案的“樸刀桿棒及發跡變泰”題材,從而轉向以揭露權豪勢要胡作非為的案件為主要表現內容,暴露社會的黑暗。
(二)明清傳奇與公案戲的傳承革新
明、清是戲曲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時期,其突出的表現是傳奇取代雜劇成為戲曲舞臺的主角。傳奇,源于宋元南戲,是南戲發展到明中葉成熟化和規范化的結果。相對元代而言,明清公案戲要遜色很多,用雜劇體制創作的公案戲基本以元代公案戲為藍本進行改寫續編,沒有突破,整體成就不高。傳奇作為與雜劇不一樣的戲曲形式,在承襲元雜劇公案戲模式的基礎上,以傳奇的樣式為公案戲的創作注入了新元素。
傳奇給公案戲帶來的革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體裁結構創新。元代公案戲結構為一本四折加一楔子。雜劇結構模式固定單一,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劇作家的創作。傳奇的篇幅,少則十幾出,多則幾十出,這給作家創作帶來了自由的發揮空間。比如,《十五貫》有二十六出,《吉慶圖》有三十二出。劇本容量的增大,使得故事變得撲朔迷離,更具趣味色彩。二是人物形象塑造更為豐滿。元雜劇演唱體制的特殊性決定每折唱詞只能末、旦演唱,其他角色一般只有賓白。明清傳奇的演唱方式有突破,除了生旦,其余角色也能演唱。演唱方式多樣化,極大地豐富了舞臺的表現力,也讓劇中人物更為多面、立體、豐滿。三是公案戲的素材選擇更加注重民眾日常生活。元代公案戲主要聚焦權豪勢要類犯案者,明清公案戲訴訟事件的取材主要來源于大眾的日常生活。
明清公案戲在傳奇的影響下,產生了體裁結構、人物形象塑造、素材選擇方面的創新,為清中葉以來地方公案戲的發展繁榮奠定了基礎。
(三)“花雅之爭”與清中葉以來地方公案戲的百花齊放
所謂“花雅之爭”,是指清中葉以來,諸多新興聲腔劇種參與競爭演出爭勝的戲曲運動。“花”為花部亂彈,泛指昆山腔以外的各種地方聲腔劇種,“雅”為昆山腔,即昆曲。隨著花部亂彈聲音益隆,地方聲腔蓬勃興起,經過三輪舞臺競勝較量,花部諸腔最終以“其文直質”“其音慷慨”的優勢取代昆曲在劇壇的王者地位。“花雅之爭”是戲曲雅化階段的一次“涅槃”,是戲曲迎合民眾審美需求、追隨時代發展步伐的一次嘗試。這種嘗試帶來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推動地方戲的蓬勃發展;二是促成戲曲重心實現由文本到舞臺的轉移。
在“花雅之爭”的助推下,公案戲被改編成各種地方戲,通過舞臺展演形式廣泛流傳。比如,包公戲就包括京劇《鍘美案》《打龍袍》,川劇《破鐵劵》《沖霄樓》,徽劇《鍘包勉》,花鼓戲《包公斬判官》等。豐富的地方戲劇種,別樣的表演形式,極大地促進公案戲的繁榮興盛。
三、公案戲的文化意涵
從發展繁榮到傳承革新及至百花齊放,公案戲對社會問題的揭露,對民眾心聲的關注,對社會價值觀的傳揚構成了其文化意涵的核心。這也是該劇種能在民間廣為流傳,被大眾廣為接受的主要原因。
(一)公案戲承載著民眾對公平法治的渴求
著名漢學家韓南指出,罪與罰是中國傳統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它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公平法治觀念。縱觀歷代公案戲的核心主題,揭露當時社會制度的不公平、法律的不公正,表達民眾對公平法治的渴求是其重要主旨。為此,公案戲塑造了眾多權豪勢要,揭示其罪惡行徑。例如,《蝴蝶夢》中的葛彪,《生金閣》中的龐衙內,《陳州糶米》中的劉衙內等,皆為權豪勢要之家,無視法紀,草菅人命。面對貪官污吏、權豪勢要的罪與惡,公案戲作家們只能通過戲劇塑造出包拯、張鼎等一批清官,并以清官為民做主,惡人最終伏法的結局,經由“藝術正義”滿足民眾對公平法治的渴求。
百姓崇敬清官,奉之若“神”,間接反映出封建社會的黑暗,也反映出為民請命的清官極為罕見,如鳳毛麟角。百姓對于清官的祈求是一種心理的“幻想”,也是對公平法治的期盼。
(二)公案戲對“正義”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傳揚
公案戲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傳揚,主要體現在其對儒家文化中“正義”思想的彰顯。儒家正義論思想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以“仁義”為基礎的“義”,其強調人的德行,是一種德性的倫理;二是以“仁”為價值基礎,以“正”為核心內涵,以“中正無偏”為實踐途徑。孔子“以直報怨”是儒家正義論思想的核心,“要通過這種以直報怨的方式,讓對方明白錯在什么地方,從而起到抑制惡行、維護正義的作用”[6]。儒家正義論思想始終貫穿公案戲作品。比如,公案戲《陳州糶米》細膩展示了包拯與權豪勢要勢不兩立的精神風貌。《勘頭巾》中,六案都孔目張鼎冒著天大的風險,在三日期限內勘出案情真相,讓真兇劉妻和道士伏法,王小二獲釋。
正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理念,被視為天地之道,人倫之本。道德和法律則是維護社會正義的基石,道德以內在良知來維護社會正義,法律則以外在制度來保障社會正義,二者在公案戲中得到有力詮釋。
四、“兩創”方針與公案戲發展路徑的新思考
如前文《意見》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內涵的詮釋,在“兩創”方針指導下,公案戲的當代發展路徑需結合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要求,創新其表現形式、傳播方式,賦予其新的文化內涵、文化功能,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積極因素。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方面創新公案戲的發展路徑。
(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改造公案戲的法治思維
公案戲是中國人“法治之夢”的藝術體現,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民眾追求公平、正義的法治思維。此類法治思維在公案戲中,表現為簡單粗暴的“復仇”類“還報”觀念與借助鬼神啟示斷案、判案。如《蝴蝶夢》中,王家三子的罪行得到赦免并加官賜爵。在《生金閣》《竇娥冤》《盆兒鬼》中,均有鬼魂訴冤而使沉冤昭雪的情節。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改造公案戲的法治思維,可以從如下兩方面入手。一是摒棄公案戲中簡單粗暴的復仇、替天行道等觀念,在各類以公案戲為藍本創作的文藝作品中,更多融入依法斷案、公正判案、公平執法、執法為民的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引導民眾形成對法律的敬畏之心和以法律為準繩懲治違法犯罪的思維。二是在以公案戲講好當代中國法治故事的過程中,改造公案戲中清官個人崇拜、神啟斷案等文化元素,強調以法律為準繩的清官形象,以法律為標尺的執法過程,從而為公案戲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注入時代活力。
(二)推陳出新,打造與時代精神吻合的高品質文化作品
公案戲推陳出新體現為結合時代精神,在繼承優秀傳統劇目的基礎上,創造與時代精神吻合的高品質文化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依據時代精神對公案戲的推陳出新從未中斷。如1956 年浙江昆劇團對公案戲《十五貫》的改編引起一時轟動,被周恩來總理稱為“改編古典劇本的成功典型”。《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從“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談起》的文章,稱贊此劇是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戲曲改革方針的榜樣。隨后,戲曲界掀起各劇種改編《十五貫》的浪潮。2018 年,全國首部原創越劇花臉劇目《包公淚》,在繼承古代廉政思想文化的同時,更是從人性角度展現包公鮮為人知的一面,從而讓包公故事煥發出與時俱進、積極向上的活力。
由是觀之,打造與時代精神吻合的高品質文化作品,不僅能夠為傳統劇目注入新的活力與時代氣息,而且對優秀傳統劇目的當代傳承、保護有重要意義。
(三)以互聯網+,創新公案戲的傳播形式
當前,公案戲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需要借助互聯網+,采取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的傳播形式。如2018年,光明網推出了“你好,新時代——中國戲PICK ME”大型直播活動,通過“傳統戲曲+網絡直播”的新形式,有力實現了藝術普及、文化輸出,全面推廣傳統戲劇形式。據統計,當年直播累計觀看量超過1000 萬人次。公案戲的傳承創新可以借助數字人文技術、VR/AR/MR(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混合現實技術)等來實現其數字化展示。通過采取優秀劇目開發、現場點播、線下展演的一條龍模式,衍生開發電影、動漫、公開課等,以此實現公案戲的跨越式發展。
五、結語
戲曲蘊含著優秀的文化因素,由于其雅俗共賞,受眾面廣,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展示欄”和“傳聲筒”。作為傳統戲曲的優秀代表,公案戲在千百年的傳承發展歷程中,始終秉承公平、法治、正義的核心思想,這也是公案戲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公案戲的社會文化價值應當被再認識、再詮釋。我們應以傳統公案戲為藍本,以時代精神為核心,打造與時代精神吻合的高品質文化作品,借助互聯網+等形式,構建公案戲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