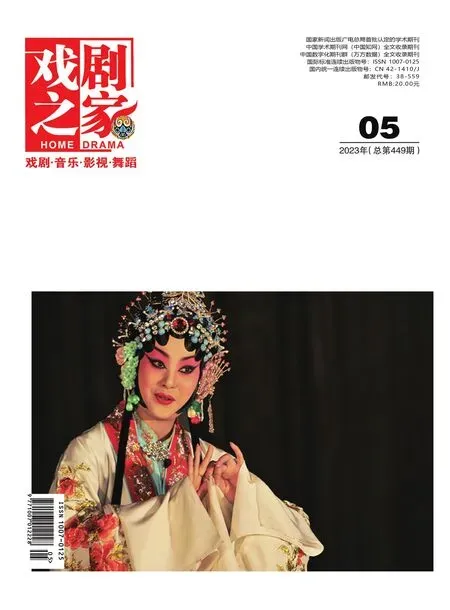試析傳統京劇旦角的行當構建
——以形象系統與程式系統為切入點
李妍霏
(中央戲劇學院 北京 100006)
《中國戲曲通論》對“行當”進行了如此闡述:“它既是形象系統,又是程式系統,兩者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每一個行當都是形象系統,同時也是一個相應的程式系統。”①由此,本文以京劇旦行形象系統與程式系統的構建為線索,以京劇旦行表演藝術的演進為依托,分析京劇旦角行當的構建,有助于當代傳承者把握京劇旦行表演藝術與時代文化的辯證關系,更加深入了解京劇旦行表演藝術的本質。
“旦”起源于扮演女性形象進行戲謔表演的游藝活動,這種演出形式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漸成為固定的模式。自元雜劇中出現的一些“旦腳”名目,如“農家女子稱‘禾旦’(元刊本《薛仁貴》)、帝王的妃子稱‘駕旦’(《古明家雜劇》本《梧桐雨》)、姓李的女子稱‘李旦’(《元曲選》本《魯齋郎》)、出賣色相的女子稱‘色旦’(《元曲選》本《陳摶高臥》)”②,還有“梅香、小梅、夫人、婆婆、母親、太后之類”③這些繁雜凌亂的以具體人物形象命名的稱謂,再到明傳奇“旦行四目”的形成,無不體現出戲曲對“旦”的人物角色設定不斷深入細化的表演需求,以致對后世旦行演員按人物類型進行表演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縱觀京劇形成前的近百年間,一貫秉承儒家思想“禮樂”文化的清廷統治者將他們所喜愛的昆曲視為崇高無比的雅文化并加以壟斷,文人將自身情志以及對女性群體的同情與憐惜付諸筆端,而高估了大眾對“句句帶典”的曲牌聯套體的接受程度,致使昆曲逐漸朝著宮廷化方向發展。反之,與“雅部”呈對峙局面的弋陽腔、秦腔、徽調、漢調等“花部”諸腔先后傳入京城,這些貼近民間生活的地方戲大都以小旦為主色,一時間“花部”旦角藝人在北京舞臺上各展其能。其聲腔、說白經過長期的相互影響與吸收,在保留自身語言特點的基礎上不斷向京音靠攏,以及演員爐火純青的技巧加持,使女性人物的藝術表現力得到了充分釋放,深受廣大群眾的熱愛與推崇。
早期京劇旦角的行當體制正是圍繞著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表演形態而發展的。一方面,延續數百年的昆曲本戲在展現才子佳人的故事情節中必然注重與生相配的女性形象塑造,這類以正旦為主的人物角色遵循著形象至美的表演法則,并滲透在一脈相承的京劇青衣行當創作理念中,呈現出“以形分行”的表演特色。另一方面,源起于民間重說唱、歌舞表演的折子小戲受到無固定劇本、演出場所等條件的限制,演員只能憑借自身技術、技巧以及即興表演等方式吸引觀眾。經過長時間的舞臺實踐,演員這種技藝化的表演形式逐漸成為“立一定的準式以為法”的程式表演,使具有“人物類型意義的‘腳色’變為所擅長伎藝的‘行當’”④。由此,兩種表演形態相互借鑒、結合,共同完善旦行表演的內容與形式,成為京劇旦行表演藝術之圭臬。
一、以類型化表演為奠基的形象系統
中國京劇本身具有“類”文化特性,其來源是不同地理環境、社會制度、民族宗教等蘊含的文化共性,具體反映在京劇運用行當表現人類共同的生活需求、人際關系與情感表達之中。京劇誕生之前,北京重旦的風氣是京劇旦行類型化表演發展的溫床。“花部”興起打破了自元雜劇開始萌芽的以生、旦為主搬演故事的結構模式,由此產生注重伎藝、戲謔的片段式舞臺表演,如徽班進京后風靡一時的“二小戲”“三小戲”。這種載歌載舞的表演方式決定了京劇花旦演員需兼備綜合的技術、技巧,因而花旦藝術率先發展,最先分化出程式特征明顯的子行當。
波多野乾一在民國初期編著的《京劇二百年之歷史》中將花旦分為閨門旦、玩笑旦、刀馬旦三類⑤,說明京劇花旦行當的演員繼承各地方戲的技藝表演已然可以賦予人物身份、職業等屬性,且涉獵較廣、文武皆能。此后,閨門旦、刀馬旦升級為旦行下的二級子行當,花旦一行又細化為玩笑旦、潑辣旦、刺殺旦、風騷旦等以人物性格與行動設定命名的子行當。每當有新的旦角行當產生,與之相匹配的表演程式動作也在逐漸豐富完善。由于花旦演員在技巧難度上的不斷追求,因一技命名一行的情況也有,比如“鬼魂旦”。這類行當的誕生意味著演員已經有意識依照人物特點,將高超的技藝分門別類到風格迥異的人物形象之中,并且建立了程式技法與人物內心世界的一種邏輯關系,而非簡單的自我“絕活兒”展示。早期花旦行當的人物扮相極為有限,最常穿的便是襖褲或襖裙,因此“以技構形”成為京劇花旦行當塑造人物類型化表演的范式。
相比之下,京劇青衣行當塑造人物形象的類型化表演集中體現在人物造型上。隨著漢戲藝人入京,以男性人物為主的生行劇目逐漸占領北京的戲曲舞臺,原先一家獨大的花旦行當很難有更多的施展空間,反而青衣行當借助本戲的盛行與莊嚴美學風格的回歸得到了發展。然而,盡管“老生時代”的青衣演員,如胡喜祿、時小福、余紫云等標志著京劇旦行藝術發展主要脈絡的代表人物亦可唱、念、做、打全能,但青衣表演始終受限于正劇中為生行配演的要求,在技術、技巧上較難自由發揮,只有在人物外型上尋求突破。
最常見的“青衣戲”莫過于《武家坡》《桑園會》《汾河灣》這類生、旦“對兒戲”,以女性人物身穿青褶子為標志而得名。這類青衣角色大都為生行陪襯,表演的是貧窮疾苦的中年婦女。早期青衣行當做功甚少,只以唱功見長且唱腔板式有限,因此青衣又有“抱肚子旦”的別稱。直到19、20 世紀相交之時,陳德霖開啟的京劇“青衣時代”的到來徹底改變了晚清京師徽班賦予花旦中心地位的歷史性軌跡,原為花旦演員擅用念功、做功表演的“宮裝戲”與“旗裝戲”被納入青衣劇目,并連帶著豐富了青衣行當的人物類型與表演技法,繼而撼動了19 世紀末發展到頂峰的以青衣、花旦為間隔的京劇旦行類型化表演。隨著“以技構形”與“按裝建形”兩種不同表演范式的進一步發展,京劇旦行的形象系統逐漸完備。
類型化表演是構建京劇旦行形象系統的基礎,從中也可管窺出京劇旦行表演藝術家對塑造人物形象以及運用程式技法的審美意識與革新精神,當旦行內部的子行當發展均衡且發生關聯時,就可被轉化為具有“集合”性質的表演方式,從而再創作出新的人物形象。20 世紀初到20 世紀40 年代,王瑤卿與“四大名旦”對京劇旦行表演藝術進行了全面整合與深入改革,開創了“冶青衣、花旦、刀馬旦于一爐”的花衫行當,隨之又發展出了具有融合色彩的“時裝戲”與“古裝戲”。“花衫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京劇旦行表演藝術由成熟走向鼎盛,本時期旦角演員“深受歡迎者,亦多限于花衫”,“各劇場每日演唱大軸者,殆為花衫人才所獨占”,成為“古來未曾有之特別現象”⑥,同時也使女性形象煥然一新。
二、以多元化表演為支撐的程式系統
京劇作為運用藝術邏輯加工生活素材并轉化為程式表演的表現性藝術,在形象系統確立的同時也會產生出相應的程式系統。程式系統的構建是在單項程式動作與成套程式組合的基礎上,借鑒不同種類的藝術形式,融入藝術家的表演風格,完成對人物形神兼備的塑造。20 世紀初,王瑤卿等人創立花衫行當后,京劇旦行表演完成了從“技術”到“藝術”的變革,“花衫化”的表演方式被廣泛運用到旦角各行當的創作之中,呈現出“由從前單一技術的極端極致、粗獷刺激,逐漸走向豐富、細膩、精致、深邃,并在所有層面都顯示出日常化、精細化、綜合化以及日趨成熟完善、富于格調內涵”⑦的發展趨勢,成為京劇旦行崛起的內在動力。在中西文化碰撞與交融的大背景下,傳統技巧化的程式表演不斷從其他藝術形式吸取營養,逐漸朝著歌舞化、情感化的方向邁進,其中梅蘭芳“古為今用”與荀慧生“洋為中用”的創新意識不僅發揮了花衫行當在塑造嶄新女性人物形象方面的絕對優勢,還在融合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多元化表演為支撐的京劇旦行程式系統。
自1915 年開始,梅蘭芳在齊如山的幫助下創作了十三出“古裝新戲”,在京劇旦行表演發展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古裝新戲”延續了“時裝新戲”與時俱進的創作思想,重視運用傳統京劇程式表演表達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并且注重增強服裝造型的觀賞性與可舞性。更值得發揚的是,“古裝新戲”的唱腔基本是在旦行傳統板式的基礎上加以擴充、精化,遵照劇情的起、承、轉、合與人物情感的遞進,形成了一個順序為【導板】【慢板】【原板】【南梆子】(《嫦娥奔月》中首次使用的新腔)【二六】【流水】或【快板】,最后【散板】收尾,節奏由慢至快,涵蓋梅派【西皮】唱腔精華的板式布局,身段則是采用曲牌體“形容詞句意義之舞”⑧的形式,彌補了板腔體戲曲身段匱乏、唱做不合的短板。此外,“古裝新戲”中的各類舞蹈正如焦菊隱先生所言:“絲毫不是空想出來的現代創造,而純系古代舞蹈形象的復原”,其可貴之處在于創作者在求新的過程中認同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古典價值,并本能地將這種精神透過當代視覺審美轉化為現代表達。梅蘭芳對“古裝新戲”的創造并非“追求‘標新立異’以炫耀于人”⑨,而是“倚借新舊過渡時代精英文士及學者的視野與力量,跳出當時時興戲曲的藝術淵源譜系和既有路徑依賴”⑩,賦予了古典藝術新的現代生命力。
若論“古裝新戲”中梅蘭芳“古為今用”的創作思路建立了京劇旦行程式表演與中國古典美學連接的橋梁,“將古典美與現代美有機地融為一體”?,那么荀慧生“中西交融”的表演方式則開啟了京劇旦行程式表演的另一種創作思路,堪稱“洋為中用”之典范。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多重影響,民國時期的大眾審美觀念透過服飾展現在京劇舞臺上,西方服飾的“窄衣文化”滲入中國傳統服飾的“寬衣文化”中,使京劇旦行服飾由寬大、平直改為以緊身、束腰為主的款式,舞臺上旦行服飾的“約束”反而成就了旦行表演的“自由”,引發京劇旦行程式表演的創新。從荀慧生塑造的經典人物來看,不論是服裝造型還是表演方式都大膽吸取了西方元素。以代表劇目《紅娘》為例,紅娘古裝頭后的蝴蝶造型的靈感來源于洋裝女帽“Poke bonnet”上的絲帶,還有借鑒大披肩、鯨骨裙上西方元素而來的古裝大云肩、百褶裙,這些注重夸張與放射效果的西洋古典設計注入在強調修長、縱向視感的傳統京劇旦行服飾之中,與荀慧生從芭蕾舞、華爾茲等西方舞蹈中擷取而來的表演身段相得益彰,塑造出紅娘的清新脫俗之感,給京劇旦行表演增添了新的活力。
多元化表演并不是程式系統的基礎,也不等同于簡單的技術表演融合,而是建立在京劇旦行內部各行當程式系統趨于成熟穩定的基礎上,以結合古今中外等不同特性的藝術元素為支撐,通過獨特的藝術形式與藝術風格拓展表演表現力與彰顯個性的一種表演途徑。此外,多元化本身也有跨行、跨界的含義,隨著時代的發展,唱片、電影、話劇等新興的藝術形式使傳統京劇藝術受到沖擊,繼續構建多元化的程式系統正是適應時代需求、迎合觀眾審美強有力的手段。
注釋:
①張庚、郭漢城:《中國戲曲通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年版,第419 頁。
②解玉峰:《青樓集“花旦”辨》,《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 年第1 期,第35 頁。
③許強:《古典戲曲旦腳研究》,河南大學,2015年,第11 頁。
④元鵬飛:《中國戲曲腳色的演化及意義》,《文藝研究》2011 年第11 期,第77 頁。
⑤(日)波多野乾一:《京劇二百年之歷史》,大報館1926 年,第9 頁。
⑥辻聽花:《花衫時代》,《順天時報》,1937年3 月8 日。
⑦劉汭嶼:《近代京劇旦行藝術的集成與突破——王瑤卿戲曲革新研究》,《戲曲藝術》,2017年第38 卷第2 期,第103 頁。
⑧齊如山:《論國劇歌舞化》,《齊如山文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 頁。
⑨劉乃崇:《王瑤卿的藝術革新與為我所用》,第37 頁。
⑩劉汭嶼:《梅蘭芳古裝歌舞劇的古典美學建構》,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戲劇》2018 年第4 期,第48 頁。
?梁燕:《齊如山劇學研究》,學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