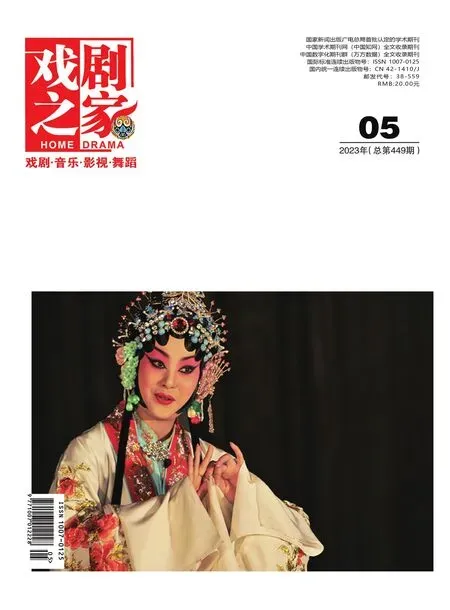寺山修司電影中的時間表達
——以《死者田園祭》為例
楊錫磊
(重慶大學 重慶 400044)
寺山修司在詩歌、戲劇方面的實踐使得他在創作中能夠以多重角度審視自己,以戲劇或詩歌的方式去構建自己的影像語言,形成了獨特的風格。于1974年上映的《死者田園祭》是寺山修司創作的第二部長片,曾獲得第28 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提名。這部影片使用了非傳統的敘事結構,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空并置或相互置換,“縫合”起了虛構主人公和寺山修司本人的童年。影片還向觀眾展現了男主人公家庭內外種種奇異的人物與景觀,荒野中的門和房間、掛滿鐘表的墻壁、掀開后能看到海的地板等等,體現了寺山修司獨特的電影美術觀念和影像風格。
一、時間的影像修辭
關于電影中的“時間”概念以及如何表現電影中的時間的問題一直受到哲學家和創作者的重視。德勒茲認為在法國新浪潮電影和意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中,“運動——時間的關系已經轉變,影像表現出分散、即興的特點,故事情節被片段化,因果關系被‘跳接’等剪輯打破,而這就是時間——影像”[1]。他提出電影必然與時間發生直接的關系,視聽影像的建構應該基于時間在影像中的綿延。蘇聯電影大師塔爾科夫斯基在《雕刻時光》中說道:“在物質世界里,時間可以消失且不留任何痕跡,因為它是一個主觀的、精神的概念”[2]。時間只有與人的思維活動相結合,才能顯露出種種痕跡。時間在人的回憶與想象中變換著形態,也反過來使回憶變得撲朔迷離。本文無意于抽象地探討時間的命題,對于寺山修司電影中的時間的討論只限制在形而下的方面,意在撥開籠罩在寺山修司影片表面令人眼花繚亂的迷霧,探究他獨特的時間觀念。
影像的制作可以被劃分為“影像元素設計、影像呈現和影像傳播三個階段”[3],筆者將從與影像自身相關的影像元素設計和影像呈現兩個階段入手,分析寺山修司如何在這部電影中呈現他的時間觀。
(一)影像元素設計——將記憶“帶入”風景
影像元素設計階段包含色彩、照明、服裝、道具、化妝、肢體語言、臺詞和空間等元素,即在電影拍攝階段預先被設計安排的將被框入鏡頭中的所有元素,其中的每一個元素都可以表現時間概念。
《死者田園祭》中制片人對身為導演的“我”說:“基本上,整個過去就是一部小說”,只有完成了對童年的敘事,才能從過去中告別出來。童年敘事在寺山修司看來并不是與事實完全相符的,他借人物之口說道:“如果不能自由地編輯自己的記憶,就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寺山修司將夢境、幻想、謊言與事實編織在一起,將童年記憶重新編輯。在這個編輯記憶的過程中,時間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帶著某個時間節點之后的愿望調查過去,過去的記憶中便存在著現在及未來時間的碎片。
寺山對時間的重新編輯合成通過他電影中的美術體現出來,他在與粟津潔①先生的對談②中提出了“帶入”風景這一概念,“同時掌握過去的風景與現在的風景,時而合成風景,時而編輯風景。風景并不僅僅作為裝置,而是必須在即將被合成、被改造的時候作為時間的一部分存在”[4]。因此,《死者田園祭》中的美術工作并不只是簡單地在恐山這一自然背景中置入象征時空環境的道具,而是改變風景的概念,通過風景的倒錯來表現人物所處的復雜的時空狀態。
《死者田園祭》中經常出現家具,或者說代表“家”這個概念的裝置,并被放置在室外環境中。比如鄰居家的妻子和她丈夫在一起吃飯的場景,在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柱子、門窗、廚具、餐桌等物品按照真實家庭的方式被布置,但用來標志家庭內與外的界限的墻和屋頂則完全不存在。甚至在紅衣女孩從恐山的山坡上跑下來的鏡頭中,只有孤零零的一個門存在著,這個門又顯得無比真實。大部分電影中的風景都是無生命的存在,只是作為故事背景出現,不會隨著記憶發生較大的改變。但寺山認為,既然記憶已經倒錯,時間也已經化成碎片散落,電影中的色彩、化妝、道具等元素為什么不可以隨著記憶發生膨脹或縮小、遠近置換等變形呢?因此,寺山在《死者田園祭》中對傳統的“家”的概念進行了揚棄,對家的范圍進行了擴充,限制家的邊界的墻壁和房頂被消除,門窗可以合理地存在于海邊與山丘上。
除了使風景發生變形和倒錯,寺山還在電影中使風景中的道具發揮語言的功能。提到寺山電影中的道具,最不可忽略的就是“時鐘”。《死者田園祭》中,主人公童年的家里掛了一整面墻的掛鐘,顯得異常陰森可怖。寺山修司將語言分為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內部語言是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外部語言是傳達思想的手段。寺山主張為了更加自由地表達,需要將外部語言進行擴展,因此他將視覺語言、身體表象、象征性的聲音等口頭語言以外的語言融入作品中。在1970 年上演的戲劇《人力飛行器》中,寺山修司就用構成風景的手旗信號代替了語言,提出了“作為風景的語言”這一概念[5]。在他看來,物品和人一樣都存在戲劇性,物品也有著言說的欲望,可以與電影中的其他人或物品進行交流。在《死者田園祭》中,鐘表指針走動時發出的噪音及壓迫感,使得無生命的掛鐘強烈地彰顯著其存在。
寺山修司在對談中說道:“日常的現實原則,向現代人的腦中帶入了電腦般的細密性。現代人帶著自己的意識支配一切的幻想,一天內數百回的眨眼,數萬次的說話,數萬粒進食,遵守著社會秩序,這就是日常性這一怪物的習慣”。[6]寺山修司在電影中不斷插入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物,插入種種疑惑,從而打破觀眾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慣性,使觀眾在觀影時不斷思考以填補電影中的空白。這樣,觀眾與電影制作者便共同感受著電影中時間的持續,電影作品也會因不同觀眾在時間進程中的不同思考形成不同的結果。寺山修司不僅利用電影這一媒介來表達自己對于人生的一系列思考,也在挑戰觀眾與作品之間的關系,并思考電影這一藝術本身。
(二)影像呈現——非現實的色彩濾鏡
影像呈現指的是被設計好的電影元素轉化為電影影像及加工處理的過程,影像的呈現常常有三種,“一是通過使用各種攝影技法把影像元素拍攝下來;二是通過創作出虛擬影像,以此達到建構電影影像的目的;三是通過蒙太奇的手法,把真實影像元素或者虛擬影像剪輯出來,以此得到電影影像”[7]。《死者田園祭》的影像呈現最為突出的手法就是色彩濾鏡的使用。
寺山修司在電影中大量使用藍色、綠色、黃色甚至多種顏色共存的色彩濾鏡,以表示與現實相對的夢境、幻覺。童年時期的“我”與心愛的女人私奔時的場景在前四十分鐘的版本里是綠色的,因為這是“我”對自己記憶的更改,是“我”虛構的情節。這種綠色的濾鏡不僅存在于本片中,《拋掉書本上街去》的男主人公英明的家庭生活部分,和《再見箱舟》中林中仙子出現的鏡頭也被蒙上了綠色的濾鏡。除此之外,本片中馬戲團出現的畫面被加上了充滿迷幻感的彩色濾鏡,而事實上童年的“我”并沒有見過馬戲團,主人公在片中解釋道:“馬戲團的演出對我而言,就像我打開第一塊表蓋時所受到的那種震動,滴答的轉輪發出類似嘉年華的響聲,就像六十個魔術師變出巧妙的戲法。但一旦我把蓋子蓋上,所有神奇的魔法就都消失了。”懷表是童年時期的“我”一直想要而不得的物品,懷表的寓意與代表著集體時間的掛鐘相對立,寓意著個人時間和自由。在電影元素設計過程中,寺山認為鐘表代表著記憶中的某處,如果說墻上的一個個掛鐘代表著“我”在恐山生活的真實記憶,那么懷表便代表著“我”虛構出來的記憶某處,比如彩色濾鏡中的馬戲團。
影片中除了運用最為頻繁的綠色和彩色這兩種濾鏡外,還有“我”在恐山上游蕩、向巫婆抱怨對母親的不滿時的藍色,成年后的“我”所在時空的黑白色,片頭小孩捉迷藏時的淡黃色等等。寺山修司用不同的顏色代表“我”記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時間隨著記憶的重新編輯而變形,電影中現在、過去以及未來的時間同時出現或相互置換,寺山修司的時間迷宮由此形成。
二、套層結構及其變體
電影敘事結構的分類非常多樣,按照《電影藝術詞典》中的劃分,電影劇作結構按歷史沿革可以分為傳統式結構和非傳統式結構;從時空處理入手可以分為順序式和交錯式兩大基本類型;按照視點結構又可被分為主觀敘述結構與客觀敘述結構,除此之外還有戲劇式、散文式、小說式等諸多結構形式[8]。《死者田園祭》這部電影的敘事結構是在非傳統結構中的套層結構的基礎上做了更復雜的改動,筆者將從闡述這種套層結構的變體入手分析時間在寺山修司電影中的呈現。
北京電影學院的汪靜認為《死者田園祭》使用了套層結構,使得導演本身和作品之間產生了密切聯系[9]。影片前41 分鐘講述的是童年時期的“我”在故鄉恐山的生活經歷,在第40 分鐘的鏡頭中,綠色濾鏡中“我”和鄰居家的妻子私奔成功,并肩走在鐵道上。電影畫面在此時突然變成了空白膠片上的劃痕,在屏幕上不停跳動。景別逐漸變大后,才顯示出原來是一群電影制作者在預覽未完成的影片,影片開始在另一時空展開敘述。在這一層時空中,長成大人的“我”是一名制作自傳影片的導演。《電影藝術詞典》指出套層結構的影片往往有現在和過去兩個時空,“兩個獨立時空的敘事交織在一起平行展現[10]”。但寺山修司并沒有止步于平行呈現兩種明顯不同的時空,而是對這一結構進行了進一步延伸,讓兩個時空中的人物相遇并進行了對話,從而對時間是否可逆這一命題進行了一次模擬實驗。現在時空的“我”想要干涉過去,這種干涉行為的影響并不只作用于“我”拍攝的電影中,也會使現在的“我”發生改變。電影中的“我”一直在追問一個問題:如果人可以回到過去殺死自己的曾祖母,那么現在的自己還會存在嗎?當現在時空中的我們對過去時間進行了干預,對現在時空中的我們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影片中的導演唆使童年時的自己去殺死母親,使自己在夢中和記憶中的場景變為現實。在原地苦等了許久后,他決定自己前往童年的家與母親見面。一見到母親后,現在的“我”便明白自己的設想全無意義,在熟悉的母親面前,自己只能乖乖坐下,接受母親的食物和一切。
現在的“我”對于過去的記憶中夾雜著的幻想和謊言的成分,即使有了改變過去的機會,也因為無法分清虛構與現實而難以實現,因為無論是謊言還是現實,這些記憶已經成為自我建構中的重要部分。安德烈·莫洛亞在《追憶似水年華》的序言中說:“人可以借助智力,通過推理、文件和佐證去重建過去。”[11]寺山修司借由影像對時間是否可逆進行了探索,像普魯斯特在書中所做的一樣,向我們展現了他回憶和把握過去的獨特方式。
三、結語
寺山修司將他在詩歌、小說、戲劇等各領域的經歷中所吸取到的東西在影像世界里反映了出來。他雖然只創作了五部長片,卻以其獨特的實驗性和先鋒氣質影響了藝術界很多創作者的視覺文化追求。“建筑家安藤忠雄是他的粉絲,森山大道與他相互啟發,橫尾忠則承認自己受到他的影響,由此意識到創作和生活不能被割裂開。”[12]在拍攝過很多青春題材影片的巖井俊二的影像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寺山修司風格的痕跡。
注釋:
①粟津潔:日本著名設計家,1929 年生于東京,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為日本平面設計復興作出重大貢獻,其藝術創作涉足插圖、書籍、建筑、音樂和電影等多項領域。曾擔任電影《死者田園祭》的美術設計,他還為寺山修司的天井棧敷劇團設計過海報,為寺山的詩集做過裝幀。在《死者田園祭》中他還出演了詩人這一角色。
②這個對談指的是1976 年日本フィルムアート社出版的《寺山修司対談集·密室から市街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