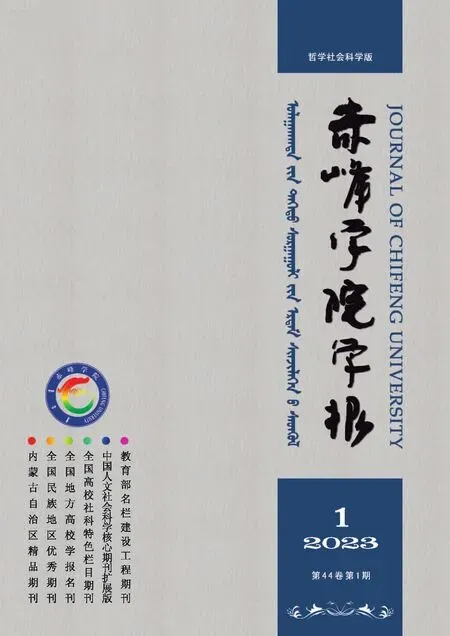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頻發的治理困境及法治對策
鄧小云,寧雪萍
(1.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2; 2.河南大學 法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后,全國人大通過《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1]。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國家及地方立法也相繼啟動修訂或者修改程序,野生動物保護的法網愈加嚴密。但是,根據近幾年的野生動物違法案件數據來看,相關的違法案件數量并未顯著減少。在強調野生動物保護、強化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對當前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特點進行梳理,并積極尋求其法治化對策具有必要性。
一、當前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情況和特點
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當前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呈現出多樣化和復雜性的特點,國家雖然強化了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力度,開展了 “昆侖2021”和“清風2022”等專項行動,但野生動物違法案件數量并未減少且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近五年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情況
2020年的昆侖行動中,在三個月的時間內,公安機關查獲了8100 多起案件,收繳野生動物23 萬頭(只、條)、野生動物制品5400 余公斤,抓獲了1.2萬名犯罪嫌疑人[2]。在2021年的“昆侖”系列專項行動中,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案偵辦涉野生動植物和森林資源刑事案件3.5 萬起,收繳救護野生動物27.4萬頭(只、條),破獲了9600 多起刑事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1 萬名[3]。2022年,由11 個部門聯合開展的“2022 清風行動”查辦野生動植物案件近1.2萬起,打掉犯罪團伙719 個,打擊處理違法犯罪人員1.4 萬余人;收繳野生動植物13 萬余只(頭、尾、株),野生動植物制品14 萬余件、近20 萬千克[4]。
此外,根據統計中國裁判文書網相關判決書數量可知,涉及野生動物違法的案件數量在近五年呈現出逐年遞增的態勢,2017—2021年的案件數量分別為2821、2815、4206、5772、2427 件。2017年—2021年野生動物違法案件數量直線上升,一方面反映了疫情背景下國家對相關案件的打擊力度增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實踐中涉野生動物違法行為難以根除。特別是經過2020年和2021年的專項行動以后,2022年專項行動的案件數量回落情況仍不理想,側面暴露了實踐中在打擊野生動物違法犯罪時存在著一些問題,致使打擊效果不理想,未能從根本上遏制這一違法現象。
(二)當前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特點
根據上述案例情況總結,當前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具有如下特點:
1.新的違法犯罪形式凸顯
在增大線下打擊力度以后,越來越多的賣家選擇隱匿于網絡,使用暗語發布信息,運輸時則借道于物流。通常賣家會借用淘寶、微信、抖音等平臺,使用拼音,英文字母等暗語發布售賣信息。在野生動物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溝通會借助隱秘性的暗語,買家通過軟件與賣家直接溝通后購買,賣家通常會使用快遞物流運輸野生動物。與傳統的線下交易不同,“人貨分離”的方式讓犯罪人更易逃脫偵查與監管。雖然《快遞市場管理辦法》規定了快遞服務業禁止寄遞的物品范圍,快遞從業人員通常對此明知,但因每日的發貨量大,快遞員有時疏于查驗,使得野生動物制品順利寄遞,更有個別快遞員受利益驅動充當內應,收取較高的快遞費,幫助賣家選擇合適的運輸方式躲避檢查,完成野生動物非法交付。
2.犯罪主體基層化特點明顯
犯罪主體多為農民,山民,這類群體一般文化程度較低,法律意識淡薄,大部分人對其違法行為并不知曉,歸根結底是其對野生動物品種缺乏了解,對相關法律知之甚少。更有甚者,據2019年“5.13”系列重特大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案記錄,在對犯罪嫌疑人劉某某實施抓捕時,民警遇到了來自犯罪嫌疑人和其親戚朋友的武力威脅,抓捕工作陷入困境,直到得到當地警方的協助以后,才將犯罪嫌疑人抓捕歸案。
3.犯罪動機多樣化
有的違法分子因為自身患有肝病,聽聞穿山甲對治療肝病有功效,就斥巨資從不法渠道收購穿山甲,而不去考慮該行為是否違法。有的違法分子為了經營餐館,給自己的餐館增加客流量,大肆購買各種野生動物,將其制作成菜肴,售賣給食客。還有一些違法分子出于獵奇心理,癡迷野味的食療和養生價值及其別致的滋味,用打獵工具自行狩獵野生動物,而后食用。近兩年寵物類案件逐年遞增,大部分人出于個人癖好喂養“異寵”,包括各種龜類、鳥類、蜥蜴類、蛇類等。此外不法分子從販賣野生動物行為中能夠謀取巨額利潤,如在阮成藝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案中,被告人阮成藝漠視國家法律,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4日期間走私穿山甲440 只入境,其中每只穿山甲的價值為人民幣4 萬元,價值共計人民幣1760 萬元[5]。因為販賣某些野生動物可以在短短幾個月內獲得極高的經濟利潤,故而有些犯罪分子在利益的驅使下以身試險。
二、當前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的治理困境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開宗明義:野生動物是地球自然系統中無可代替的一部分,各國人民和國家是本國野生動植物的最好保護者[6]。扎實推進野生動物保護工作,是全面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保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促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立法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導致實踐中的案件打擊效果并不理想。
(一)個別條文內容科學性和完整性有待強化
當前我國在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立法方面存在不足,要想真正解決人工繁育動物上產生的問題,需要對法治理念進行更新[7]。2021年2月新調整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公布,要求維護從事相關物種人工繁育活動的單位或個人的合法權益[8]。那么是否可以考慮將那些規范合法的養殖場內的、不會危害野外種群的、人工繁殖成熟的子三代物種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張明楷教授認為人工繁殖的動物與野生動物在刑法上不可一概而論[9]。2022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明確了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案件的處理規則:在刑事方面,將涉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案件與涉野外環境中自然生長繁殖的野生動物案件一視同仁是不合適的。因此,根據《解釋》的規定,對于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當其屬于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或者其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作為寵物買賣、運輸的,對該類案件一般不認定為犯罪或依法從寬處理[10]。毋庸置疑,《解釋》 的公布對立法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提供了一種辦法。然而,僅靠《解釋》是不夠的。現行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陳舊且亟待更新,上述《解釋》規定的情形仍然較為籠統,實踐中沒有具體的認定標準,執行起來仍然困難重重。
(二)監督機制有待加強
隨著我國對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日益重視,公安機關圍繞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查處力度也在增大,這對大部分野生動物的違法犯罪案件起到了強有力的打擊作用。然而,與野生動物有關的犯罪屬于無受害人犯罪案件,此類案件的事實只能通過公安機關的調查和公眾舉報才能查明,加上野生動物違法行為通常具有較高的隱蔽性,所以此類案件發現、取證難度大,案件的偵辦也很難。在當前的防疫背景下,野生動物的非法交易極大可能會更多地從線下轉移到線上,犯罪分子將以更加隱蔽的手段物色消費者,打擊的難度必將進一步增加。地方的野生動物保護執法力量有限,僅僅依靠地方政府難以充分防范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發生[11],中國仍有大量未發現的與野生動物有關的違法案件。另外,由于嫌疑人作案地點地處人跡罕至的山區,違法犯罪行為被當場發現的可能性小,案件線索大多靠群眾舉報,即便在清查過程中發現捕獸吊索、鐵夾和捕鳥網等作案工具,也很難據此查找到嫌疑人,公安機關和其他行政機關在查處此類違法犯罪案件的道路上步履維艱。
(三)協同監管機制有待構建
野生動物保護涉及多個部門,但部門之間缺乏聯動協同機制,存在協調性不足以及配合度不高等問題,由此導致各部門的職能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切實發揮,無法形成打擊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合力[12]。因為野生動物違法案件往往涉及狩獵、運輸、收購、賣出等環節,如此繁多的環節令公安機關、林業、市場監管等部門無法將執法力量集中到一處,導致實踐中涉野生動物的違法案件監管不力。甚至各部門在執法檢查過程中發現疑似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往往以罰代管、以罰代刑,不會將案件移送給公安機關,導致監管上存在漏洞。公安機關也因為無法得到此類案件的線索,不能及時對其進行有效打擊。一些犯罪分子在跨地域作案時,若當地偵查機關不積極配合,各部門往往不能形成有效的打擊合力。此外,在實踐中存在多個部門擔負保護野生動物職責的情況,陸生食用動物歸畜牧部門管理,水生食用動物歸漁政部門管理,運輸歸城管部門管理。所以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牽涉的環節多,導致管轄權上的混亂,出現“搶著管”或者“都不管”現象,從而不能及時處理野生動物違法案件。
(四)野生動物保護社會氛圍有待進一步營造
以農民、山民為主體的狩獵群體,容易接觸野生動物,能夠更靈活地支配時間,因此有作案的時空條件。這一群體大多法律意識薄弱,有些人以為自己捕捉麻雀、斑鳩等夏候鳥的行為是幫助人們“除害”[13]。此外,相關職能部門對野生動物保護宣傳工作重視不夠,沒有擺上重要議事日程,野生動物保護宣傳工作浮于表面。野生動物管理部門對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宣傳工作仍停留在城市里的宣傳欄上,很少深入農村挨家挨戶做普法宣傳,甚至去鄉鎮集市上發傳單的宣傳工作都極少開展。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宣傳工作的缺位,導致很多村民并不知道狩獵野生動物是違法的。
(五)跨境監管能力有待強化
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中國海關共偵辦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制品走私犯罪案件923 起,查獲各類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制品1552.7 噸[14]。走私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案件在中國如此猖獗,原因與其背后的巨額利潤密不可分。一方面,非法野生動物貿易的商業化助長了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的走私。野生動物交易通常可以獲得巨額利潤,但犯罪分子獲得的處罰卻非常輕微,現實中普遍存在著“罰輕于過”的現象。另一方面,由于我國野生動物產品需求旺盛,龐大的市場需求導致進口走私問題嚴重。消費市場的存在客觀上刺激了走私者牟利的貪欲,給野生動物的保護帶來了極大的阻礙。目前,我國走私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刑事案件的主要特征是,以走私珍稀動物及其制品刑事案件居多,且有逐年遞增的趨勢; 部分案件涉及的走私物品數量和價值巨大,造成的危害無法估量;在普通旅檢通道中會發現零星的走私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且屢禁不絕。
三、未來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立法的改善
結合上文提到的當前我國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其立法不足,需要做出相應改善,以更好地保護野生動物,打擊涉野生動物違法犯罪。
(一)健全和豐富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
首先,適時修訂、更新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具體而言,在實踐中要適時調整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且調整間隔時間不宜過長。調整前,既要廣泛征集林業專家、群眾代表、人工養殖地商戶代表等意見建議,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技術成熟度、種群數量等方面對物種狀態進行專業評估,也要充分聽取司法機關的意見建議,把野生動物司法保護中遇到的疑難困惑作為重要參考,更加科學合理地確定名錄范圍。
其次,應明確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與野外生長的同類野生動物在法律性質和價值上都存在較大區別[15]。凡是經過馴養繁育的野生動物品種或其后代(多代人工繁育),均被視為刑法意義上的珍稀瀕危野生動物,這與野生動物保護實踐脫節,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對一些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穩定的純人工繁育種群和同類野生種群采取不同的保護和管理措施,既符合有關國際公約,也符合大部分國家的通行做法[16]。此外,司法機關在辦理涉野生動物違法案件時,應當考慮對人工繁育動物犯罪案件確立綜合評判法益侵害程度的規則[17]。針對在已申辦人工繁育許可證、獲得專用標志等,確定可追溯性的前提條件下,相對數量上已經明顯增加、單純由人工馴化或養育、沒有野外天然繁殖經歷的野生動物,可以在國內開展貿易、運輸等商業用途。如刑法上再將此類動物認定為野生動物,就會不當擴大犯罪的打擊面,以致違背罪刑法定原則[18]。同時,相關部門也要進一步細化和確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的標準,規范商戶的養殖規模,強化人工養殖地商戶的買賣運輸監管,確保人工繁育的動物確是作為寵物被買賣和運輸。
(二)健全監督機制
應采取有效行為禁止野生動物濫用,最重要的是完善針對食用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監督機制。公安機關要緊密跟蹤涉野生動物違法案件的新動向、新特點,善于使用新型偵查設備和新的媒體平臺,提高自身偵查打擊能力。除此之外,也要重視社會公眾的力量,在實踐中積極動員公眾以多種形式加入野生動物保護行動中來,實行舉報監督獎勵機制。相關部門可以與各級主流媒體展開合作,及時公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信息,讓公眾直觀、高效地參與和監督。
(三)優化構建協同監管機制
全地區、部門間攥指成拳,形成合力,推動構建齊抓共管、科學治理的野生動物資源保護新格局。首先,考慮《野生動物保護法》與《環境保護法》的銜接,建立野生動物保護的統一監管與專業執法分立機制[19]。在健全有關立法的基礎上,全面完善野生動物保護綜合執法,確立野生動物保護執法與司法的有效協同機制。執法部門在執法時發現行為人的行為事實涉嫌野生動物違法的,就必須及時移交公安機關處置,不可以用行政執法替代犯罪懲罰。其次,各部門要樹立“野生動物保護一盤棋”思想,加強溝通配合,根據情況適時開展聯合執法專項活動,創新戰法,切實筑牢野生動物保護屏障。各部門之間要協同互助,加強協調合作,共同對捕獵、出售、購買、食用、運輸等各個環節加強監管,嚴厲打擊野生動物違法案件。
(四)健全野生動物保護宣傳機制
不能完全依靠法律來對野生動物進行保護,而應該更多地提高公眾的保護意識,尊重社會公眾在野生動物保護中的“主體地位”[20]。首先,各級政府和組織要充分認識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的重要性,穩步開展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宣傳,強化廣大群眾特別是山區群眾對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護意識,徹底根除“野生無主,誰獵誰有”的錯誤想法,禁止亂捕濫獵,禁止食用野生動物,讓他們積極同破壞野生動物違法活動作斗爭,樹立人與野生動物和諧相處觀念。
其次,檢察機關可以通過一些短視頻平臺、微信視頻號、微博直播等新媒體發布涉野生動物違法的典型案例,提高案件宣傳效果。對于具有重要宣傳和教育意義的案件還可以協同當地法院的巡回法庭在案發地開庭審理,組織當地群眾和干部旁聽,充分發揮庭審的法治教育功能。庭審結束后,法庭工作人員可以向廣大群眾發放一些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宣傳冊,積極宣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普及相關生態法律法規,并就常見的非法獵捕、收購野生動物等違法行為開展針對性的釋法答疑,達到“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必要時,檢察機關可以組建野生動物保護司法基地和實踐基地,組織群眾去基地參觀學習,強化群眾的野生動物保護觀念,增強法律意識。
(五)強化跨境監管能力
首先,加強國際合作,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除了一同建立野生動物走私犯罪的情報共享平臺外,我國也要加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出入境物品監管力度,爭取從源頭上遏制野生動物走私犯罪的擴張趨勢。其次,加大資金投入,加強管理和執法隊伍建設,提高執法水平和力度,積極采取有力措施打擊野生動物走私行為。再次,加強海關監管,提高海關人員的整體執法素質,杜絕海關內部的腐敗現象,防止腐敗人員為走私分子“開綠燈”;在海關場所張貼宣傳畫報,對旅客進行不定期法律宣講,減少普通旅檢通道的走私案件。最后,增強國內的行政監管協調能力,重點針對終端消費因素,從根源上杜絕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非法貿易,打擊國內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市場,提高國民的法律意識。
四、結語
野生動物保護關系到國家生態環境的總體平衡[21]。當前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的法網日益嚴密,但野生動物違法案件仍然猖獗,表明我國在野生動物保護的法治應對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現行的法律規范不足以起到規范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的作用,存在著個別條文內容科學性和完整性有待強化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健全和豐富野生動物保護政策法規。野生動物的保護涉及多個部門,環節繁多,需要相關部門加強監督機制和協同監管機制。跨境監管能力也需進一步提高。此外,也要健全野生動物保護宣傳機制,營造野生動物保護社會氛圍,形成野生動物保護的治理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