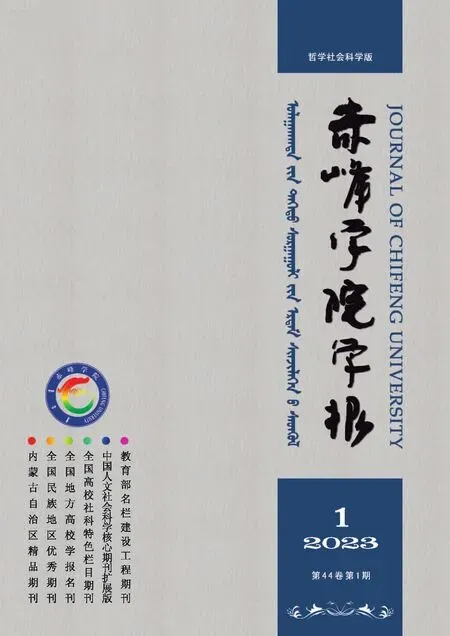論元代北方民族詩人的漢文創(chuàng)作
——以同題集詠創(chuàng)作為例
畢兆明,陳碧優(yōu)
(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內(nèi)蒙古 通遼 028000)
同題集詠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可以上溯到魏晉時期,如曹丕、陳琳、王粲曾均以《瑪瑙勒賦》為題作賦。從創(chuàng)作實踐看,有的集詠組織嚴密,有發(fā)起者、評判者和詩作收集者,集詠后往往有詩集流傳于世;有的則形式自由,參與者就某事件(或陳設景觀)即時起興,唱和應答,馳騁詩情,展示才情。
元朝民族眾多,文化多元,雅集聚會活動頻繁,這為同題集詠創(chuàng)造了條件,由此迎來了同題集詠的興盛。元朝推行漢法,修習漢典,北方民族詩人廣泛接觸中原文化,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由此元代展現(xiàn)出兼容并蓄、開放吸收的時代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詩人學習中原詩歌同題集詠的創(chuàng)作形式,并用漢文創(chuàng)作了很多優(yōu)秀的詩作。民族詩人同題集詠如激流交鋒,浪花飛濺,交互騰躍,姿態(tài)萬千。
一、民族詩人同題集詠的創(chuàng)作盛況
同題集詠這一創(chuàng)作形式在元代極為興盛。元初遺民詩人痛感時移世易,紛紛舉辦詩社抒發(fā)感懷之情,同題集詠日漸興盛;元代中后期詩人們多緣情、緣事而發(fā),同題集詠的主題不斷豐富,往往與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相吻合;至元末同題集詠達到極盛,延至明清仍遺響難絕。受這種詩風的影響,北方民族詩人也積極參與其間,或詠物,或酬唱,或題贈,或懷古,創(chuàng)作了很多優(yōu)秀的漢文詩歌。
石抹宜孫本為契丹人,石抹家族至宜孫祖、父輩已定居臺州,漢化程度極高。石抹宜孫重孝廉、嗜讀書,“于書務博覽,而長于詩歌”,①又極富將軍之才,禮賢下士,善于用兵,因此身邊聚集了劉基、葉子奇、泰不華、余闕等朝臣文士,形成了“極東南人物之勝”浙東文人群。《元詩選·癸集下》記載了一次同題集詠創(chuàng)作活動:“至正中,石抹宜孫總置處州時,嘗構掀篷于妙成觀,集諸名士投壺賦詩。宗姚首賦是詩,宜孫和之,一時屬而和者數(shù)十人,自何宗姚以下十一人,并見《掀篷倡和詩》。”②這次同題集詠首先由何宗姚創(chuàng)作了《妙成觀掀篷》,其后石抹宜孫、費世大、謝天與、廉公直、趙時英、陳東甫、郭子奇、孫原貞、吳立、張清、寗良十一人均有《妙成觀掀篷和何宗姚韻》,其中石抹宜孫《妙成觀掀篷和何宗姚韻》:“結構新亭似勝前,登臨歷歷瞰晴川。放懷喜解防秋戍,乘興還操下瀨船。從此入林堪避地,何妨坐井亦觀天。東風回首春城暮,桃李依然種日邊。”③詩中“登臨歷歷瞰晴川”一句化用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一改原詩吊古懷鄉(xiāng)之憂愁,保留氣勢恢宏之境界,抒發(fā)與友人游賞的喜悅。
竹枝詞初為唐代劉禹錫、白居易等模仿南方民歌首創(chuàng)的一種新題樂府。發(fā)展到元代,竹枝詞已不限于描寫南方風物,比如出現(xiàn)了“同時擁有民歌創(chuàng)作、紀行寫作與館閣酬唱多種屬性的”④上京竹枝詞。至正元年四月,袁桷同王士熙、陳景仁前往上京集賢院任職,留三月有余,八月返回大都時已有六十二首集體唱和詩作。⑤其中以竹枝詞為主題的有:袁桷《次韻繼學途中竹枝詞十首》、⑥王士熙《竹枝詞十首》《上都柳枝詞七首》、⑦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詞十首》《和王左司柳枝詞十首》、⑧許有壬《竹枝十首和繼學韻》《柳枝十首》《和繼學壁間韻》⑨等。集詠內(nèi)容廣泛,如王士熙《竹枝詞十首》其一“居庸山前澗水多,白榆林下石坡陀。后來才度槍竿嶺,前車昨日到灤河。”與許有壬《竹枝十首和繼學韻》其一“居庸泉石勝概多,桑干北去漸沙陀。龍門鉤帶水百折,一日驅車幾渡河。”都提到了居庸關、灤河等獨具特色的北方地域景觀;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詞》其七“太官湯羊厭肥膩,玉甌初進江南茶” 和許有壬《竹枝十首和繼學韻》其七“宛人自賣葡萄酒,夏客能烹枸杞茶”兩詩皆涉及了民族風俗;王士熙《竹枝詞十首》其二“宮裝騕裊錦障泥,百兩氈車一字齊。夜宿巖前覓泉水,林中還有子規(guī)啼。”以及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詞》其五“日邊寶書開紫泥,內(nèi)臣珠帽輦步齊。君王視朝天未旦,銅龍漏轉雞人啼。”都談到上都的宮廷生活。此次竹枝詞同題集詠可謂詩作頗豐,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充分發(fā)揮了“詩可以群”的社會功用。
顧瑛主持的“玉山草堂雅集”是元代后期(至正年間)規(guī)模最大、參與人數(shù)最多的文士雅集活動。顧瑛出身于豪富之家,卻主動放棄家業(yè),傳予其子元臣,自己則在舊宅之西構筑玉山草堂,只為召集文人名士賞名畫、觀美景、讀古書。“園池、亭榭、餼館、聲妓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名士若張仲舉、楊廉夫、柯九思、李孝光……常主其家,日夜置酒賦詩”“一時風流文雅,著稱東南焉。”⑩元代末年戰(zhàn)亂紛起,但因顧瑛長子和次子均授正千戶,玉山草堂得到吳中地區(qū)控制者張士誠的庇護,所以玉山草堂得以在政局混亂中存在二十年之久,成為文人在末世尋求清雅的歸處。據(jù)楊鐮、葉愛欣整理的《玉山名勝集》記錄,玉山草堂(玉山佳處)共有二十六處景觀,共集合詩人二百余首同題集詠,其中民族詩人昂吉、聶鏞為草堂多年的常客,二人曾參與到“碧梧翠竹堂”同題集詠,皆有以“碧梧翠竹堂”為題的詩作。昂吉《碧梧翠竹堂》:“爾愛小軒梧竹好,雨晴添得草堂幽。掛簾涼月作秋色,繞屋清陰如水流。莫剪高枝留宿鳳,好依勁節(jié)聽鳴璆。醉來幾度憑欄立,但覺蕭蕭爽氣浮。”?用詞簡練清爽,語言清新可人,既援用鳳凰這類帶有中原文化內(nèi)涵的意象表現(xiàn)玉山草堂之盛景,扣題梧竹乃“靈鳳之所棲食者”,?又不吝感情肆意抒發(fā),用“爽氣浮”三字表達身處玉山草堂的舒爽與愜意;聶鏞《碧梧翠竹堂》:“青山高不極,中有仙人宅。筑堂向溪路,鳥啼花落迷行跡。翠竹羅堂前,碧梧置堂側。窗戶墮疏影,簾帷卷秋色。仙人紅顏鶴發(fā)垂,脫巾坐受涼風吹。天青露葉凈如洗,月出照見新題詩。仙人援琴鼓月下,枝上棲烏弦上語。空階無地著清商,一夜瑯玕響飛雨。”?詩作形式自由,詩行隨情感循序迭進,將草堂比作傳說中仙人的居所,但這里又不至于高聳難以攀登,而是如此親切、雅致,帶有人間風味。此外,還有圍繞張叔厚的《玉山草堂圖》題畫同題集詠,昂吉也參與其中并作有一詩,詩中“蘭亭勝事不可見,賴有此會如當年”?一句將玉山雅集與文學史上著名的蘭亭集會并提,可見對玉山雅集高度認同與贊揚。昂吉還參與了“釣月軒”同題分韻賦詩的活動。
元代北方民族詩人詠物題材廣泛,同題集詠更是萬物皆可入題。所詠之物不僅包括淵源已久的典雅之物,還有獨具時代風貌的特色物件,一方面在前人已有的詩境中開辟新路,另一方面結合詩人自身體驗為詩歌意象增添新鮮血液。畏兀兒詩人貫云石有一首《蘆花被》,意象鮮明,境界高遠:“采得蘆花不涴塵,翠蓑聊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妒,欸乃聲中別有春。”?貫云石家世顯赫,外祖父為元代著名世家高昌廉氏人,但是他不慕名利,“宦情素薄”,?曾北上向漢族儒臣姚燧求學,晚年辭官隱居,自稱“蘆花道人”。關于這首詩的寫作緣由,作者在小序中寫道:“仆過梁山泊,有漁翁織蘆花為被,仆尚其清,欲易之以綢者。翁曰:君尚吾清,愿以詩輸之。遂賦,果卻綢。”?從中可以看到,“蘆花被”這一意象蘊含著詩人隱逸、孤傲的思想品格和高潔不染的人生志趣。隱逸是中國古代詩歌中一種常見的主題。貫云石雖為色目人,但受中原文化影響頗深,從這首詩也可以略察北方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浸潤滲透。貫云石之后,“蘆花被”成為元代文人競相集詠的對象,雖無固定的主辦者和統(tǒng)一的創(chuàng)作時間,但是士大夫競相吟詠,從者如云,形成了集詠的系列詩作,體現(xiàn)集詠之精神。代表性的如謝宗可《蘆花被》:“白似楊花煖似烘,纖塵難到黑甜中。軟鋪香絮清無比,醉壓晴霜夜不融。一枕和秋眠落月,五更飛夢逐西風。誰憐宿雁江汀冷,贏得相思舊恨空。”?前兩聯(lián)著重刻畫蘆花被輕軟、不落凡塵、不被塵世玷污的特征,后兩聯(lián)表達出對隱逸、高潔文化精神的認同及對作者的仰慕;張昱《題貫酸齋蘆花被詩后》:“學士才名半滑稽,滄浪歌里得新知。靜思金馬門前直,那似蘆花被底時?夢與朝云行處近,醉從江月到來遲。風流滿紙龍蛇字,傳遍梁山是此詩。”?用“風流”“龍蛇”頌揚原詩作者貫云石的才氣和風度,“傳遍梁山”更是表現(xiàn)出《蘆花被》傳播范圍之廣,影響之深。這些集詠詩作步貫云石之后履,以“蘆花被”為喻道出了中國古代文人高潔不染的價值取向和隱逸孤傲的精神氣質。
二、民族詩人同題集詠的藝術特征
民族詩人的漢文創(chuàng)作離不開民族詩人對中原文化和詩歌傳統(tǒng)的認同。隨著元朝的建立,很多北方家族遷居至大都、江南,家族后代雖然具有民族身份,但生長于漢族聚集區(qū),生活習慣、精神志趣早已漢化。另一方面,基于民族身份和與眾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在意象的營造及詩情的表達上,民族詩人的漢文詩又呈現(xiàn)出獨特的民族風情。
(一)豪縱闊達的時空感
北方民族詩人的詩歌具有豪縱闊達的藝術特征,具體表現(xiàn)為時間和空間的延展性。這種時空感的形成與北方民族長期游牧的歷史及元代獨具民族特色的兩都制密切相關。北方民族多有長期游牧的歷史,元朝立國后實行兩都制,每年夏季,皇室都要從大都出發(fā)前往上都避暑消夏,同時大都作為元代副政治中心,政府各部門與大都配套,官員扈從皇室搬往上都處理公務,到秋季返回大都。統(tǒng)治者在上都汗帳接見來自歐亞各地的使臣,南方文臣有機會跟隨統(tǒng)治者遍覽北方風景:“關途覽歷之雄,宮龠物儀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動神竦。”?生活環(huán)境的置換以及民族情結的重現(xiàn),使得民族詩人們感嘆帝國疆域之遼闊、物產(chǎn)之豐富的同時,將豪縱闊達的時空感自然融入詩中。比如至治三年(1323),馬祖常、袁桷、虞集扈從上京,途徑元代名驛槍桿嶺,三人停馬提筆聯(lián)詩,圍繞槍桿嶺和個人際遇即興舉辦一場小型同題集詠。馬祖常作《至治癸亥八月望同袁伯長虞伯生過槍桿嶺馬上聯(lián)句》:
有嶺名槍桿,其上若棧閣,白云亂石鑿,青峰轉簾腳。積冰太古陰,出礦無底壑,馬飲沆瀣泉,鷹蕩扶搖幕。轍跡委垂紳,人聲發(fā)虛橐。舄飛接鳥背,羽沒疑虎膊。霧松秋發(fā)長,霜果紅頰薄。斤樵不知疲,獨往端有愕。兢兢矛頭浙,杌杌井口索。凝睇見日觀,引手探月廓。南下渺塵海,北廣絡沙漠。金橋群仙游,寶塔百神鑿。禽鳴蜀帝魂,鐵鑄石郎錯。闌干掛鉤衡,攙搶斂鋒鍔。屬車建前矛,馳道狗嚴拆。載筆三人行,弭節(jié)半途卻。?
其中“禽鳴蜀帝魂”一句運用“望帝(蜀帝)化鵑”的典故,“鐵鑄石郎錯”中的“石郎”指宋代石公弼。傳說望帝杜宇心系國家,在蜀地帶領百姓從事生產(chǎn),死后仍化為杜鵑飛到田間啼叫,提醒百姓到播種的時節(jié)了。宋代石公弼做宗正寺主簿時,疾惡如仇,直言不諱,彈劾奸臣蔡京數(shù)十次,后將蔡京貶出京城。二人皆有功于國家與百姓,馬祖常借此呼喚名臣治世,也希冀自己能為國家建言獻策。神話典故和歷史典故的運用實現(xiàn)了時間的跨越,為詩作增添了闊遠的歷史感。同時,詩中“棧閣”“白云”“青峰”“塵海”“沙漠”等物象的運用又將詩歌的空間感擴大。如此,詩歌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為我們展示了詩人磅礴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先用遠景營造大氣赫然的視覺效果,再用典故填充因大而略顯空曠的空間維度,增添詩作歷史沉淀感,于是整首詩就猶如一位飽經(jīng)滄桑的將軍在追憶過去的崢嶸歲月,偉大而又深沉。楊義在評價馬祖常的詩作時用了“豪縱的氣質”這一短語,?顯然這一特點的形成與詩中時間的縱深和空間的擴張有關。
再如馬祖常《和袁伯長待制送虞伯生博士祠祭岳鎮(zhèn)江河后土二首》。?在元代,“官僚政客以王命出使四方,館閣群人往往賦詩送別”。?延祐三年,虞集奉詔前往西部祭祀名山大川,與虞集交好的新朋舊友紛紛賦詩送別,馬祖常此詩就作于此次同題集詠。另有王士熙《送虞伯生祭祀還蜀用袁待制韻》、?柳貫《奉同伯庸應奉韻送伯生博士行祠西岳因入蜀望祭河源二首》?等。馬祖常詩作其一“芙蓉仙掌坐中低”運用漢武帝在建章宮造銅仙人這一事典,“使者才華似揚馬,題詩應進草堂西”將虞集才華與草堂主人杜甫作比,既對應入蜀這一主題,又贊美虞集才華冠絕有過人之處。“棧路”“蜀天”“岐陽”三個物象和地點名詞同樣將詩歌觸角放遠,讓人讀罷會不自覺地極目遠眺,領會詩歌時間感和空間感延長擴大所帶來的藝術之美。
(二)靈動自然的動態(tài)美
在繼承傳統(tǒng)同題集詠即時性、集體性特征的同時,北方民族詩人因其歷史與文化的獨特性,同題集詠漢文詩更擅長描摹喧鬧的場面和變動的意向,詩作具有靈動自然的動態(tài)美感。詐馬宴是元代皇族在上都舉辦的盛大宴會,一年舉辦一次。據(jù)王祎在《上京大宴詩序》中記載,詐馬宴在皇帝使用的大宮帳“失刺斡耳朵”中舉辦,場面盛大,輝煌異常:“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馬,窮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后就列,世因稱曰詐馬宴,又曰只孫宴。”“然則鋪張揚厲,形諸頌歌,以焯其文物聲容之烜赫,固有不可缺者,此一時館閣諸公賡唱之詩所為作也。”?目的是“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上下之情者也”。?作為一次大型文藝聚會,少不了詩人作詩歌詠盛世:“詩自宣文閣授經(jīng)郎貢公為倡,賡者若干人,總凡若干首。”?廼賢有《失刺斡耳朵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jīng)先生韻五首》,?詩句“象輦時從黃道出,龍駒牽向赤墀嘶”用巨輦、良駒出場展現(xiàn)出詐馬宴的宏大場面,讀后耳邊似響起大象和馬駒的嘶鳴,“伯梁競喜詩先捷,羽獵爭傳賦最豪” 一句中,“競”“爭”二字描摹了文人群體才思敏捷,爭相作賦的熱鬧場景。詩豪們你爭我搶,卻毫無嫉妒之心,只為酣暢淋漓地享受盛宴。這五首詩都表現(xiàn)了廼賢對元朝大一統(tǒng)局面的由衷贊美。廼賢另一首同題集詠詩作《次上都崇真宮呈同游諸君子》?同樣動感十足,豪氣滿懷:“雞鳴涉灤水,慘淡望沙漠。穹廬在中野,草際大星落。風高班馬嘶,露下貂裘薄。晨霞發(fā)海嶠,旭日照城郭。嵯峨五色云,下覆丹鳳閣。琳宮多良彥,休駕得棲泊。清樽置美酒,展席共歡酌。彈琴發(fā)幽懷,擊筑詠新作。主時屬承平,幸此帝鄉(xiāng)樂。愿言崇令德,相期保天爵。”從“涉”“望”“落”“嘶”到“發(fā)”“照”“詠”,動詞的流轉適應了詩情從低落到高昂的變化,整體詩歌流暢連貫、豪放平實,具有動態(tài)美感。此詩作于廼賢與友人在上都崇真宮雅集之時,“崇真宮雖然是一個道教場所,但是,這里在元代一直是文人聚會雅集的重要場所”。?
三、民族詩人同題集詠創(chuàng)作的社會語境
同題集詠在漢族文人圈中的繁盛與科舉制度的時興時廢及民族政策偏倚關系密切。元朝一度廢除科舉制度,即使后來恢復科舉,依然有很多的保護性政策,漢人、南人與蒙古人、色目人中舉名額均等,總人數(shù)更多的漢族士子落榜比例增大,文人拯時濟世的社會政治理想無處實現(xiàn),以至于“士失其業(yè)”,從而由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轉向向內(nèi)“修身”。舉辦雅集、吟詠唱和、群體賦詩,實在是他們巨大落寞感之后的無奈之舉,同時也是互相安慰、支持、肯定的有效途徑,有助于表達時代困境下的生活態(tài)度。“在這種情況下,借用科舉考試的形式來進行詩社活動,實際上就有了模擬科舉考試的性質,知識分子可以通過參加這一活動,‘復喚起青衫之夢’,得到些許精神補償。”?相比較而言,北方民族詩人熱衷于同題集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施行漢法的政策環(huán)境
基于穩(wěn)固政權的需要,元世祖忽必烈就曾倡導恢復科舉,但未能實行。中統(tǒng)四年,翰林學士王鶚等人上表:“唯科舉取士,最為切務。”?于是忽必烈時設立國子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jīng)書,俟其藝成,然后試用”,?培養(yǎng)蒙古、色目能士治理國家的能力,為王朝所用。為提高在朝為官者的治國水平,元仁宗時正式恢復科舉,考試范圍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明確說明采用朱熹編撰的章句集注。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jīng)問的選拔標準是“義理精明,文辭典雅”,?第二場古賦昭誥的答題要求是“用古體”,?與前朝科考標準別無二致,并被明清兩代沿襲。
在這樣的政策環(huán)境下,蒙古、色目弟子得以系統(tǒng)學習中原傳統(tǒng)文化,培養(yǎng)儒家胸懷,與漢族人同朝為官或拜于同一師門,這就具備了參與同題集詠的文化條件,也更容易對文人集會產(chǎn)生興趣。同時,投身中原文化活動,與漢族文人交流融合,也為熟諳漢人經(jīng)術文學帶來極大幫助,從而有助于科舉答題。正如蕭啟慶所指出的那樣:“經(jīng)術文學的掌握,對蒙古上層家庭子弟而言,可以作為服官佐治的工具。對中下層子弟及上層家庭一些庶子而言,則可作為打開登仕之門的敲門磚。”?
(二)開放多元的文化氛圍
元人馬上取天下,更信服武力。沒有學禁,沒有文字獄,禮法束縛相對松弛,同時元代疆域遼闊,族群眾多,人員流動頻繁。這種開放多元的文化氛圍更有利于詩人馳騁詩情,盡興酬唱,為各族士子雅集聚會、同題集詠提供了相對寬松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透過文史互證的視角,可以看到元代詩歌顯示出與國家政治生態(tài)相呼應的特點——主題開放,忌諱少,自由度高。對于當時參與同題集詠的詩人來說,詩的題目好像已經(jīng)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參與聚會本身。到了元末,這種輕禮法,重本心的特征愈加顯明,“主情” 成為元末詩學領域的一股清新的氣息,元末文壇領袖楊維楨就曾提出“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強調詩人作詩時不吝個性[1]。當時甚至出現(xiàn)了薩都剌《紀事》這首揭露文宗、明宗兄弟相殘真相的詩作:“當年鐵馬游沙漠,萬里歸來會二龍。周氏君臣空守信,漢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璽傳三讓,豈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灑淚,世間骨肉可相逢。”?清代元詩專家顧嗣立評價此詩:“史氏多忌諱,紀事只大抵。獨有薩經(jīng)歷,諷刺中肯綮。”?可見當時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之寬松。
(三)文人雅集的時代風尚
如果說統(tǒng)治者施行漢法、文化多元開放是同題集詠的肥沃土壤,那么文人喜愛雅集酬唱的社會風尚就是促使它枝繁葉茂的潤澤春風。
不喜祿仕的心態(tài)和舒緩的政治氛圍讓文人們將視線從弘道明理、治國齊家轉移至個體精神滿足上,促發(fā)了元代士人培養(yǎng)詩、書、畫兼擅的基本技能。寄情山水、聚會交游、觸景抒懷也成了元代士人最常見的雅集緣由。也就是說,文人們大規(guī)模舉辦、參與同題集詠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賞玩的態(tài)度在尋找心靈慰藉。比如時任宣政院使的廉惠山海牙曾主持了一次玄沙寺小集,“這次雅集匯集了乃蠻人答祿與權、畏吾人廉惠山海牙,以及漢族人貢師泰等人,甚至還包括僧人藏石師,是一場典型的多民族的盛會”。?相比于其他雅集,這次雅集氛圍更加開放和隨意,包括飲酒、歌舞甚至戲謔活動。“及至,則四君子已坐久飲酣……皆執(zhí)酒歡迎,互相酬酢。廉公數(shù)起舞,放浪諧謔……清溪雖莊重自持,聞道夫言輒大笑。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傾欹傲兀,為之扺掌頓足焉。”?但此次雅集并不止于玩樂。在即將離去之時,幾人痛感時局動蕩,只覺不可沉湎于杯勺之間;但又無所事事,因此暫且把此次聚會當成療愈心靈的遣興活動:“方今寬詔屢下,四方兇頑猶未率服,且七閩之境,警報時至,而吾輩數(shù)人,果何暇于杯勺間哉? 蓋或召或遷,或以使畢將歸,治法征謀,無所事事,故得從容,以相追逐,以遣其羈旅怫郁之懷。然而謝太傅之于東山,王右軍之于蘭亭,非真欲縱情丘壑泉石而已也。夫示閑暇于搶攘之際,寓逸豫于艱難之時,其于人心世道亦豈無潛孚而默感者乎? 他日當有以解吾人之意者矣。”?所以幾人以杜甫“心清聞妙香”之句分韻,各賦五言詩一首。杜甫“心清聞妙香”出自《大云寺贊公房》其三,也是杜甫在大云寺暫時忘卻塵世紛擾時所作。
再如至正十一年廼賢等七人出游燕城,出游途中觸摸古跡,感念世事無常,于是偶發(fā)一次同題集詠:“覽故宮之遺跡,凡其城中塔廟樓觀臺榭園亭,莫不徘徊瞻眺,拭其殘碑斷柱,為之一讀。指廢興而論之,余七人者,以為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有足惜者,豈獨感慨陳跡而已哉。各賦詩十有六首以紀其事,庶來者有所征焉。”?雅集酬唱中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大量民族詩人參與同題集詠、創(chuàng)作漢文詩的重要原因。雖然統(tǒng)治階層用森嚴的民族政策將元人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層次,但是在民間私宅、山水佳處,文人交往不限身份、不限民族,因為相同的志趣和旨歸聚集,切磋詩藝,共同享受生活,群體的精神志趣已凌駕于族群之上。不僅民族詩人主動融入,漢族詩人同樣將民族詩人納入自己的交際圈中,“漢族士人亦視蒙古、色目士人為己類,如許有壬稱蒙古酎溫臺氏萬家閭‘確然無間于吾徒’,許謙稱奈曼和利氏魯古訥丁‘吾黨之士,鮮能及之’”[2]。各族詩人唱和贈答、同題集詠,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一篇篇優(yōu)秀的作品。
(四)托詩留名的文人傳統(tǒng)
雖然托詩留名有附庸風雅、追慕名利之嫌,但是追求以文名世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寫作的宏愿。比如《國語·晉語八》就記載:“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謂死而不朽。”?盡管這里的“文”與漢文詩的“詩”不盡相同,但二者都是作者思想的顯現(xiàn)。除了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托詩留名也可看作是民族詩人對于自身價值的肯定,這種價值就是民族詩人意識到可以通過寫詩確立穩(wěn)定的社會歸屬以及社會定位,擔負起文人中的“文”字和“文”字背后的風騷雅趣。總體來看,托詩留名算是除前述原因之外的附加項。
除了賞玩這類純娛樂的理由,托詩留名也成為部分民族詩人參與集詠的較為冠冕又相當合理的緣由。對元代詩風形成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元好問就在《中州集》 中表達過作詩留予后世的想法:“特別是金元之際元好問編《中州集》,給元初南方文人兩點啟發(fā):第一,渴望有人(自己或他人)匯編宋末一代詩集,借以為宋末存一時之史;第二,自己要作詩,以備他年有人輯錄,以便托詩留名以不朽。”?
著名元代文學學者李修生先生說過:“元代是一個多民族相互融合、又與外界有著廣泛交流的時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這兩個特點。”?中國文學史不只是漢族文學史、主流文學史,更應該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文學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學作品,為中國文學發(fā)展注入新的生機。北方民族詩人同題集詠的漢文詩創(chuàng)作不僅是民族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為民族文學史添磚加瓦,更讓后人見證了元詩的勃勃生氣。
注 釋:
①?????[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②③[清]顧嗣立.元詩選癸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
④蒙翔.元代上京竹枝詞之新變[J].陰山學刊,2022(02):20-24+54.
⑤⑥[元]袁桷著,張亮校注.袁桷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⑦???[清]顧嗣立.元詩選二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
⑧??馬祖常著,李叔毅點校.石田文集[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⑨楊鐮.全元詩(第34 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3.
⑩????[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
???[元]顧瑛輯,楊鐮,葉愛欣整理.玉山名勝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8.
?[清]顧嗣立.元詩選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
?[元]張昱.可閑老人集卷三[Z].文淵閣四庫全書.
?李修生.全元文(第25 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1999.
?楊義.中國古典文學圖志(宋、遼、西夏、金、回鶻、吐蕃、大理國、元代卷)[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
?唐朝輝.元代文人群體與詩歌流派[M].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
?楊鐮.全元詩(第25 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3.
???李修生.全元文(第55 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1999.
?劉宏英.元代上京紀行詩研究[M].北京: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2016.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第2 版)[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蕭啟慶.內(nèi)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7.
??[元]薩都剌.雁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張建偉.高昌廉氏與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4):113-117.
??李修生.全元文(第45 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1999.
?陳桐生譯注.國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3.
?查洪德.元代詩壇的雅集之風[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06):669-677.
?李修生.全元文(第1 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