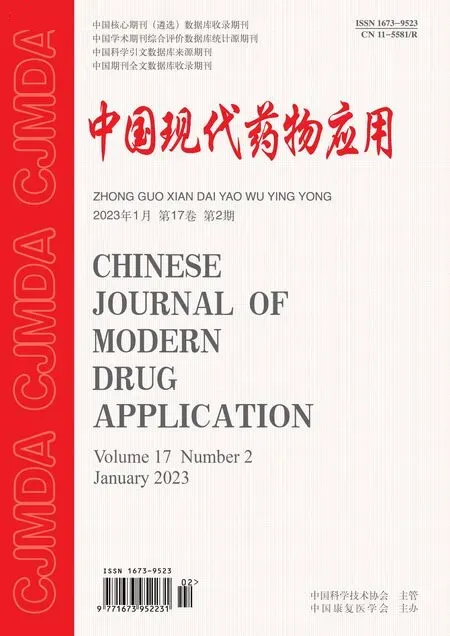保留器官功能的胰腺切除術在胰腺實性假乳頭狀瘤外科治療中的應用
張思睿
胰腺實性假乳頭狀瘤(solid pseudopapillary neoplasm of the pancreas,SPN)約占胰腺外分泌腫瘤的2.7%和囊性胰腺腫瘤的5.0%[1],1996 年,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命名為SPN 并將其歸類為胰腺外分泌低度惡性腫瘤,大多數患者呈孤立的局限性病變且完全切除后預后良好,僅在10%~15%的患者中可能出現轉移或局部浸潤。最近報道稱,SPN 是40 歲以下女性患者中最常見的胰腺腫瘤,約占40 歲以下患者胰腺腫瘤總數的1/3[2]。隨著醫學影像學技術的進步和對胰腺囊性腫瘤更充分的鑒別診斷,SPN 的發病率增加。對位于胰頭或胰體尾的SPN,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和遠端胰腺切除術聯合脾切除術(distal pancreatectomy with splenectomy,DPS)分別是外科手術治療的標準操作。盡管這兩種手術具有根治性切除和降低腫瘤復發風險的優點,但也導致胰腺實質過多喪失以致胰腺外分泌和內分泌功能受損[3],還有膽腸、脾臟的結構破壞。多數SPN 患者發病年齡較小且具有較長的生存期,除考慮切除預后及復發風險外,術后生活質量也應納入考慮范疇[4]。在SPN 外科治療中,保留器官功能的胰腺切除術開始被臨床更多的考慮,包括腫瘤摘除術(enucleation,EN)、胰腺中段切除術(central pancreatectomies,CP)、保留脾臟的胰腺遠端切除術(spleen-preserving distal pancreatectomy,SPDP)、保留十二指腸的胰頭切除術(duodenum-preserving pancreatic head resection,DPPHR)等。保留器官功能的胰腺切除術目前尚未有標準的手術指征,目前有一系列相關的病例報道可供參考以探究SPN 患者中保留器官功能的胰腺切除術的臨床優勢和劣勢。
1 EN
摘除術作為一種侵入性較小且保留實質的手術,應用于一些良性或低度胰腺腫瘤,包括SPN。EN 存在比較嚴格的適應證,有研究顯示,腫瘤和主胰管之間的距離≤3 mm 可以作為摘除術后胰瘺發生率增高的獨立危險因素[5],且要求腫瘤不存在局部周圍組織和血管侵犯。腫瘤的大小也是評估適應證所需的重要因素,大腫瘤(直徑>3 cm)與小腫瘤相比,其發生主胰管損傷和術后胰瘺的風險較高(64% VS 31%,P<0.05)[6],同時大腫瘤具有更大的潛在惡性風險,需要仔細進行術前影像學評估。目前通常認為摘除術只適用于直徑<2 cm 的腫瘤,腫瘤與主胰管之間的距離需要>3 mm,然而,這一點尚未得到大型臨床數據庫的驗證[7]。
摘除術的主要優勢在于最大程度保留胰腺功能。據Crippa 等[8]報告顯示,實行EN 后患者激發內分泌和外分泌功能不全的發病率<2%。在一項納入1101 例接受摘除術患者的Meta 分析中,結果顯示摘除術使術后內分泌功能不全發生率降低[95%CI=(0.1,0.5),P=0.001]和外分泌功能不全減少[95%CI=(0.02,0.20),P<0.001][9]。與傳統的胰腺切除術相比,摘除術的手術持續時間更短,失血量更少[10]。
從術后短期并發癥來看,目前的研究中,摘除術后的胰瘺發生率似乎高于常規切除術后,但統計學結果并不顯著(19.4% VS 8.6%,P=0.180),且胰瘺發生率升高在臨床治療下并沒有導致更高的嚴重發病率[10]。SPN 術后仍有風險發生局部復發或轉移,這也是決定是否采用EN 的主要問題,一項長期隨訪(平均 46.1 個月)顯示,摘除SPN 與傳統的胰腺切除術相比并不會導致腫瘤復發或轉移率增加[10]。目前經驗保證切緣陰性的摘除術似乎足以滿足治療胰腺低級別SPN的需求。
2 SPDP
>40%的SPN 累及胰腺尾部,一般情況下,對累及胰體尾部的腫瘤多選擇DPS,然而研究表明,對包括SPN 在內的良性或低度惡性腫瘤應避免切除脾臟,因為脾臟在免疫系統中有重要作用,且脾切除術可能引發嚴重并發癥,如血小板增多癥、癌癥風險和脾切除術后感染等[11]。此外,一些病例系列報道顯示,脾切除術對長期生存有負面影響。因此SPDP 受到越來越多外科醫生的提倡。
在國內多項相關臨床研究中,保留脾臟與切除脾臟的胰體尾切除術的手術時間、手術切口長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12-14],而保留脾臟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等圍術期指標優于切除脾臟的對照組[14]。Pendola 等[15]通過Meta 分析證實,SPDP 和DPS 術后胰瘺的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且SPDP 術后腹腔積液和腹腔膿腫的發生率更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術后脾靜脈(SVT)和門靜脈(PVT)血栓形成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在術后平均(28.3±3.8)個月的長期隨訪期間,接受SPDP 和DPS 手術治療的患者中成功隨訪的均無腫瘤復發、轉移或死亡病例[13],提示SPDP并不伴有更高的復發風險。
迄今為止,腹腔鏡下遠端胰腺切除的脾臟保留率在32%~84%。SPDP 通過兩種主要技術進行,一種是分離結扎小血管分支保留脾血管,即脾血管保留(SVP),保留正常的解剖結構,但其相對耗時且復雜。1988 年Warshaw[16]報道了一種新技術,切斷脾動脈、SVT 而由胃短血管和胃網膜左血管為脾臟供血。Warshaw 法(WT)因術中失血量低和手術時間短而很快流行,但術后脾梗死和胃底靜脈曲張的發生率較高[17]。SVT 被胰腺包圍,特別是在腫瘤包繞情況下難以分離,SVP 手術因大出血可能性而需要轉換為WT,目前在多數醫療中心,SVP 始終是SPDP 的初始計劃,術式是否需要切換到WT 的影響因素主要在于腫瘤大小、腫瘤與脾血管位置關系和切除胰腺的長度等[18]。
3 DPPHR
小部分SPN 位于胰頭部及鉤突,PD 是公認的胰頭惡性和良性腫瘤的標準外科手術,但PD 包括十二指腸、膽道和胰腺組織多器官切除,容易導致較高的術后早期并發癥和長期代謝性疾病的發生風險。20 世紀70 年代,Beger 等[19]首次提出DPPHR用于治療慢性胰腺炎患者,1988 年,相關學者第一次使用DPPHR 治療胰頭的良性或低度惡性腫瘤,保留十二指腸及其來自胰腺十二指腸動脈的完整血液供應[20]。DPPHR 保留了十二指腸和膽道的完整性和更多胰腺實質,可降低對糖代謝和消化功能的影響。最近的一項系統綜述顯示,DPPHR 術后遠期糖尿病的發生率明顯降低(14.1% VS 5.0%),外分泌功能不全發生率亦明顯降低(44.9% VS 6.7%)[21]。從安全性角度考慮,無論是短期并發癥如胰瘺、胃排空延遲甚至住院死亡率,還是腫瘤復發風險,PD 與DPPHR間未見顯著差異[21]。目前國內各級醫療中心也在積極開展DPPHR 治療胰頭部SPN,亦取得了樂觀的 結果[22,23]。
DPPHR 的最新進展得益于微創技術的改進,中山大學Cao 等[24]2019 年報告了12 例腹腔鏡下DPPHR用于治療胰頭良性或低度惡性腫瘤,術后結果良好,且與開放性DPPHR 手術相似的并發癥風險更低。腹腔鏡下DPPHR 將DPPHR 的優點與微創手術相結合,但為保護十二指腸血液供應和膽總管(CBD)對手術技術有更高的要求。
4 CP
CP 術中切除中段胰腺后,殘余兩個胰腺殘端,遠端胰腺殘端與空腸襻行端側吻合;而胰腺近端殘端予縫合關閉,或者同樣行胰腸吻合,其更多地保留了頭部和遠端的胰腺實質。對位于胰腺頸部和近端無法摘除的病變(腫瘤直徑>2 cm 或距離主胰管位置過近等),CP 是一種可能的替代方案,特別是剩余的遠端胰腺長度>5 cm,且沒有任何鄰近器官或胃十二指腸動脈受到侵襲的情況下[25],目的是保留胰腺實質并降低內分泌和外分泌功能受損的風險。
一項2019 年的Meta 分析顯示[26],CP 切除胰腺長度顯著少于遠端胰腺切除術(DP),接受CP 的患者圍術期間術后胰瘺的發生率明顯高于接受DP 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術后出血、感染及胃排空延遲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內分泌功能不全的總體發生率,包括糖尿病新發或惡化,與DP 組相比,CP 組的總內分泌功能不全率顯著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關于CP 在保存胰腺實質及保持外分泌功能的具體作用,Lee 等[25]回顧性研究提示,CP 組和PD 組在術后12 個月觀察到殘余胰腺體積 (44.9 ml VS 23.6 ml)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且CP 組和PD 組術后12 個月患者糞便彈性蛋白酶水平(151 μg/g VS 245 μg/g)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3)。與DP 相比,CP 術后胰瘺的發生率更高,但總體術后并發癥發病率相近,在胰腺外分泌功能和胰腺實質保存方面CP 則顯示出明顯優勢。目前CP 通常發生在年輕女性中,47~52 歲女性占接受CP 患者的59%~73%,除較多應用于NET 外,近年也正被積極用于SPN 的治療[27]。李森等[28]相關研究中,CP 應用于SPN 的治療同樣獲得積極的結果,且在隨訪期內未發現腫瘤復發的病例。CP 在維持SPN 手術患者胰腺功能、改善長期預后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其限制在于術后早期并發癥的控制,隨著微創外科技術的發展,腹腔鏡及機器人與CP 的技術結合為提高手術安全性、減少胰瘺等并發癥提供更多可能性。
5 小結
根據已發表的研究得出,與常規胰腺切除術相比,器官保存策略的術中損傷、出血更少;雖然存在術后早期并發癥如胰瘺發生率較高的風險,但通常可以通過保守治療恢復;根據遠期隨訪,保留胰腺功能的患者術后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或術后新發糖尿病的可能性顯著降低[4],保留脾臟功能的患者術后感染、出血等短期并發癥及脾臟相關后遺癥也能夠獲得明顯改善;短期隨訪內也未發現較高的腫瘤復發率。
但目前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理想情況下應該通過精心設計的前瞻性分析評估,但由于病例數量有限受到極大限制。大多數相關研究采用回顧性的臨床研究形式,或者Meta 分析,因此缺少一些實驗室數據、精確的腫瘤相關信息等。無復發生存期和局部復發率等腫瘤學結局決定手術過程的最基本要素,但目前研究隨訪時間總體較短。而由于研究的局限性,手術適應證還沒能嚴格定義,探查術者的經驗仍然是判斷能否進行保留器官功能手術的關鍵。鑒于胰腺切除術經驗的增加,手術技術和圍術期管理的進步及新設備的引入,保留器官功能的胰腺切除術的報告也在增加,將來可能會有更多機構報告更多病例以供參考研究,在基于逐漸增加的臨床數據積累獲得明確的答案前,關于保留器官功能的胰腺切除術的爭議可能仍會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