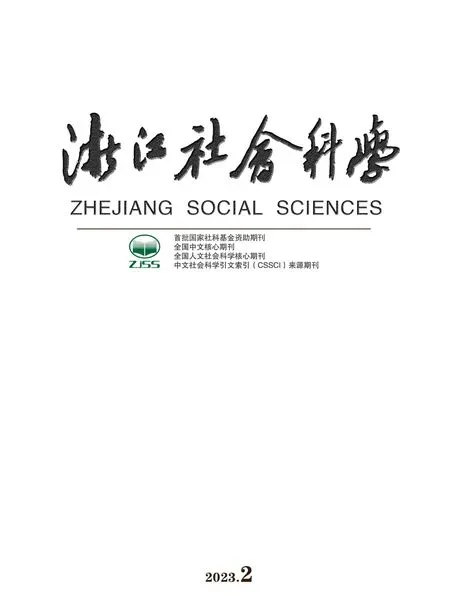論文學經典化中的文化權力轉移與文明新識*
□ 魏麗娜
內容提要 文學經典的生成、演變與流傳,與近現代社會制度、文化權利轉移和審美體制形成有密切關系,具體呈現為“經典化”“去/反經典化”“再經典化”的相關機制與過程。 秉承知識社會學立場的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人類學、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流派,以“上-下對沖”的文化權力斗爭方式,破壞了現代主義構建的文化“板結”,“沖決”了知識領域的“割據”與思想領域的“等級”,并將傳統經典生成的“潛規則”公諸于眾——貌似嚴肅莊重和苦大仇深的歷代經典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合謀”。不斷涌現的文學經典的時代重構,蘊藏著文化權力的斗爭與文學場域的博弈,也帶來了思想視域的拓展與文明新識的構建。“二戰”后興起且至今盛行的女性批評,帶來了性別政治的兩性發現與兩性平衡的文明更新,文學經典的歷史浮沉與權力轉移浸透著思想的能量和文明的憂思。
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 文學經典的出現與被認可,與近現代社會制度、文化權利轉移和審美體制形成有密切關系。在文學經典的生成、演變與流傳進程中,民族區域文化的選擇、人文藝術歷史的沉淀、時代審美趣味的影響、社會政治標準的制約等至關重要,具體呈現為“經典化”的相關機制與過程,以及“經典化”的延伸或“一體兩面”性問題——“去/反經典化”和“再經典化”,即“去/反”已有的經典認定,進而調整、補充、拓展現有的文學經典體系,以完成文學經典的歷史“演變”與時代重構, 而具體的細節性差別只在于起因是屬于個體性的敏銳或先覺、群體性的政治蠱惑還是合力性的審美趣味。實際上,真正能夠站在解構主義立場、徹底否定或“反對”文學經典的并不占主流,他們只是人類文明史“邊線”處一直都有的“反”文明勢力或文化“無政府主義”的翻版或變種,但其存在價值和“參照系”意義不容小覷,猶如詩劇《浮士德》中靡菲斯特的存在之于上帝的價值,從一定程度上說,他們是人類文明保持活力的深層能量。
一、文學經典的時代重構與經典生成的權力斗爭
一般來說,“經典”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權威性和永恒性,或是經過歷史淘汰、優勝出來的被證明是最有價值的特殊文獻, 或是對某個領域產生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①從宏觀層面看,文學經典是指那些蘊含人類共識性的審美價值和道德價值的代表性文學作品, 他們具有超越歷史的、地域的、民族的②甚至功利層面的永恒性與“偉大性”(greatness)。 從當今學術視野來審視,此類文學經典理念顯然屬于印刷/平面媒介時代文學語境中的產物,其本質是封閉的、自律的、模范的和規定性的,即把文學經典看成是靜態的客體,因此,追求永恒性與不變性是此類經典化的內在邏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美國家興起的“文化研究”③,恰恰是要置疑文學經典的這種本質主義建構及其所謂普遍性、永恒性、純審美性或純藝術性,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去經典化”浪潮。④
通過一系列非精英化的“去魅”和視角調整,文化研究更多地秉承了知識社會學的立場, 認為文學經典以及經典的標準實際上總是具有特定的歷史性、階級性、特殊性和地方性;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經典問題被還原為文化權力問題或從權力的角度進行理解,個體性的權力介入(譬如批評家的作用)和整體性的“權力轉移”(譬如國家權力的哄抬與打壓)勢必極大影響文學經典的生成、演化與傳播,因此,文化研究的文學經典理論必然帶有極大的政治性⑤與反體制性。其理論和思想貢獻在于:調整視角,注重日常,將文化生成拉回到市民社會的日常生活;為精英文化“減負”,替文明史“減壓”,告訴人們一臉嚴肅和苦大仇深的歷代“經典”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合謀”。“文化研究”以及其后的“跨文化研究”,以“上-下對沖”的權力斗爭方式,破壞了現代主義構建的文化“板結”,與文化人類學等一道“沖決”了知識領域的“割據”與思想領域的“等級”,使文化藝術的諸領域日趨“柔和”和“融通”,并將傳統經典生成的“潛規則”公諸于眾。
文化研究并不把經典視作想當然的現成物,也不認為它們是普遍的、不帶偏見的審美標準的體現。 他們甚至從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謂文學作品“固有的”美學價值與文學價值,認為這種價值實際上不過是披著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 是以無功利性為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 用法國哲學家布迪厄的話來說,就是“超功利的功利性”。他們質詢經典化過程背后的權力關系,包括所謂普遍的“審美價值”“文學價值”的非普遍性、歷史性和地方性,揭露“經典化”中隱藏的精英掌控的等級陰謀與意識形態標準。⑥英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弗蘭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1919—2010)在《經典與時代》一文中給人們透露了一些“內部”消息。他認為,經典總是與權力合謀, 它為主流意識形態塑造“過去”,并將“過去”變為“現代”。 因此,經典成了“反叛者”對抗權力的斗爭所必須占領的主要領域。⑦
“改革開放”40 多年來的現代化進程是幾代中國人共同努力與奮斗的結果。然而,也許是源于缺乏精神維度的商業沖動和物欲沖動,21 世紀的消費主義與娛樂至上主義相結合, 以沒有任何價值底線的“一點兒正經也沒有”,史無前例地呈現出“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曾經神圣的傳統和文學藝術經典被現時代的人 “戲說”、“大話”和隨意“誤讀”、“強制闡釋”。因此,盡管近些年大量類似“世紀經典”“大師文庫” 的選本相繼問世, 卻很少能夠得到學界自身和大眾讀者的一致認可。在一個文化范式調整未曾到位的時代,盲目叛逆和反抗權威造成了道德觀念之間的沖突、非正統因素對正統因素的挑釁等。⑧因此,經典的辨析與再造成為一個相當艱巨的文化發展課題。
美國學者赫伯特·格拉貝斯在《文化記憶與文學經典》一文中對“經典”作了非常精確的概括,他認為“經典是個人或者群體共享價值的客觀化”,由此, 它們在更大的文化框架內擁有相當高的聲望。⑨根據荷蘭著名學者佛克瑪和蟻布思的研究,中西方的文學經典至少經歷了下述重大危機。 在西方,中世紀向文藝復興過渡時期,拉丁語文學經典遭遇民族方言(俗語)文學的挑戰;古典主義向浪漫主義過渡時期, 古典主義戲劇經典遭遇浪漫主義小說與詩歌的沖擊。 而在中國, 當儒家中國(即封建時期的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時,儒家經典也遭遇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的質疑。佛克瑪的研究沒有延續到當代,其實在當代中國,文學經典遭遇的危機更加深重。⑩
由于時間久遠, 文學經典反映的社會生活與表達的情感范式,都與當代生活有著巨大的落差,當代人難以與其達到共鳴。 無論歐洲的騎士抒情詩、古典主義戲劇、現實主義小說,還是中國的唐詩、宋詞、明清小說,反映的無非是農耕文明或工業化文明時期的社會生活。 當今世界已進入互聯網主導的信息化時代, 文學經典反映的情境與今天的生活愈發隔膜, 人們的心理和情感形式肯定與經典的表達有巨大差別。 在今天高度發達的通訊技術面前,年輕人很難理解古人詩歌中“心有千千結”的離愁別緒,在世界已成“地球村”的今天更別指望有多少人對著一輪皓月發思鄉之幽情。?
毫無疑問,價值層級的變化因時代變遷、社會轉型、技術升級等或隱或顯地發生著,而文學經典的新陳代謝與歷史“切換” 也不免受此影響而變化。 除了以上提及的“歷史隔閡”,當代人的“代際差別”也愈發拉大,飽讀文學經典之士與80 后、90后的隔閡與差距幾乎可以用“對牛彈琴”或者“雞跟鴨講”來形容。平面媒體承載的高貴“經典”與互聯網時代的大眾文化,必然性的“血統式權威”與偶然性的“交互式體驗”愈發涇渭分明、天人相隔。這是真實的現實,我們必須面對也必須包容,因為人類文明發展正從封閉的、單一邏輯的“一元更替”進入開放的、多元并存的“多軌”“復調”時代。
二、文學經典的場域博弈與文明理念的時代更新
實際上,無論按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布迪厄的“場域”理論,還是“納粹極權”時代的“文學從屬政治”、女權主義實踐中的“走出家庭”與“姐妹情誼”、互聯網時代的“交互式體驗”的文化生成與傳播等特殊表現, 文學經典中的歷史演變背后都蘊藏著“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的強勢邏輯。已有的世界文學經典體系,往往因為女權的自覺、政權的更迭、歷史文明的反正等“權力變更”而受到強力沖擊,“去/反經典化”后進而調整、挖掘、補充,新舊文學經典藉此而得以更換,完成“再經典化”, 而新元素的融入標準則是基于新的“文明共識”。 由此可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不但國際政治一直存在暗流涌動的“權力轉移”的區域變化與“文明共識”的時代重構,世界文學經典的演變過程同樣存在“權力轉移”的歷史浮沉與“文明共識”的不斷修正,既包括不分性別的“權力變更”,也包括有可能徹底顛覆現存文明史的“性政治”的“權力變更”。
文學與權力的關系體現在很多方面, 在當今的民主與“個人賦權”時代里,這種關系愈益復雜,而文學與現實政治、文明歷史之間的關系問題仍然是一個主要方面且較有爭議。英國學者邁克爾·伍德(Michael Wood,1948— )認為:“作為一個當代人,你就得將政治及歷史的中心性視為必然,就算你沒有一直談論它也一樣。說得明白一點,我不認為政治和歷史狹義地決定了文學, 但我也不認為文學是超越這兩者的。 ”“文學與歷史(的書寫)距離太近了,以至無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時候文學就是歷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文學以更加激進的形式引發歷史去做再度思考。 ”?而法國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 dieu,1930—2002)則依據自己獨創的“場域”理論,提出了“文藝場”概念,認為它是充滿了歷史、現實內容的開放性結構,其內部因與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抗而形成了“純生產”場與“大生產”場的兩極對立格局,并朝“象征資本”的積累方向發展。在藝術發展史上,波希米亞群體的誕生是文學藝術“場”形成的關鍵步驟,波德萊爾、福樓拜等人則終生堅定地追求文學藝術的自主性。顯然,布迪厄剝去了“文藝場”內作者的神圣外衣,使之還原為一個斗爭和爭取各種資本的行動者角色;“文藝場” 內的讀者也是文化資本的爭奪者,對“文藝場”之價值具有重要影響。?
毋庸置疑,文學作為一種話語權力,其屬性是通過文學在社會歷史語境中所具有的文化資本?的多寡來界定的。在符號資本稀缺的條件下,文學理所當然地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強勢地位; 大眾媒介的興起徹底改變了文化資本的安排與配置,當書籍不再是惟一的或最重要的文化資源時, 文學便從寶貴的稀缺資源過渡到充實乃至過剩的資源,這一變化導致了文學必然從中心走向邊緣。所以,“文學觀念由統攝一切的神祗的智慧, 降而為與統治階級同謀的‘文以載道’,再降為回歸到‘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自身。文學表征能力的降低以及指涉范圍的縮小,意味著文學權力的逐漸衰竭,以及文學合法化的逐漸流失。 ”?這些發展動態多數情況下是有益的, 盡管有可能出現短期的反復甚至倒退, 特別是在很多人尚不適應而存有抵觸心理的情況下, 譬如傳統經典無疑會成為現有民族優勢、階級優勢和性別優勢的有效載體。
偉大文學作品的內在力量, 來自于它的世界性與共識性價值,盡管這其中也有文明理念的“讓渡”與“更新”。 傳統的文學經典被解構或發生危機,一般是因為“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利的變動”與“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觀念的變動”, 這兩項是文學經典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 事實上,人們說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時代變了,文學經典生存的社會、文化語境變了,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利變了,而且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觀念也變了, 文學經典的標準和尺度也就發生了變化。?現代的經典“傳習”既要注重經典的大眾化、通俗化,更要注重經典的學術性闡釋和創新性發展。?當前,整個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盡管有時“改變”意味著痛苦,但是當今時代的“變化”日新月異且勢不可擋。對待文學經典的歷史演變,我們應該淡然處之,對待文學經典的當代劇變,也應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既要心存敬畏又要敢于創化。
進入21 世紀以來,西方政治、經濟力量過度干涉文學藝術的勢力仍然強大,異化了的“政治正確”與“市場化異動”常常直接干預文學藝術生產與傳播,而經濟利益的誘惑、打壓又常常使文學藝術尊嚴掃地,反人類、反人性、反文明等重大罪行在文學生產與傳播中屢有發生,“詩性正義” 往往只作用于精神自由的想象卻在政治極權和經濟重壓面前脆弱不堪,唯有依靠建立在強大公義基礎上的憲政法制才能眼眉吐氣。譬如在當今的德國如若有人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替納粹翻案必遭譴責甚至可能觸犯國家法律,而同樣是對待法西斯主義和種族屠殺,日本現政府卻將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和法西斯文學家大川周明(1886—1957)視若神明, 土耳其現政府也將勇敢揭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一戰”時期對亞美尼亞人大屠殺的著名作家奧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 )定性為“詆毀國家”?而判刑。 美國著名學者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Nussbaum,1947— )提出:“除非人們有能力通過想象進入遙遠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這種參與的情感,否則一種公正的尊重人類尊嚴的倫理將不會融入真實的人群中。 ”?努斯鮑姆曾試圖尋找一條折衷之路, 一方面肯定外在制度運作的主導性, 另一方面也試圖利用文學的想象資源以彌補制度之弊, 其用意就在于超越僵化的制度建構和功利主義的倫理學。 歷史和現實告訴人們,在文學經典的歷史演變中,正義的底線與道義的原則是根基, 無論文學作品的藝術性有多么高,反人性乃至反人類都是大忌,它不可能永駐文學經典的歷史殿堂。
三、性別政治的兩性發現與女性批評的文明重構
從詞源學角度講,“政治” 一詞在古希臘人眼中明顯具有褒義色彩,最早的文字記載是在《荷馬史詩》中,其最初含義是城堡或衛城,后擴展為城邦中的公民參與統治、管理、斗爭等各種公共生活行為的總和。?上古時代,以孔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思想家, 把政治等同于或歸結為倫理道德, 認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為了使人和社會達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曾說:“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相反,中西方也有以韓非和馬基雅維里為代表的思想家,把政治視為“權術”“統治術”,認為政治是爭奪權力、施展謀略和玩弄權術的活動。?因此,“政治”一詞便從源頭上留下了兩副面孔,一是光明的“至善”,與“理想”“樂園”相關;另一是陰險的“大惡”,與“謀害”“骯臟”相聯。 現在的“政治”一詞日趨中性化,一般多用來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至于中文語境中的基本語義,始自英文“politics”從日本傳入中國時,孫中山認定以“政治”一詞來對譯。他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是傾向中性的。
其實,“政治” 除了存在于人們熟知和習慣了的“公共事務治理”層面,也存在于“性別關系與權屬”層面,或者說“兩性之間的權力關系”,即女性主義思想家所強調的“性別政治”?。人們雖然一直都有關于自由獨立、不受他人支配與控制的政治理想,并以各種方式為實現這一理想竭盡努力,但遺憾的是,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未能真正實現這個政治理想, 而依仗某種權力支配其他人和其他群體的現象往往比比皆是。?女性主義研究在這個問題上的獨特之處, 是指出男女兩大群體的界定, 其實也是依據與封建等級制度類似的“自然”模式,在父權制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由男性對女性實行全面控制與支配,這在本質上與種族、階層、階級間的控制與支配并無二樣。?美國學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 )的“性別政治”理論明確提出,性別關系同種族關系、階級關系一樣,都是一種政治關系。她還對有關兩性關系的規范、制度進行了考察,發現“從歷史到現在,兩性之間的狀況”是“一種支配與從屬的關系”,即男人依據天生的、生物學性別就可獲得特權,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她認為,男權社會把生理差異作為依據,在男女兩性的角色、氣質、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為的價值觀念,并從意識形態、心理學、經濟、教育、神話、宗教等方面對其進行精心維護,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內在化,從而實現對女性的長久統治。?隨著人類文明視域的調整與擴展,那些赤裸裸歧視與壓迫女性的昔日文學經典正被逐出經典殿堂,相應地,女性地位上升、女性書寫受到尊崇, 其中的杰出作品被推舉為經典殿堂中的新貴。
確實,女人曾經由于顯不出能力和受到隔絕,既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能衡量自己。?進入經濟領域的努力和在社會上的不斷爭取,讓女性不斷認識自己、壯大自身,并對社會、對男性的書寫產生影響。同時,文學藝術領域的“厭女癥”和對女性的歪曲性書寫依然有待于擦拭與重寫。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1937— )指出:“迄今為止, 寫作一直遠比人們以為和承認的更為廣泛而專制地被某種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經濟所控制。 這就是對婦女的壓制延綿不絕之所在……在這里婦女永遠沒有她的講話機會。 因為寫作恰恰正是改變的可能,正是可以用來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變革社會和文化結構的先驅運動。”?她明確提出,女性也希望在文學領域做一個“真正的女人”。回望歷史,在19 世紀初的英國,勃朗特三姐妹以及其他女作家們還只能以男性的名字出版書籍。同時,女性形象一直以來在男性作家筆下被恣意涂抹、歪曲甚至被侮辱、被損害等,這些都是女性要改變的現狀。因此,眾多女性的前赴后繼與合力付出,使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抨擊立足于生理差異的“陽物批評”;第二階段,以女性自身視角解讀作品;第三階段,開展更加理論化、全面化的“女性詩學”批評。 女性在文學創作、批評領域的砥礪前行, 讓這一性別以不容忽視與歪曲的姿態存留在文學歷史中, 也在人類歷史中彰顯出健康、嬌美的身姿。?
根據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 garet Atwood,1939— )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使女的故事》第三季中,華盛頓的使女們被剝奪說話的資格,所有使女面罩下的嘴巴都被鋼圈禁錮。毫不夸張地說,這一象征性畫面,寓言化地暗示了女性為爭取自身的發言權所進行的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來艱辛抗爭的悲觀結果。 在這種現代文明的整體沉降中,令人欣喜的是,對自由的渴望與想象力的迸發在更多的女性身上展現出來——女性渴望擺脫附屬地位,想要做一個獨立的“真正的女人”。男女平等的兩性社會, 以及男性與女性的真正平等,不應僅僅是女性對自身權益的爭取,而是人類對一種更優社會狀態的共同追求。
關于“兩性之間的權力關系”的立場、觀點的尖銳對立,除了一大批女性主義理論家如瑪麗·沃斯頓·克萊夫特、弗吉尼亞·伍爾夫、西蒙·波伏瓦、克里斯蒂瓦、茜克蘇、伊萊恩·肖瓦爾特、朱蒂斯·菲特利、瑪麗·艾爾曼、凱特·米利特、凱特·蕭班、蘇珊·古芭和桑德拉·吉爾伯特等之外,在當代文學創作領域也有廣泛而深刻地反映,并通過這些文學作品傳導給廣大受眾群體,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聯動和輿論“場域”,前所未有地動搖了現有歷史觀念和文明秩序,使人們在相當程度上走出固化了的思維定式,大大拓展了思想視域。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小說家丹·布朗(Dan Brown,1964— )的《達·芬奇密碼》(The Da Vinci Code,2003)引導形成的輿論“場域”和思維延展。
20 世紀下半葉后, 后現代主義小說興起,其敘述特點可簡略概況為顛覆傳統和雅俗共賞。《達·芬奇密碼》是21 世紀初頗受矚目的后現代小說經典,它以“藝術方式”演繹了“神圣女性”由輝煌到妖魔化進而重生的歷史是在“權力”和“抵抗”這兩股此起彼落的力量作用下形成的, 兩性之間的關系也伴隨著“神圣女性”的歷史變化由平衡到失衡進而重新恢復到平衡。 丹·布朗對“真相”和“玫瑰”的執著,最終還是將他引向了一個小說家的結論:由于“人類歷史的危機”和“自我毀滅的危機”?,作者認為“有恢復神圣女性崇拜的必要”?,針對父權制的男性中心的價值觀, 讓女性重新圣化, 讓古老的女神信仰得到復興并引導未來的人類精神。?因此,“追尋圣杯,實際上就是要跪在抹大拉的馬利亞的尸骨前, 期望能在被遺棄的神圣女性腳邊祈禱。 ”?當今時代紛爭不斷,各式熱戰、冷戰、科技戰、貿易戰不斷上演,各種神秘組織團體泛濫,人們對于大地母親愈發不敬,自然美好的生態環境與本真和諧的人際關系瀕臨危機, 也許正是基于戰爭與殺戮的司空見慣,由宗教分歧和性別歧視引發的沖突與悲劇更是頻繁發生。?丹·布朗主張重塑女神精神, 表達了他對和平世界與和諧社會的渴望。
結語:文學經典化的歷史浮沉與文明憂思
基于文學經典在當今時代的復雜遭遇, 美國文學批評家萊斯利·菲德勒秉承“開放經典”?的理念,以“少數人文學”和“多數人文學”這兩個概念來區分文學,剔除了傳統上的高雅與低俗、正宗與邊緣(或次等)之分,顛覆了“經典”的固有標準。 在他看來,固有標準經常披著“教師與批評家們的忠告”的外衣,而踐行肢解經典并疏離其與大眾間情感的不義之舉。 顯然,這與美國書評人邁克·德達的觀點暗通款曲, 后者認為經典之為經典不是因為它們具有教育意義,而是“一代又一代、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的人們發現這些作品值得閱讀”,“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替我們表達出情緒和弱點,所有關乎我們人性的夢想和困惑”?。
有關文學經典的生成機制, 學界很早就達成了共識, 即在以布魯姆為代表的本質主義和以布迪厄為代表的建構主義之間建立起一種綜合、全面的經典觀:一方面受建構主義啟發,認識到經典不會自動呈現, 經典是在歷史中由多種因素、力量,通過多元途徑推舉建構而成,經典都有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同時,又接受布魯姆對作品藝術價值、審美價值的強調,認為作家作品經典化的根本依據或主導因素仍在于作品自身。?由此看來,文學經典的生成、演變與流傳,其“經典性”的成色與品質是內在的、決定性因素,而“經典化”過程更多地呈現為一種外在的歷史機遇。很顯然,文學經典化是一個多種力量參與、多方勢力博弈的復雜過程。在歷史長河的發展變化中,文學經典化既是一個自然前行的歷史過程, 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不必有意為之地限定單一的標準尺度,或沒有邊界地擴大范圍。?從文學性、藝術性的獨立價值來看,“經典化” 不是簡單地呈現一種結果或對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排座次, 而是要進入一個發現文學價值、感受文學價值、呈現文學價值的過程,可以說,文學“經典化”過程,既是一個歷史化的過程,又是一個當代化的過程,需要當代人的積極參與和不斷實踐。?由此看來,即便是作為歷史沉淀物和文化“傳家寶”出現的文學經典,也并非是一個蓋棺定論式的“最終結果”,頂多算是一個仍在輪回的“階段性結果”,因為對他們的具體認同一直存在著地域認同、時代認同、個體認同的巨大差異,他們自身更蘊藏著復雜的、不同的文化集體記憶、時代情緒和審美風尚。
注釋:
①?《今天為何要讀經典》,《光明日報》2020年12月5日。
②⑧傅守祥:《經典文化的焦慮:從精英掌控的標準到動態選擇的趣味》,《現代傳播》2006年第4 期。
③傳媒學者、“文化研究”風云人物約翰·費斯克(John-Fiske,1939— )在他的《英國文化研究與電視》一文中,開篇就說得很清楚:“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詞,側重的既不是審美,也不是人文的含義,而是政治的含義。 文化在這里并不是偉大藝術形式中的審美理想,也不是超越時間和民族邊界的“人文精神”,用來抵擋如潮洶涌、粗鄙污穢的物質主義,而是工業社會內部的一種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此種社會經驗的所有意義。 費斯克這里的話或許是矯枉過正,強調“文化研究”的對象是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日常生活方式,將致力于啟蒙和人文關懷的“大寫的文化”撇在了一邊,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性。
④⑤⑥陶東風:《文學經典與文化權力(上)——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經典問題》,《中國比較文學》2004年第3期。
⑦弗蘭克·克莫德:《經典與時代》,載閻嘉主編《文學理論精粹讀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 頁。
⑨赫伯特·格拉貝斯:《文化記憶與文學經典》,載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寧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85 頁。
⑩佛克瑪、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 俞國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6 頁。
?張浩文:《文學經典:時間的朋友和敵人》,《文藝報》2010年2月24日。
?“權力轉移”理論是由密西根大學教授奧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于1958年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中首次提出,1980年他與古格勒教授(Jacek Kugler)合著的 《戰爭總帳》(War Ledger)一書算是該理論的完整建構。 不同于“權力平衡”認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前提,“權力轉移”認為國際體系是有層級的(hierarchy)。由于國際體系中的國家確實是大小有別的,所以“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政治權力集中于少數國家之手,而戰爭則源自體系內主要國家間綜合國力之差異、成長速度之快慢及對現況之滿意程度。 譬如主流觀點認為世界權力正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印度等,盡管當前的世界格局仍然是“一超多強”,但是“后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當今時代的“權力轉移”,除了上述的區域與國別變化之外,第二種常見的就是由政府讓渡到跨國公司、跨境網絡與社會團體、個人(中產階層的龐大和女權的自覺等)的權力轉移。
?李梅白:《詩心吳曉東: 文學性的命運》,《看歷史》2014年第5 期。
?張倩:《皮埃爾·布迪厄及其〈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
?朱國華:《認識與智識: 跨語境視閾下的藝術終結論》,《文藝研究》2008年第3 期。
?朱國華:《文學與權力——文學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序二。
?譚旭東:《也談電子媒介與文學經典的當代危機》,《綏化學院學報》2008年第4 期。
?奧爾罕·帕慕克:《帕慕克: 因談及亞美尼亞大屠殺,我成為一個真正的土耳其作家》,澎湃新聞,2015年4月28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5377。
?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 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丁曉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 頁。
???徐秀虎:《政治資源的均衡化路徑研究》,《天府新論》2011年第1 期。
?“性別政治”一詞,源于美國學者凱特·米利特的博士論文《性政治》(Sexual Politic,1970)。 《性政治》是女性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經典著作之一,通過界定性問題的政治內涵,對西方社會和文學作品中的父權制進行全面的批評。 《性政治》所指的政治并不是通常所指的議會開會、參與選舉、政黨等,而是指一群人可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關系和組合。 把這個定義再擴大一點,政治就可以被理解為“維持一種制度所必需的一系列策略”。
?《男權制的全面批判和文學作品的抗拒性閱讀——評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豆瓣,2017年6月21日,https://www.douban.com/note/625806952/?_i=4812921tUl9Hai。
??王宏維:《解讀 “性政治”》,《南方日報》2005年5月27日。
?馬新國主編:《西方文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95 頁。
?波伏瓦:《第二性Ⅱ》, 鄭克魯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 頁。
?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 頁。
?鄭露娜:《“反烏托邦三部曲” 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溫州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楊慧林:《“圣杯” 的象征系統及其 “解碼”——〈達·芬奇密碼〉的符號考釋》,《文藝研究》2005年第12 期。
??丹·布朗:《達·芬奇密碼》,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05~506、517 頁。
?徐鵬:《男權意識下的女性崇拜:〈達·芬奇密碼〉中的圣女崇拜》,《劍南文學》2011年第1 期。
?萊斯利·菲德勒:《文學是什么? 高雅文化與大眾社會》,陸揚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 頁。
?邁克·德達:《悅讀經典》,王藝譯,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9 頁。
??顧林:《史鐵生文學經典化歷程初探》,《中國文學批評》2021年第3 期。
?楊洪承:《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6月12日。
?吳義勤:《當代文學“經典化”: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面向》,《光明日報》201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