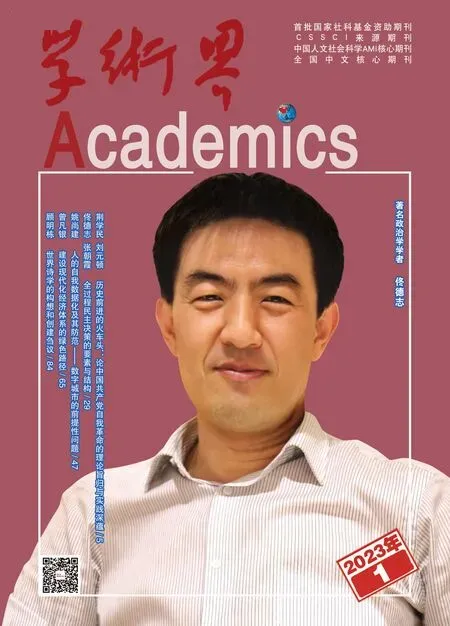規范主義者何以言自然〔*〕
——基于布蘭頓哲學的闡釋
周 靖(上海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 上海 200235)
“自然”(what it is)與“應然”(what it ought to be)之間的關系自休謨始便是一個難解的經典論題。懷疑論者斷然否定我們能夠從關于世界的主觀理解進展到關于世界本身的客觀知識,其主要理由在于,在主體間達成的合乎規范的理解層次上,我們無法根除這種理解中滲透的主觀性,從而呈現一個“清白”的世界本身。與此相關,布蘭頓(R.Brandom)在其近作《信任的精神》中,借助對黑格爾哲學的吸收和運用,為我們提供了一道“從最初(屬于自然界)的單純的生命有機體轉變為精神的規范性領域內的居民”的思路,〔1〕在布蘭頓對“自然”與“應然”關系的闡釋中,我們既能夠對“規范”提供一種非還原論的自然主義解釋,也能夠同時在“應然”的規范視野內談論“自然”的世界之所是。
一、動物性“欲求”的意義結構
在《信任的精神》一書的“結論”中,布蘭頓道明了其數十年來始終堅守的基本立場,即“不相容性和后果性的模態關系既有著真勢的(alethic)形式,也有著道義的(deontic)形式。我們既可以對它們作出法則論的(合乎定律的,nomological)解讀,也可以作出規范的解讀。這些模態相應闡明了存在的客觀領域(實在,事物的自在存在)和思維的主觀領域(顯像,事物的自為存在,事物被理解為什么)”。〔2〕其中,不相容性與后果性指的是物與物之間的實質(material)關系,如“紅”與“白”的不相容性,從吃下“紅色的蘑菇”到“死亡”的推論,這類關系是合乎定律的自然關系;相比之下,在道義層面上對這類關系作出的規范解讀則體現了我們對“自然”的“應然”理解。在布蘭頓那里,自然法則和應然規范是深深捆綁在一起的,這種立場的基本理由在于,“意義(顯像,現象,自為存在)的差別性和指稱項(實在、本體、自在存在)的統一性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只有在它們包含彼此的語境中才能理解它們”。〔3〕
從表面上看,布蘭頓的這一觀點類似于康德立場,康德認為“直觀和概念構成了一個我們一切知識的要素,以至于無論是概念沒有以某些方式與它們相應的直觀、還是直觀沒有概念,都不能提供知識”。〔4〕然而,在康德那里,直觀中把握的雜多已經有了一個綜合,從而“直觀雖然呈現雜多,但若沒有一種此際出現的綜合,就永遠不能使這種雜多成為這樣的雜多并被包含在一個表象中”。〔5〕康德因此面臨兩個進一步的問題,一是承諾為雜多提供來源的“物自體”存在,二是構建能夠借以對感性雜多進行綜合的知性范疇形式。與康德不同,在《信任的精神》中,
(a)布蘭頓從對動物層次具有的欲求(desire)層面開始討論,嘗試在“緊扣”世界本身的意義上構建初始的意義(significance)和自我意識;
(b) 布蘭頓用社會層面的社會規范性和歷史性取代德國觀念論中的先驗性和超驗性,嘗試在社會性的承認(recognition)和歷史性的回憶(recollection)中同時實現主體和社會、世界與語言的構建和發展。
本節擬討論論題(a),下一節將討論論題(b)。就論題(a)而言,我們的討論將下降至動物性的欲求層面,此時討論的動物至少需是一類理性生物,它能夠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行事。但要注意的是,合乎理性地行動的能力不要求動物具備成熟的概念,僅要求它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如它不會吃下紅色的有毒蘑菇,會避開捕食者的地盤而不會有意闖入等。
布蘭頓首先區分了兩類對周遭環境中的對象作出可靠反應的模式:
(1) 鐵在潮濕的環境中生銹;〔6〕
(2)饑餓的動物對食物有著欲求(desire),它將事物(thing)視為可以滿足其欲求的某物(something),即食物,從而在某物從樹上落下時會直接吃下它。〔7〕
布蘭頓的這一區分與布洛克(N.Block)對“取用意識”(access consciousness)和“現象意識”(phenomenal consciousness)的區分類似,〔8〕認為在情形(1)中,鐵僅對潮濕的環境有著可靠的反應模式或傾向(disposition),但鐵不具有自我意識。相比之下,在布蘭頓看來,情形(2)則包含了一種基本的“立義”行為——動物關于事物的“欲望性覺識”(orectic awareness)體現了一種由如下三種要素構成的三位結構:態度(欲求),例如饑餓;回應性的活動,例如進食;以及意義項(significance),例如食物——這種“立義”行為將幽暗的“本體”(noumena)直接構建為“現象”(phenomena)。進而,現象意識中既敞開了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同時動物在基于欲求的對事物的直接的“認知關系”中,在規定什么對“我”而言是有用的對象的意義上,也構成了初始的自我意識。
現象意識和自我意識是同時構建起來的,此過程需依賴于“事物本身”,因為“欲望不僅是以某種方式行事的傾向,因為某動物傾向于對對象作出反應的活動是否能夠滿足其要求,這取決于那些對象的特征”。〔9〕布蘭頓認同實用主義的一個基本觀念,即“最根本的那類意向性(在指向對象的意義上)是關于世界中的對象的,這些對象是感性(sentient)生物所嫻熟應對的世界中的對象”。〔10〕這些對象就是自然之物,是世界本身具有的樸素之物,而非某種掩藏在現象之后的、無法直接觸及的“本體”。
關于本體和現象,布蘭頓將前者闡釋為“可以被認知的東西”,后者則是關于前者的“嘗試性認知”。〔11〕世界是可知的,但這不意味著世界完全是在屬人的(personal)概念范圍之內的。與麥克道威爾(J.McDowell)認為“思維無邊界”,從而“概念性”是一路向下地涵括世界的全部范圍這種立場不同,〔12〕布蘭頓認為,世界的可知性的確承諾了我們能夠以概念的形式將它表達出來,但這不意味著世界沒有自身的屬性——恰是因為世界有其客觀屬性,我們在主觀的實踐活動中才會對之有著錯誤或正確的理解,這種現實存在的張力構成了推動認知活動前行的動力。例如,動物的“進食是這樣的一種活動,它對饑餓的欲望有著工具上的適當性(instrumentally appropriate)。這是一種主觀上適當的,因為這種活動實際上是饑餓的動物在饑餓的欲求狀態下被迫做出的活動。它也是客觀上適當的,因為它是一種對環境中的對象作出反應的活動,這一活動實際上通常(足夠)會帶來對欲求的滿足”。〔13〕只有在這樣的成功進食活動中,理性生物才能建制起有意義的世界:據其意義,將本體構建為初始的現象界;只有在這樣的世界中,其意義才是有效的。“自然”與“應然”攜手并進、互為前提,不能用“應然”完全掩蓋“自然”。
總結而言,布蘭頓近來下降到動物性欲求的層面來討論意義的緣起,在初始的意義和自我意識的構建中,“世界本身”無疑發揮著不可消除的作用。然而,具有自我意識的生物與如我們這樣的規范主體仍然相距甚遠,如何從這樣的自然生物發展成社會生物,理性生物具有的合乎定律的反應傾向如何進一步呈現為我們的規范表達,這些構成了布蘭頓下一步需要回答的問題。
二、“承認”雙層次的規范建制
“規范”通常指某一主體在公共空間內如何以正當方式行事的規則,因而它涉及到“我”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從自然層面的“物—我”單層次的、直接的認知(cognitive)關系進展到應然層面的“物—我—我們”雙層次的承認(recognitive)關系蘊藏著一道從具有自我意識的個體進展到社會性的主體的思路,在此過程中,埋首于應對自然對象的理性生物遭遇到另一個類似的理性生物,他們彼此“承認”,攜手邁入精神展開的“歷史”。“承認”是布蘭頓從黑格爾那里取用的一個概念,它指的是將他人視為與我們一樣的主體的社會實踐態度。布蘭頓“根據承認來從社會視角解釋規范性,以及根據回憶理性(recollective rationality)來從歷史視角解釋概念內容的表象維度”。〔14〕其中,表象維度恰是在初始的“物—我”認知關系中獲得的世界內容。
乍看之下,布蘭頓這里的表述明顯有著讓人感到困惑之處:他似乎認為表象性的自然是通過回溯視角以合乎理性的方式重構而來的,而重構活動是一種以“承認”為態度的規范活動,那么,我們將面臨本文所指的問題——規范主義者何以言自然?換言之,主體間的承認關系如何進入到“物—我”間的認知關系,從而能夠保證在社會視角下展開的那些合乎規范的闡釋確然是亦可從歷史視角重構的那些表象內容?
這一問題的答案蘊含了兩點關鍵認識:首先,動物性欲求層面建構起的內容(現象)和認知關系能夠進一步被普遍化和范疇化,從而演化為更為高階意識的內容和知識形式,這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在“物—我—我們”雙層次的模式中伴隨著社會性的交往活動,孤獨應對世界的欲求性個體在與另一個理性主體的遭遇中發展為一個主體,這必然要求個體承諾的內容和理解能夠同時得到他者的普遍認可。其次,在此意義上,后繼從歷史視角進行的回憶理性重構將仍然能夠呈現對初始現象的理解,只不過此時的理解呈現了更高的綜合或更完備的表達,但這種綜合仍是對原先內容的綜合,在此意義上,規范主義者仍可以言說自然。
具體而言,關于第一點認識,布蘭頓指出,動物性欲求層面上“物—我”層次的認知關系中,理性生物獲得了某種“自我意識”,而非如鐵塊具有的那般“取用意識”,這是因為理性生物在活動中對其周遭環境進行著有模式的反應,它能夠根據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包括相容性和不相容性關系,以及后果性關系)作出實質推論(material inference),如“知道”吃下紅色的蘑菇就會死亡這種“后果”,以及“紅色”與“白色”的不相容性。理性生物不需具備成熟的概念便能夠作出這樣的推理。
具有作出實質推論的能力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理性生物因此能夠對其認知過程(實質推理)以及對象(現象)進行普遍化或范疇化的處理,從而,在后繼的活動或與其他理性生物的交互活動中,能夠直接將普遍化的認知過程和已有意義負載的對象作為一個可直接調用的單位;進而,當遭遇到另一個類似的理性生物時,“承認”實際上將會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是在個體內部展開的線索,個體會反省自身將事物理解為某物的“承諾”,如果其活動失敗,他將會對其承諾作出一些修改和完善。另一條線索是人際間或理性生物間“溝通”的線索,個體的承諾在尋求合作的“規范”態度下,將會受到來自他者的審查,那些經受住審查的個體理解(意見)將會構成知識,個體承諾的“內容”則將構成建制世界的實質材料。〔15〕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仍是在討論尚不具有成熟概念或語言的理性生物之間的交流,用托馬塞洛(M.Tomasello)的話說,“在這種交流中,個體首先發出同合作任務相關的注意或意向性想象信號,接收到該信號后,他的伙伴則會推論信號所包含的社會性意圖”。〔16〕“信號”將會引發推理反應,這意味著將發出信號的他人“承認”為一個與自身一樣的他者,即第二人稱,并且,從第二人稱視角“反身”省察自己,省察性的互動將會再次確認第一人稱的“我”,此時,“我”不再是一個直接與“事物”接觸的孤獨個體,而是與他者一道進行探查的主體。隨著交往活動的豐富化和深化,推理進入遞歸的程序,“個體”被確定為總是有著“第二人”進行監控的“主體”,成為一個總是經由他者中介的反思性自我。在澄清信號意義的遞歸的主體間的活動中,信號既獲得了越來越清晰和穩定的規范意義,信號所“表征”的因果關系也將在主體間最初的想象和符號化的認知活動中被固定為類別、圖式和原型等。在類似的意義上,布蘭頓指出,“具體的承認包含了認可另一個人對事物如何(作為Ks的事物是怎樣的事物)有著某種權威。當我這樣做時,我將你視為‘我們’(初始的規范意義上的‘我們’)的一員,‘我們’受制于相同的規范,相同的權威;‘我們’恰由這般態度所建制”。〔17〕其中,Ks指的是將事物理解為K的類別,只有“我”在“我們”中才能將原先對事物的具體理解拓展至普遍理解。
關于第二點認識,隨著“我”發展為“我們”中的一個“我”,〔18〕具有穩定意義的符號演變為“概念”,進而我們最終能夠根據成熟的語言,從形式上以合乎邏輯的方式來表達對世界的理解。在其《使之明晰》〔19〕與《闡明理由》〔20〕等著作中,布蘭頓重點發展了其推論主義(inferentialism)思想,即如何以推論方式闡明推論中使用到的語言表達式所“關涉”的內容。對布蘭頓的工作心存疑竇的反對者們仍然會提出筆者曾稱之為“語義學之幕”的問題,即在使用語言的判斷活動或語義交往活動中將會出現一種以推論為方式、以概念為原材料織就的“語義學之幕”,它替代了近代哲學中橫陳于心靈與世界之間的由因果關系織成的“因果性之幕”。〔21〕語義學之幕帶來了“語言/世界”的劃界,這種劃界在以使用語言作出推理的方式所闡明或表達的對象(what is expressed)和外部世界中的實際事物(what there is)之間劃出了一道界限,在此意義上,布蘭頓面臨的問題是,推論的闡明能否刺破語義學之幕,從而達到事物本身。在布蘭頓看來,這里的問題源于下述錯誤立場,“人們經常將推論的闡明等同于邏輯的闡明。實質推論因此被看作是一個派生的范疇。這種觀點認為,所謂合理的(being rational)……可被理解為一種純粹的邏輯能力。”〔22〕人們不僅將推論能力視為人所獨有的理性能力,也認為形式上正確的推論是普遍有效的。然而,在布蘭頓看來,“推論”實際上包含了實質推論和形式推論,前者是在應對周遭世界的實質語用活動中作出的推論,后者則是在主體間使用語言的話語活動中作出的推論,結合上一節中的討論,我們看到布蘭頓幾十年來始終恪守的立場是:應該融合實質的語用學討論和形式的語義學討論;然而,盡管我們在現實的闡釋活動(articulating)中,從方法論上來說,僅能以過語句和次語句(sub-sentential)表達式在推理活動(reasoning)中起到的作用來理解表達式的意義和內容——這種語義推論主義(semantic inferentialism)構成了布蘭頓哲學中一個重要的支柱;但是,從實踐的發生次序上來說,實質語用層次的闡明是在先的,我們終究需要根據在語用層次辨明的“知道—如何”“做”來理解“知道—什么”“說”出的話語,根據實質推論的“善”(goodness)來衡量后繼的形式推論的“正確性”(correctness)。〔23〕
布蘭頓持該立場的理由在于,對相同內容作出的實質推論和形式推論是同一過程的兩面,換句話說,“言”與“行”互相規定,“言行合一”意味著兩類語匯的貼合。布蘭頓否認關于世界的闡釋和世界本身之間存在一道需要跨越的溝壑,在此意義上,根本不存在刺破語義學之幕這類任務。
布蘭頓進一步為“物—我—我們”雙層次的“承認”添加上了“歷史”維度,“規范態度和規范身份之間所具有的有著社會性本質的關系,以及在關于概念內容的語義學方面,內容的自為存在(現象、意義、表象)和自在存在(本體、指稱項、被表象物)之間有著歷史性本質的關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同一種發展過程的兩個維度,即承認的維度和回憶的維度”。〔24〕在歷史的進程內,本體與現象彼此對照,指稱與意義在我們的認知和承認活動中一道發展,“我”在“我們”中,“我們”在世界中。
總結而言,根據布蘭頓的敘事,關于世界的客觀理解和主觀闡釋始終是彼此成就的,在此意義上,自然與應然之間根本不存在需要跨越的鴻溝,從而規范主義者必然能夠言說自然。然而,布蘭頓似乎太過輕易地承諾可以從自然性的生物發展至應然性的主體。實際上,布蘭頓對真正主體性到來的進程(其中,主要經歷了從傳統、現代性,再到后現代性的發展階段)作出了復雜、細致的討論,限于本文主旨,不作贅論。
三、反對規范自然主義
前兩節的闡釋仍有些讓人感到困惑之處。布蘭頓一般留人以理性主義者的形象,這是因為他強調根據語言表達式間的推論關系而非語言和世界間的指稱關系或因果關系來分析表達式的意義與意向狀態的內容,其理性主義進路以概念性為哲學探究的起點,而非直接探查心靈與認識能力的自然源起。實際上,布蘭頓在其所有著作中從未提供過對自然發展史的描述,那么,究竟如何在理性主義框架下理解他對動物性欲求的討論?
作為理性主義者的布蘭頓,他明確反對規范自然主義立場,即根據自然性的生物特征來理解我們的理性成就。規范自然主義者“……反過來認為實踐態度源于情緒特征……由于這種態度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以諸如我們自身這樣的社會生物所具有的自然歷史的形式存在,因此它們建制或規劃的規范身份也是如此”。〔25〕我們是歷史性的生物,但需要區分開兩種歷史性,即理性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布蘭頓哲學中滲透著一種黑格爾式的哲學精神,他始終認為“思維形式首先表現并且記載在人的語言里。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必須牢記,那把人和禽獸區分開來的東西,是思維”。〔26〕哲學的探究應該以概念性為起點,動物性的欲求層面上已經有了意義的初始形態,因而我們可以從它開始討論,探究它后繼發展的歷史。然而,這種歷史不是對其生物性特征的歷史描述,例如進化論敘事、動物行為學敘事,以及訴諸顱內神經狀態的敘事等——需要尤為強調的是,布蘭頓并不反對這類自然敘事具有的價值,他僅是認為這類工作是認知科學家們而非哲學家們的工作。〔27〕從哲學上說,規范自然主義的錯誤在于,混淆了自然的歷史敘事和社會性的歷史敘事,哲學工作者更應在后一類敘事中展開自身的獨特工作。
我們可以根據丹尼特與布蘭頓的思想差別來進一步理解布蘭頓這里的立場或哲學態度。丹尼特哲學呈現了一種典型的自然主義進路,即從世界一方直接探究心靈的自然起源,可以預見的是,布蘭頓與丹尼特之間有著無法調和的思想差別。
布蘭頓多次援用丹尼特的“意向立場”(intentional stance)以表明,理性生物關于某物的意向已然滲透有初始的規范維度,這些(可能僅是實質推論層次的)規范為語言表達式之間的理性(rational)關系奠定了基礎,從而我們可以進一步將語言表達式所關涉的意向內容在推理活動中加以闡明。這種闡明的過程是在自然和應然之際,在“行”與“言”之際展開的認知和承認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活動。具體而言,丹尼特這樣介紹意向立場的工作機制:“首先,你決定把要預測其行為的對象看成是一個理性自主體(rational agent);然后根據它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它的目的,推測這個自主體應當具有什么信念。之后基于相同的考慮,推測它應當具有什么愿望,最后你就可以預言:這個理性自主體將依據其信念行動以實現其目的。從所選擇的這組信念和愿望進行一些推理,在很多——但非所有——情況下都能確定自主體應當做什么;這就是你對自主體將做什么的預言。”〔28〕布蘭頓將丹尼特的意向立場闡釋為如下三個推理步驟:〔29〕
(1)首先認識到或被歸因的(attributing)意向狀態有著規范意義(significance),這意味著持有該意向狀態的理性生物應該以某種特定的合乎規范的方式行事;
(2)將規范身份歸派給理性生物的信念和欲求,這意味著該理性生物在持有那類信念和欲求時,持有理由;
(3)最后,基于前兩點,界定一種意向系統,任何持有這種系統的生物均合乎理性地行動。從而,我們可以在規范的空間內談論意向狀態相關的信念和欲求內容。
實際上,丹尼特對布蘭頓為何論及他的“意向立場”了然于心,因為在意向立場中已經建構好了布蘭頓需要的初始意義或規范。〔30〕丹尼特承認“用語言來表達愿望的能力打開了愿望歸屬的閘門”。〔31〕語言帶來了關于欲望更為具體的歸因。然而,丹尼特同時指出,“并非有機體之間的一切互動都是交流性的”,〔32〕從而是語言性的。恰在這一點上,丹尼特開始與布蘭頓分道揚鑣,他對布蘭頓主要有著如下三點批評:
首先,丹尼特認識到他與布蘭頓在一階的意向系統和二階的意向系統何者為先的問題上懷有分歧。一階的意向系統指系統懷有信念和欲求,但沒有關于信念和愿望的信念和欲求;二階的意向系統則更為復雜地包含了關于自己以及他者的信念和欲求的信念和欲求。也就是說,一階系統體現的是單獨個體的意向與對象(意向內容)的直接關系(如布蘭頓所指的“物—我”認知關系),二階系統則包含了對直接關系的反思,以及對其他個體相似系統的理解(如布蘭頓所指的“物—我—我們”雙層次的關系)。就此而言,丹尼特的解釋順序是從一階的意向系統“自下而上”地邁向二階的以及更高階的意向系統,而在他看來,布蘭頓則采取了相反的“自上而下”的解釋順序,即從二階層次上意向狀態已經滲透有的規范——主體此時能夠將意向狀態合乎規范地歸屬給其他主體——來解釋一階層次上的意向內容。
其次,解釋次序上的不同構成了兩人思想差別的底色。丹尼特批評到,如若采取自上而下的解釋順序,訴諸理性共同體規范的言語活動來談及意向內容的話,那么,共同體如何而來,這便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在丹尼特看來,在初始意向性中,某主體認為他者“似乎”具有相同的意向系統,這種“似乎”態度將他者視為與我類似的存在,在進化的漫長歷史中,“似乎”態度的成功與失敗促成“我們”的聯結以及對“我”自身的重構——共同體有著如此這般的自然源起。然而,布蘭頓認為,“初始的、獨立的,或非衍生的意向性已經全然是一種語言事態了”。〔33〕這一表述讓布蘭頓免除了對其中的自然起源作出直接的描述,也體現了布蘭頓與丹尼特的思想之別,這不禁讓丹尼特懷疑布蘭頓何以在“無根”的共同體內談論自然。
最后,即便我們將共同體如何而來的問題放置一旁,在規范本身的起源問題上,兩人也有著類似的歧見。丹尼特指出,就人類這種使用語言的生物而言,布蘭頓的確正確地認識到,我們僅能通過語言表達的方式來談論意向內容,然而,僅在社會的范圍內編織規范,這將省略掉“交流”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維度:我們人類可以出于獲得快樂的單純目的進行交流,但交流在自然史中并非偶然發生的,它涉及復雜的適應和調整機制,這意味著規范是自然選擇這一過程的結果,而非單純的語言構造。〔34〕規范與共同體一樣有其自然源起,從一階意向系統邁向二階以及更高階的意向系統是“成為人的條件”,是意義和規范衍生的條件,對此條件進行具體的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在丹尼特看來,布蘭頓僅在已經屬人的語言、共同體和規范范圍內進行探究,這將忽略掉自然主義一面的洞察。
基于上文中的討論,我們可以幫助布蘭頓對丹尼特的指責作出一個簡單回應。在筆者看來,爭議的根源在于,丹尼特將布蘭頓所指的已經具有規范形態的“概念性”理解為共同體能夠使用的成熟概念,從而他將布蘭頓的事業理解為在二階的意向系統內談論一階的意向系統內關涉的自然內容。實際上,布蘭頓認為“概念性”一路向下至動物性欲求的層面——這體現在他對丹尼特意向立場的認可上——并且,如上一節中闡明的那般,自然與應然之間、實質的語用推理與形式的語義表達之間,或一階的意向系統和二階的意向系統之間從未存在本體論的差別,因而,在布蘭頓那里,不存在簡單的何種層次上的意向系統在先的問題:從實踐的層次上說,低階的系統為先;從闡明的方法論上說,高階的系統為先;但“低階”和“高階”之別僅體現為認知和承認的語用和語義探究在發展程度和階段上的不同,而無本體論上的差別。在這一點上,丹尼特無疑誤解了布蘭頓。
但就丹尼特倡導的進化論敘事而言,布蘭頓明確指出兩點:一是,他的理性主義闡明與自然主義的進化論解釋兼容;二是,為心靈與世界間的因果關系提供科學模式,這是認知科學家而非哲學家應當為之的工作。丹尼特的相關立場是,“認為哲學考察并不高于或優先于自然科學考察,而是與這些真相探索事業構成合作伙伴關系,哲學家的適當工作是澄清和統一常常相互沖突的看法,以獲得一個單一的宇宙圖景。那意味著歡迎來自良好確立的科學發現和理論的禮物,并將其作為哲學理論建構的原材料,所以,做出對科學與哲學都是有見識的建設性批評是可能的。”〔35〕故而,丹尼特的討論多以科學的發現為材料,相比之下,布蘭頓則更加像是一位傳統或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他秉承著理性的思辨精神作出哲學探討。
總結而言,布蘭頓與丹尼特對于哲學與科學的關系有著不同的立場,布蘭頓認為,自然發展的終點——概念性——構成了哲學討論的起點,在這樣的起點上,主觀的規范理解直接與自然的世界本身根深蒂固地糾纏在一起,這種立場實質上是對世界的存在方式(ways of being)作出了解釋,認為世界只有在我們的理解中才是可能的,但我們的理解只有依存于世界自身的特征才能是正確的。在此意義上,規范主義者必然能夠言說自然。相比之下,丹尼特則試圖通過對自然史的描述來理解規范的起源,盡管他將意識或規范視為僅是由語言構建的幻象,根本不存在意識這類東西,從而自然描述便能夠充分地直接解釋一切。〔36〕或許因為此,丹尼特在其著作中多是在對科學發現進行描述后便結束其思考,直接給出哲學上的結論。布蘭頓無疑不會接受這類承諾了“規范自然主義”的探究方式。
四、結 語
布蘭頓哲學的基本立場在于,認為闡明表達式之間形式(formal)關系的道義規范語匯需對闡明內容之間實質(material)關系的真勢模態語匯負責。粗略言之,道義規范語匯能夠使得我們“說”出在“做”什么,而關于“做”的真勢模態語匯則限定了我們能夠“說”什么;在“言”與“行”的關系上,“言”與“行”互相規定,“言行合一”意味著兩類語匯根本上是關于同一類事件的不同表達。布蘭頓實際上抵制在截然對立的自然與應然之間作出劃分,從而對他而言,或許根本不存在“規范主義者何以言自然”這類問題。
注釋:
〔1〕〔2〕〔3〕〔7〕〔9〕〔11〕〔13〕〔14〕〔17〕〔24〕〔25〕Robert Brandom,A Spirt of Trust: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238;667;451;240-247;242;666;242;12,245;253;303;264.
〔4〕〔5〕〔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9、128頁。
〔6〕〔10〕〔29〕〔33〕See 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 & discursive commi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3-34,592,55-57,143.
〔8〕Block,Ned,“On a confusion about a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8.2(1995):pp.227-247.
〔12〕參見〔美〕麥克道威爾:《心靈與世界》,韓林合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0-51、30頁。
〔15〕參見陳亞軍:《實用主義:從皮爾士到布蘭頓》,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7頁。
〔16〕〔美〕托馬塞洛:《人類思維的自然史:從人猿到社會人的心智進化之路》,蘇彥捷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頁。
〔18〕布蘭頓對此過程進行了復雜的具體討論,限于本文論題,在此不作贅論,參見Robert Brandom,A Spirit of Trust: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469-499.
〔19〕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 & discursive commi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0〕〔22〕〔美〕布蘭頓:《闡明理由:推論主義導論》,陳亞軍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7頁。
〔21〕參見周靖:《論語言在開顯世界中的規范建制功能——基于布蘭頓語言哲學的闡釋》,《哲學研究》2021年第5期。
〔23〕See Robert 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 and Contempo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9.
〔26〕〔德〕黑格爾:《邏輯學I》,先剛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頁。
〔27〕參見〔美〕布蘭頓:《在理由的空間內:推論主義、規范主義與元語言語匯》,孫寧、周靖、黃遠帆、文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44頁。
〔28〕〔31〕〔32〕〔美〕丹尼特:《意向立場》,劉占峰、陳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8-29、32、332頁。
〔30〕〔34〕See Dennett,D.,“The Evolution of ‘Why?’”,InReading Brandom: On Making It Explicit,Bernhard Weiss and Jeremy Wanderer (Ed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p.48,53-55.
〔35〕〔美〕丹尼特:《自由的進化》,輝格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20頁。
〔36〕Dennett,Daniel C.,“Animal consciousness: What matters and why”,Social Research,1995,p.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