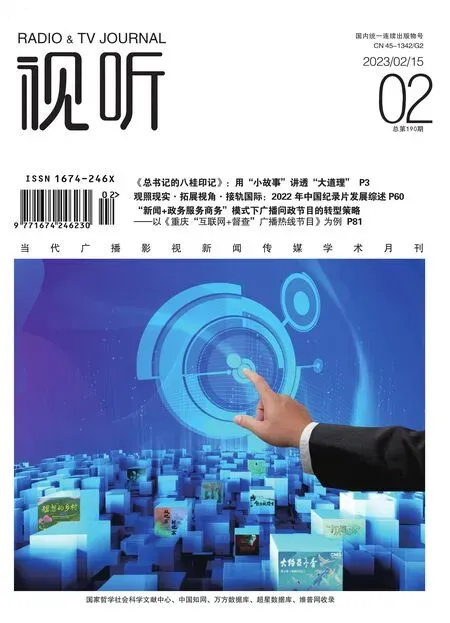青年文化視域下新主流影視的敘事表達
◎張洋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重點強調(diào)青年群體在國家戰(zhàn)略層面、社會層面以及家庭層面的重要地位。青年強則國強,“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繼續(xù)發(fā)揚五四精神,以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為己任,不辜負黨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這是時代對新青年賦予的新定位,也是中國新青年肩上承擔(dān)的責(zé)任和擔(dān)當(dāng),弘揚的是一種新時代、新青年、新作為的初心力量和使命精神。”①在總體方針的指引下,以青年群體為主的亞文化因子逐步融入主流影視中,并在與其他文化碰撞中展現(xiàn)出自身獨有的蓬勃生機與活力,賦予主流影視年輕化的樣態(tài)姿勢。本文以主流影視歷時性的敘事轉(zhuǎn)變?yōu)榍疤幔骄啃轮髁饔耙暸c亞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耦合,在文化接合中實現(xiàn)觀眾情感的跨越,達成觀眾心靈的默契。
一、敘事流變:歷時梳理中的價值重現(xiàn)
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范式,青年文化正以積極、個性的青春樣態(tài),彰顯出自身的時代價值。青年亞文化自誕生起,便被視為一種與主流文化相悖的異類文化、邊緣文化。正如馬赫列爾所說:“從家庭和社會群體的地位本身來說,青年往往(雖然并非不可避免)處于一種‘邊緣’狀態(tài):他們還沒參加生產(chǎn),不負擔(dān)經(jīng)濟責(zé)任,處于‘服從’‘家長’權(quán)威的地位,因此有依附性,一般說來,必須學(xué)習(xí)‘成人的角色’,通過一段漫長的社會學(xué)習(xí)來為未來的成人地位做準備。”②由此可見,邊緣性是青年文化的一個突出特質(zhì)。青年群體在社會與家庭共同作用中所產(chǎn)生的錯頓感,使得青年群體選擇以異類的方式突出自我,從而獲得來自社會與家庭的關(guān)注。基于自身的本質(zhì)屬性,青年文化與主流文化有時會處于針鋒相對的過程中。但隨著市場受眾的轉(zhuǎn)移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革新,主流文化以下潛的姿態(tài)逐步實現(xiàn)對青年文化的收編與互嵌。
相比于國外青年文化,國內(nèi)青年文化的發(fā)展起步較晚。改革開放初期,政策重心的轉(zhuǎn)移和國內(nèi)文化語境的改善,為青年文化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但由于彼時國內(nèi)生產(chǎn)力仍處于窘境中,加之物質(zhì)資源的匱乏,青年群體急需一種方式來宣泄物質(zhì)與精神上的雙重壓力。不過,與以往時代下的青年文化相比,“它是當(dāng)代中國青年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形成的全新的行為方式,不這樣看,就無法公正地評價當(dāng)代中國青年文化,同樣也無法正確地理解當(dāng)代中國青年文化在我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巨大歷史作用。”③因此,青年文化正以一種蓬勃的姿態(tài)在與主流文化的碰撞中嶄露頭角。
進入21世紀,互聯(lián)網(wǎng)應(yīng)用技術(shù)的驟變促使著市場受眾群體轉(zhuǎn)移與搬遷。特別是新媒體的出現(xiàn),既加快了受眾搬遷的進程,又為青年文化的飛速發(fā)展提供了外部契機。時代形勢的改變,促使功能內(nèi)容不斷革新。新形勢下,面對外部資本力量的嵌入,主流文化不得不以包容性的樣態(tài)表征接納與收編青年亞文化,具體表現(xiàn)在兩點。其一,青年文化的主流表達。隨著受眾主體的不斷下移,青年群體的受關(guān)注度不斷提升。“變”是時代發(fā)展亙古不變的定律,青年文化從邊緣化逐漸中心化的過程趨勢,預(yù)示了社會對青年文化的認同,并在與主流文化互嵌中達成新的敘事方式。其二,主流文化的下潛與收編。隨著全球化發(fā)展趨勢的加快,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yè)化沖擊著主流文化的主導(dǎo)地位。面對嚴峻的形勢局面,主流文化由被動應(yīng)對轉(zhuǎn)向主動出擊,主動吸納以青年文化為代表的其他亞文化因素,并通過接洽新媒體平臺的傳播優(yōu)勢,達成主流架構(gòu)的內(nèi)部賦新。
二、敘事表達:形式賦新中的青春對話
(一)想象消費的青春化呈現(xiàn)
時代內(nèi)涵的演變會引起形式功能的變化。當(dāng)下,“伴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成長起來的90后‘網(wǎng)生代’觀影群體……消費選擇備受網(wǎng)絡(luò)媒介濡染,具有網(wǎng)感氣質(zhì),其所代表的青年亞文化不斷被主流文化收編,日漸成為新主流大片的靈感來源。”④因而,新主流影視在文化接合的藍圖中,不斷順應(yīng)觀眾口味變化,以全新化的姿態(tài)滿足年輕化的市場群體,進一步形成共情共鳴的價值認同。
與主流影視不同,新主流影視既繼承了以往主流影視永不褪色的價值內(nèi)涵,打破政治視野下的單一化敘事建構(gòu),又在題材形式上實現(xiàn)與青年群體的平等對話。并且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視域下的網(wǎng)生代青年群體,“虛擬”“未來”“科幻”日漸成為這個時代青年群體的群像表征。互聯(lián)網(wǎng)培養(yǎng)了他們高度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甚至取代以往影視作品的主導(dǎo)性地位。因此,“這個時代的青少年主體受眾需要一種超越現(xiàn)實的‘想象力消費’更甚于認知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消費。”⑤毋庸置疑,以網(wǎng)生代為代表的青年亞文化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影響著新主流影視的發(fā)展走向,并在主流文化中彰顯著青春之姿態(tài)。
所謂想象力消費,指的是依托于受眾的想象力上限,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腦洞極大的藝術(shù)作品,從而實現(xiàn)受眾對藝術(shù)作品的認同。著名學(xué)者陳旭光認為,想象力消費是“受眾對于充滿想象力的藝術(shù)作品的藝術(shù)欣賞和文化消費的巨大需求。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想象力消費’,不同于人們對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消費需求,它主要表現(xiàn)為青少年受眾對于超現(xiàn)實、后假定性美學(xué)類、玄幻、科幻、魔幻類作品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需求”⑥。因而,新主流影視要想實現(xiàn)對青年群體的收編,便要在題材形式上順應(yīng)他們的想象力消費。當(dāng)下,新主流影視彌補了主流影視的空缺,實現(xiàn)題材形式的超現(xiàn)實主義構(gòu)造,在充分發(fā)揮青年群體想象力消費的過程中,逐漸縫合主流文化與青年亞文化間的差異與地位,拉近國產(chǎn)影視作品與好萊塢電影間的想象差距。
《流浪地球》作為開啟“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科幻巨制,以圍繞種族存亡的問題,書寫了一代國人為后人繼往開來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太陽異變下的極端環(huán)境”“地核深處的巨大動力引擎”“宏偉奇觀下的地下世界”……一幕幕僅存在于未來的奇觀景象,通過震驚觀眾的奇觀化場景布置,為青年群體描摹了理想化的未來世界,從而迎合青年群體的想象力消費。貓眼數(shù)據(jù)顯示,“國內(nèi)電影市場觀影結(jié)構(gòu)逐步偏向年輕化。科幻電影核心的觀影人群,男性年齡分布在25~34歲之間,19~24歲人群只占到15.6%,略高于大盤。”⑦由此可見,以《流浪地球》為代表的科幻巨制也正是立足于青年群體對超現(xiàn)實主義的市場需求,才能實現(xiàn)口碑與效益的雙豐收。同樣,圍繞著中華神話傳說而展開的奇幻創(chuàng)作也是對觀眾尤其是青年觀眾的一種想象力消費。無論是《哪吒之魔童降世》《西游記之大圣歸來》還是《白蛇:緣起》《姜子牙》,都存在一個共性的市場條件,即滿足青年群體的想象力消費。這些電影通過幽默詼諧的語言,搭配萌化的人物形象,并以奇幻般的題材敘事,將中華文化中的仁、智、孝融入青年亞文化的內(nèi)涵價值中,實現(xiàn)題材形式上的青春化表達。這也是好萊塢科幻電影一直頗受中國市場喜愛的最主要因素。
(二)話語表意的青春化書寫
作為視聽藝術(shù)的新主流影視是社會、精神、文化的共同集合體,本質(zhì)上,它通過作用于觀眾的意識層所形成的集體認知,建構(gòu)起大眾群體的集體認同與感性情感。并且,承載著眾多內(nèi)涵意旨的新主流影視在“試圖調(diào)和乃至消弭市場與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票房與口碑以及商業(yè)性與藝術(shù)性之間或?qū)α⒒蚓o張局面”⑧的過程中,既包含國家意識凝聚力情感表達,又蘊含家庭倫常關(guān)系的個性宣泄。新主流影視在話語表意中建構(gòu)出一代代青年群體的時代擔(dān)當(dāng)與歷史使命,實現(xiàn)主流文化的破圈傳播和青年群體的自我映照。
當(dāng)下,新主流影視話語表意的青春化書寫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方面,通過家國同構(gòu)彰顯青年群體的時代擔(dān)當(dāng)。無論是講述脫貧攻堅的故事,還是反映時代變革的事件,無論是從過去到現(xiàn)在,還是從現(xiàn)在到未來,都存在著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即在家國情懷中書寫出共同的使命與初心,也只有在家國情懷的敘事主線中才能消融青年群體的“叛逆”。如《流浪地球》中,由吳京飾演的中國宇航員劉培強,在全人類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時刻,毅然駕駛飛船引爆木星,在家國大義中詮釋自己的價值。《功勛》中,于敏因兒子對自己感到陌生而自責(zé),張富清因?qū)δ赣H疏于關(guān)愛而感到愧疚……每一位時代楷模,都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心中對國家的集體感、榮譽感。而青年群體也在與英雄人物對話中,感悟新時代所賦予自身的時代擔(dān)當(dāng),喚醒心中的家國夢。另一方面,通過“網(wǎng)感”元素符號適應(yīng)青年群體的審美習(xí)慣。互聯(lián)網(wǎng)多樣性、碎片化、便捷化等特征優(yōu)勢早已嵌入青年群體的審美習(xí)性,而這種審美習(xí)性使得青年群體特別是伴隨互聯(lián)網(wǎng)而生的“網(wǎng)生代”群體習(xí)慣甚至依賴互聯(lián)網(wǎng)所打造的烏托邦式虛擬世界。無論是通過抖音等新媒體平臺發(fā)布的草根創(chuàng)作,還是基于VR、AI等技術(shù)端的虛擬創(chuàng)作,都能捕捉到受眾尤其是網(wǎng)生代青年受眾的關(guān)注與喜愛。因此,新主流影視只有在主流價值引導(dǎo)中融入當(dāng)下熱門的網(wǎng)感符號,才能堅守主流而不失趣味。如講述新時代下人民與家鄉(xiāng)之間樸實而平凡故事的《我和我的家鄉(xiāng)》,影片通過單元篇章展開敘事,并且在每個章節(jié)故事之間都融入網(wǎng)感元素。影片在頗具網(wǎng)感的時代語境中,以下沉的姿態(tài)、包容的習(xí)性,實現(xiàn)主流文化與青年亞文化之間的靈魂激蕩。
(三)形象表征的青春化演繹
戈夫曼認為,“人與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相互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視作一種表演。生活中的每個人或是個體表演者,或是劇班中的一員,總是在某種特定的場景,按照一定的要求,在觀眾的注視下進行角色呈現(xiàn)。”⑨由此可見,青年群體正是通過平凡人物視角,從富有鮮明人物形象的表演與刻畫中代入年代情景,感受時代情懷,在與主流文化交流中實現(xiàn)自我召喚。
首先,新主流影視通過“前臺”演繹,實現(xiàn)與青年群體身份上的共鳴。沒有深入實踐,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當(dāng)前,新主流影視在前期演員選擇上,會充分考慮青年群體所熱衷的青年演員,并通過他們對劇中人物的生動演繹,拉近新主流文化與青年群體之間的情感距離。無論是《大浦東》《大江大河》等改革獻禮劇,還是《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嬌》等鄉(xiāng)村扶貧劇,都提出一個選擇傾向,即通過青年演員的生動演繹,捕獲青年群體的喜愛偏向。并且,新主流影視對于青年演員的采用有著嚴格的擇取標準,既要求青年演員有扎實的演技,又要求其具有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念。如單元劇《功勛》在前期制作中采用了有代表性的青年演員來飾演青年時期的人物楷模,諸如雷佳音飾演的于敏、黃曉明飾演的黃旭華等。其將時代楷模青年時期的生活習(xí)性以復(fù)現(xiàn)化的手法再現(xiàn)出來,打造青年群體心中平凡化的人物形象。
其次,新主流影視通過“后臺”重置,實現(xiàn)與青年群體情感上的共振。新主流影視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創(chuàng)新內(nèi)容表達。一方面是創(chuàng)作理念的革新。理念的先進性決定其內(nèi)容表達的新穎性。在當(dāng)下市場中,那些占據(jù)市場份額,取得市場先機的產(chǎn)品往往一開始都具有先進的創(chuàng)作理念。主流影視作為依賴受眾群體的視聽媒介,只有實現(xiàn)創(chuàng)作理念上的革新,才能最大程度地包容廣泛的受眾群體。如革命歷史題材劇《覺醒年代》,作為一部講述革命歷史的電視劇,它從歷史人物的平凡化視角出發(fā),通過小人物大時代的創(chuàng)作理念,講述了革命人物家庭中的溫情、革命中的堅毅,為青年受眾群體勾勒出一幅全新的歷史畫作。另一方面是創(chuàng)作手段的革新。伴隨著新媒介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傳統(tǒng)的制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與時代脫節(jié)。在新形勢下,新主流影視在創(chuàng)作中汲取新媒體的手法技藝,以全新化的創(chuàng)作手段賦予內(nèi)容表達新的血肉與架構(gòu)。無論是《功勛》中現(xiàn)實人物片尾呼應(yīng)的巧妙設(shè)計,還是《人世間》中父母過世后劇集發(fā)展的情感高潮,都通過一個個鏡頭組接打破傳統(tǒng)正反打鏡頭,實現(xiàn)新主流影視創(chuàng)作技法的革新。由此可見,新主流影視通過“前臺”演繹與“后臺”重置之間的樣態(tài)化賦新,使得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實現(xiàn)情感與使命的自我召喚。
三、情感互動:思想激蕩中的身份認同
伴隨著媒介融合的深度發(fā)展,青年群體對于自身選擇權(quán)的意識不斷提升。簡單地說,青年群體對于互動的強烈渴望,使新主流影視不得不借助新媒體傳播的優(yōu)勢,從而達到對青年群體價值觀的正確引領(lǐng)與溝通。
一方面,通過虛實結(jié)合下的情感互動,達成青年群體的思想認同。與以往主流影視相比,新主流影視通過敘事方式的創(chuàng)新,結(jié)合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在家國同構(gòu)的主題中,融入多樣化的敘事視角,使得青年群體在觀看影視劇的同時獲得心理與情感的沉浸式代入,從而實現(xiàn)青年群體的身份認同。如在精準脫貧方針指導(dǎo)下的《江山如此多嬌》,講述了正值青春年華的大學(xué)生干部毅然帶領(lǐng)落后山區(qū)脫貧致富的青春故事,展現(xiàn)了時代青年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以改革大變局為前提的《大江大河》講述了以雷東寶、宋運輝、楊巡為主人公的青年群體在時代變革下的選擇與堅持,體現(xiàn)了緊跟時代潮流的青春歲月。立足于當(dāng)下新時代背景下的《號手就位》復(fù)現(xiàn)了應(yīng)征入伍的大學(xué)生,在愛國之心的助力下實現(xiàn)心中屬于自己的強國夢,生動刻畫了當(dāng)代大學(xué)生的青春之姿。一幕幕極具真情實感的劇情演繹沖擊著青年群體意識認知,助力青年群體實現(xiàn)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通過新平臺下的社交互動,實現(xiàn)青年群體的思想激蕩。立足于新媒體語境下,新主流影視從前期內(nèi)容創(chuàng)作到后期傳播營銷,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新媒體平臺的傳播優(yōu)勢,并通過新平臺的技術(shù)加持,實現(xiàn)影視劇與青年群體的社交互動。其中包括使用彈幕、直播的方式與青年群體進行實時互動。如影視劇中的演員空降彈幕交流區(qū),或采用直播的形式,以“鄰家哥哥”“魅力大叔”的人物形象,實現(xiàn)對青年群體的正確引領(lǐng)與教導(dǎo)。除此之外,青年群體內(nèi)部之間也可以進行思想上的碰撞與交流。如在《人世間》中,周家父母的相伴離去直接將劇情推向高潮,這時彈幕中的青年群體產(chǎn)生高度一致的情感認同,并且在官方微博賬號評論區(qū)留下自己對劇集的情感觸動點。新主流影視劇通過新平臺的社交互動功能,有效地緩解了部分青年用戶面對說教時的叛逆感,在思想激蕩中打破圈層之間的割裂感。
四、結(jié)語
青年文化所具有的成長性特征,使得其本身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步向主流文化靠攏。而主流文化也通過下嵌、包容的姿態(tài),通過形式上的多樣性賦新,逐漸接納、收編青年文化當(dāng)中的青春化樣態(tài)。當(dāng)然,青年文化所具有的抵抗性特性,又使兩者在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入一些誤區(qū)。當(dāng)下,新主流影視在接納、收編青年文化時,要堅守主流價值的初心,以更嚴謹?shù)膽B(tài)度,處理好可能產(chǎn)生的矛盾問題,在與青年群體的情感對話中,喚醒他們的責(zé)任和擔(dān)當(dāng)。
注釋:
①徐曉明.新時代成就有為新青年[EB/OL].光明網(wǎng),2020-05-04.https://news.gmw.cn/2020-05/04/content_33801949.htm.
②[羅馬尼亞]F.馬赫列爾.青年問題與青年學(xué)[M].陸象淦,譯.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1986:246.
③周曉虹.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410.
④楊旦修.“IP”的進路與中國新主流大片的內(nèi)容想象[J].中國電影市場,2020(10):4-8.
⑤陳旭光.“想象力消費”的理論闡釋及其批評方法論考量[N].中國藝術(shù)報,2020-11-20(003).
⑥陳旭光.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想象力消費”[N].中國社會科學(xué)報,2020-07-14(001).
⑦貓眼研究所發(fā)布科幻電影大數(shù)據(jù):19—34歲女性觀眾占三成[EB/OL].界面新聞,2019-06-21.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237925.html.
⑧饒曙光,李國聰.主流大片新拓展:范式轉(zhuǎn)換與戰(zhàn)略升級[J].當(dāng)代電影,2017(01):20.
⑨王長瀟,劉瑞一.網(wǎng)絡(luò)視頻分享中的“自我呈現(xiàn)”——基于戈夫曼擬劇理論與行為分析的觀察與思考[J].當(dāng)代傳播,2013(03):10-12+16.